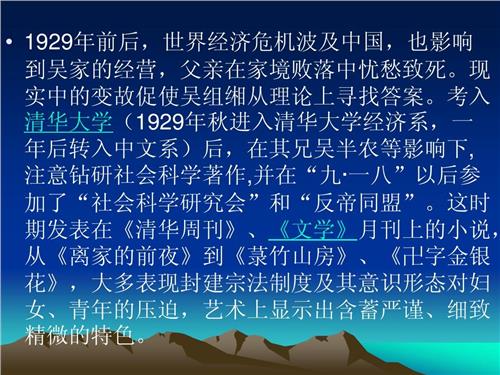吴组缃山房 吴组缃《菉竹山房》浅议——文化的“魔咒”
文化批评有广义、中义、狭义三种不同的界定。广义的概念是指囊括所有从文化角度来看待文学的研究和批评。美国的弗·杰姆狲《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0页):“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源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
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个群体时所发见的氛围。”这是一种从关系角度来理解的文化。这和一般所说的社会批评完全重合,只是所看待的角度有些区别。
中义的文化批评最典型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是人类文化学批评,它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建立了殖民体系,涉及许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需要建立一种专门的学科来对文化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生理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是相对的概念。
英国的爱德华·泰勒(1832--1917)是人类文化学的创立者。狭义的文化批评也是严格意义的文化批评,主要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一种文学研究方式。包括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及法国学者福柯、罗兰·巴特等一些批评家。此外还可以把女性文学批评和后殖民批评也看成这样一个文学研究思潮的延伸。
《菉竹山房》集中体现了文化是和日常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按威廉姆斯的说法,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个人的文化经验其实是社会整体文化一种反映形式。小说中的二姑姑,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但是,小说却通过她的日常生活写出了日渐没落、腐朽的文化,而我和阿圆则代表着另外一种文化,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与洗染,是二姑姑的对应面,常见电灯、电影洋装书、柏油马路等等就是这种文化的集中体现。
文本所展示的没落、腐朽文化在异域文化的对比中更显古墓般的沉寂、荒唐,文化批判的眼光不能不毒辣。小说通过我和阿圆这个独特的视角看二姑姑显得那样意味深长。
“二姑姑的故事好似一个旧传奇的仿本”、“我脑中的二姑姑家到现在更是模糊得如云如烟。那座阴森敞大的三进大屋,那间摊乱着雨蚀虫蛀的古书的学房,以及后园中的池塘竹木,想起来都如依稀的梦境”、还有丫鬟兰花则更是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没落、荒唐、腐朽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回忆则更显荒诞的色彩。日常生活的精雕细刻,更体现拯救的无力,毒害之深入骨髓。“叔祖的学塾中有个聪明年少的门生,是个三代孤子。因为看见叔祖房里的幛幔,笔套,与一幅大云锦上的刺绣,绣的都是各种姿态的美丽蝴蝶,心里对这绣蝴蝶的人起了羡慕之情:而这绣蝴蝶的姑娘因为听叔祖常常夸说这人,心里自然也早就有了这人”。
二姑姑的“爱情”故事刚开了头,却因“出格、有伤风化”而备受奚落,故事一波三折,少年赴京赶考却意外死亡,二姑姑也要殉情,却被救下,因而能够与少年的亡灵完婚。
“金燕村,就是二姑姑的村;菉竹山房就是二姑姑的家宅。”“阿圆是外乡生长的,从前只在中国山水画上见过的景子,一朝忽然身历其境,欣跃之情自然难言。我一时回想起平日见惯的西式房子,柏油马路,烟囱,工厂等等,也觉得是重入梦境,作了许多缥缈之想。
“屋子高大,阴森,也是和姑姑的人相谐调的。燕子、壁虎、蝙蝠他们亲切地称之为“福公公”、“虎爷爷”、“青姑娘”。何等的和谐,何等的荒凉。这又是何等的气氛,何等的阴森。在对比之下,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故事却更显可贵。因为他们的死承担的是对爱情的坚定不移。
不信鬼,却去扮演鬼。安慰、麻醉自己的同时,也在安慰、麻醉着别人。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能不深思,不能不却探究小说的“原型”生命形态-----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与传说、郭茂倩《玉台新咏》刘兰芝和焦仲卿这些故事背后有多少的合理性东西。
鲁迅先生的“不怕鬼的故事”、《聊斋志异》鬼故事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看不见得凄婉人生和欺世盗名的勾当。鬼背后的“原型”与神话又会是什么。《钟馗捉鬼图》无疑也是一种反讽和嘲弄。嘲弄文化嘲弄文明嘲弄自身。文化已无生机,成为束缚桎梏人性的牢笼。只能一声长叹。“蝴蝶”和“孔雀”东南飞的意象给人灵魂上的进一步麻醉。
人性的异化、扭曲、变形以及文化对美好人性的摧残无疑更是小说表现的另一主题。小说写到大伯娘对侄媳妇的爱也是别有意味的。 “但是阿圆却有点怕我们家乡的老太太。这些老太太——举个例,就如我的大伯娘,她老人家就最喜欢搂阿圆在膝上喊宝宝,亲她的脸,咬她的肉,摩挲她的臂膊”。
这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人喜欢钟情的“二丑”艺术。没有丈夫的爱只能寻求虚无缥缈的爱与寄托。没有异性的爱,只能寄托在后辈的痴恋中,要么特别关爱子女把他视为自己的财产,要么像曹七巧那样摧毁子女的爱情幸福。有这样的文化我们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