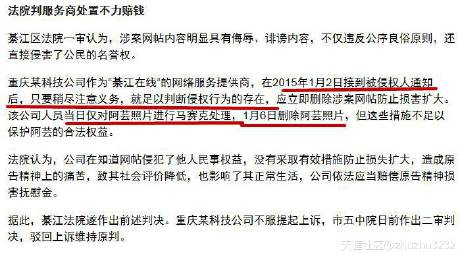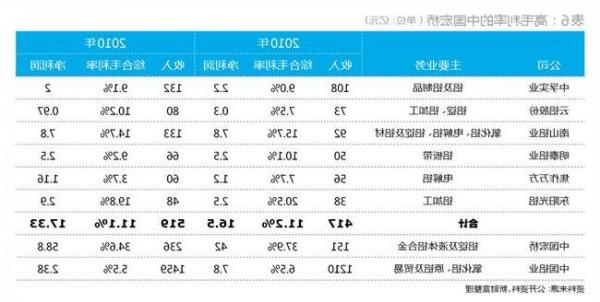画坛昆仑王肇民:百年王肇民学术研讨会纪要
为展示绘画艺术大师王肇民作品风采,“百年王肇民艺术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王肇民先生家属王进女士12日在北京通过电话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展览在北京结束后,还将在广州继续展出。
本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美术馆联合主办,由中国嘉德广州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及广州华艺廊承办。在中国美术馆的展期为8月11日至17日;在广州广东美术馆展期为8月25日至9月9日;在广州华艺廊展期为9月14日至28日。
王肇民被誉为画坛昆仑,其绘画作品,特别是水彩画作品,被美术界赞誉为百年一峰,是一百多年来西方写实主义绘画进入中国后达到成熟的真正标志之一。美术评论界认为,王肇民的水彩画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他的作品告诉人们,一切关于绘画的争执都是徒劳无谓的,举世杰出的绘画作品定与画种及题材无关。他的作品对当下纷纷扬扬的美术界是一种警醒:绘画还是要回到绘画本身。
本次展览精选王肇民先生于上世纪70至90年代创作的水彩静物、风景及肖像人体作品共100幅,并以此展览纪念即将到来的王肇民先生诞辰100周年。
王肇民(1908-2003),安徽萧县人,一生坎坷,先在杭州艺专求学,与李可染同学。在参加“一八艺社”被开除后,又远赴北京,进入北平艺专。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后奔父丧,进入四川,靠当中学教员维持生计。抗战后到武汉,进入武昌艺专任教。
解放后随并校进入中南美专,后一直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直到逝世。他在艺术方面的造诣,一直获得广泛好评。著名美学家迟轲先生评价他的作品是“伟大的风格”。当今众多艺术评论家也认为他是当今中国水彩画第一人。王肇民先生不仅水彩画突出,在素描、速写、水墨以及绘画理论和旧诗方面,同样成就斐然。
7月11日在北京华侨大厦二楼宴会厅举行了“百年王肇民学术研讨会”,会议发言纪要如下——
靳尚宜(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王肇民先生的展览是下个月举行,现在开这样一个研讨会我觉得很重要。
王先生的画我是八十年代初在一个展览里头看到的,看到以后我就很景仰。以前不太熟悉,我以为是油画,后来仔细看是水彩。水彩本身有油画的特点和气质在里面。因为,不管水彩还是油画,都是西方的画种。他整个的对于物体的处理和结构是吸收西方造型里面最基本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块面的方式来表现的。
他的画的特点就是猛一看就是很朴素的,很单纯的,但是,他的画面和其他的很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有很深厚的力量在里头。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因为这种画面的做法是西方造型最基本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初学的时候,研究基础的时候,都要这样做。但是做到他这样一个程度是很难得的、是很不容易的。表面看是很朴素,也普通,但是很精彩,问题就在这儿。
他把这样一种西方最基本的方式单纯化,把琐碎的自然的形概括起来。不仅一路到底,而且整个画面都用个这个变化处理,形成了一个既朴素又单纯,又很有特点,很浑厚的这么一个画面,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是运用水彩的工具,他的效果有油画很厚实的效果,这个又是很不容易的。水彩本来是灵动的、有水分匀染的东西,他没有在那方面的长处出现,而用水彩这样一种工具出现油画很厚重的效果,这个是不容易的。而且它的色彩不是很简单,色彩很含蓄,也很丰富。用单纯的颜色,用水调出来的,没有油画那么复杂,油画可以弄出很复杂。水彩没有,就是用水让它淡下来,水就是这样一种工具,弄成一种很含蓄的、很厚实的、又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王先生了不起,就是在把两种工具特点,它的弱点补充掉而强化,而把油画里头的优点在水彩里头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
另外我以前看他的静物比较多。这次看到他的人物和风景,特别是风景上也非常有意思。还是用同样的体面的方式在风景里头,比如树、水、当然房子造型容易结合,也用这样一种方式体现出来了,也很单纯、很概括,他是同样的风格,也是很有意思的。
当然,人物复杂一点。人物就是一个头像,包括全身、半身的就是一个头像里头同样的方式建构这样一个画面。所以艺术说起来可以很复杂,讲很多道理,但是简单起来啊,艺术也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就是很简单。但是越简单说清楚的越不容易做到,王先生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我对他的研究不是很多,但是我很早在八十年代就注意到王先生的这个特点,我个人很喜欢的。应该说他的这个作品的内在的力量和整体的浑厚的气质是很难得的。所以,他的作品和他的人应该很值得研究。
是怎么从一个很普通的对象和物品里头能够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和内在的表现,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的很好的一个范例。所以现在开他的研讨会,包括展览,而使我们美术界更加关注这个老画家,从里头吸取经验,为后人提供一些很宝贵的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邵大箴(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
王肇民先生我接触比较少。1993年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水彩画展并举行研讨会,那时见到了他。听他谈他的水彩画观念和他的艺术见解,非常有收获。当时他在北京的展览,很成功,反响很大,学术讨论很热烈。
我觉得王肇民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也是世界写实派的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真正的写实艺术追求的不是形式的写实,而是本质的写实。就是艺术家通过描写客观世界同时来描写自己。西方好的写实主义也是如此,它不光是讲究形式的写实美感。在中国,像王肇民先生的水彩画这样深入表现物象本质是不多的。当时在1993年的讨论会上,很多油画家、国画家都参了与讨论,他们都认为王先生这种画法太绝妙了。这在二十世纪,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水彩是一个画种,英国透明水彩画在世界上享有声誉,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但水彩画的表现方法可以多种多样,王肇民在英国水彩画之外另辟蹊径,用写实厚涂法,强调结构美,透过表现物象的形似表现其神韵,表现一种精神力量。他的水彩画有一种宏大、深沉的美感。
王先生非常热爱生活、热爱艺术。也希望用自己的艺术参与到更多社会文化的大的运动之中,他是有这种愿望的,这是看得出来的。不过,王先生始终对左的理论是很警觉的,而且很反感。他说有人批评他画的水彩画,没有主题性创作,还认为他画的死,等等。
他说,我们过分的强调主题、题材的重要性,忽视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对中国艺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他说他吃过很多苦头,有人挥舞辩证法的大棒对他进行压制和批判,他说那是假马克思主义、伪辩证法。王肇民先生是顶着左的压力走过来的。他的为人和艺术都表现出反潮流的精神。当然,王肇民先生的才能和智慧因为受到文艺界左的理论的压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王肇民不是画主旋律的题材,但是他的精神是主旋律。他的文化精神,作品的艺术精神有一种力量在里面,这种写实的艺术里面有精神、有力量。
我觉得王肇民先生艺术创作的意义就在这里。
王肇民在美术界被边缘化了,是一个“边缘人物”。但是他是一位有思考、有独立见解的艺术家,是对艺术规律有深刻思考的人。我最佩服广东两个人,一个是王肇民,一个是廖冰兄。他们拥护马列、辩证唯物主义。他们从新时代、新生活中获得巨大的鼓舞力量。但是他对我们体制中“左”的东西,妨碍人个性健康、自由发展的东西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们的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刘曦林(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我来之前翻看了一些我过去积累的一点关于王肇民先生的资料,有几点感受。今天又看了画、看了诗,看了他的论述,感到非常地激动。第一点,他是北平新兴木刻的播火者。我前不久刚刚做完了《北京美术志》,另外又参加了《二十世纪北京绘画史》的写作。
王肇民先生和北京是有关系的,他曾是北京现代木刻界的热血青年。肇民先生和可染先生当年同在杭州艺专,他们都因为参加“一八艺社”被视为“左倾分子”,王肇民被开除,李可染被迫退学会徐州。
林风眠先生也保不住他们,因此“文革”期间给林风眠先生加上了迫害进步青年的罪状。实际上林风眠先生通过各种方法如写手札把他们转到了其它学校,王肇民先生就这样到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即原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当时得到了北京木刻家王青芳的支持。
刚到北平不久,1932年春天,王肇民就发起成立了“北平木刻研究会”,这个北平木刻研究会是王肇民先生负责的,还有杨澹生、沈福文、汪占非等人。这四个人都是杭州“一八艺社”的成员。1932年4月,他又与胡蛮、李苦禅等人,成立了“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1933年4月,他在西长安街艺文中学,就是王青芳先生执教的那个中学,办了“北平、上海木刻作品联展”。
1933年7月又办了第二次会员作品展,这个展览后又移去天津。1933年8月他们遭到搜捕,详细情况还有待于深入的了解。通过这些史实来看他是北平新木刻运动的播火者。王肇民先生1933年被搜捕之后北平木刻并没有就此熄火,1934年后又成立了平津木刻研究会,1935年他们在太庙举办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
这些事情已经载入了《北京美术志》和《二十世纪北京绘画史》。王肇民应该是北京美术界不应该忘怀的前辈,一个新兴木刻的播火者,他是北京最早的木刻社团的发起者。
从此之后北京的新兴木刻开始兴旺起来,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青芳先生本身是画中国画的,在他们的鼓动下拿起木刻刀,号称“万版楼主”,独创了一路有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以线为主的木刻新风。
我想在北京开“百年王肇民学术研讨会”不应该忘记这一点。而且希望在座的青年史论家能再查一下史料,把这段历史进一步丰富、充实起来。也希望邹师母能够再补充一下。
第二点感受就是:我认为他是20世纪中国水彩画坛艺术品格最高或者是最高的作者之一。他有这么几个特点,给我印象特别深。一是他的水彩画最有力度、最具体量感、浑厚感。这个类如叶浅予先生对速写的要求,稳、准、恨,不犹豫、胸有成竹。
他曾经说过我的水彩靠的就是素描,他说过“形是一切”。也就是说他在杭州艺专从克罗多教授学习素描的时候是画得很坚实的一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他早期的素描作品,不知道有没有留下的。如果从他的水彩画风和个性显现来推测,他画的素描应该是坚实的,粗犷的,或是像可染先生画的那样黑乎乎的。
关于可染先生画素描有一个故事:克罗多老师看到他画的素描很黑,就摸摸他的额头说,这个青年人是不是发烧了,感冒了?后来一了解中国人喜欢黑,喜欢墨,就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王先生和可染先生师从同一个教授,从素描的基础和形的基础来讲,当然不一定是我们现在先把铅笔削尖了画的这种画法。那时候的素描可能是非常浑厚有力的,那种稳、准、狠,毫不犹豫的表现和胸有成竹的造型意识甚至和他个人的体质、体貌是同构的。所以他主张“人当物画,物当人画”,这也是中国的美学传统。
二是,我感到王肇民的画非常的纯美,他并不过多地追求色阶的细微变化,色彩有变化但整体色调特别的纯。我们中国美术馆藏了一部分王肇民先生的作品,经常拿出来的有两张画,一张是《杜鹃花》,花是粉色的,后面衬了一个棕红色的背景,是红调子。还有一张就是《珠江小艇》,水边上一组小船,码头画得很简练,就是用枯笔扫了一些淡黄色,运用了大量的空白。因为他说过色阶越少越有力度,纯度和力度是相通的。
另外一点,他的水彩也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我刚才讲到中国美术馆藏的《珠江小艇》就运用了大量的空白,大量的线,非常的有力。同时还能感到他的画包含了现代构成意识。我记得1985年在武汉看他个展的时候,他画了很多的苹果,其中有一张是《六个绿苹果》,当时我还勾勒了一个草图,把他的结构方式、六个苹果的摆布和桌案的角度之间的关系记下来,我认为处理得非常好。
他曾经非常明确地说过:“我是油画的色彩,国画的笔法”来画。今天我看了他的书法,感到吃惊,如此苍老、厚朴、温敦,非常整肃,这种力度、厚度、量感,我想和他的水彩画是有同构关系的。
第四点,通过这些最终看出的是他的人格,他非常具有一种人格的自我的表现力度。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既尊重造型、色彩,也讲究中国画的味道,但是最后要由他作主,他就是上帝,他就是独裁。他说:“三军之灾,犹豫最大。
作画也和作战一样,既要善谋,也要善断,面对现实,不能犹豫,犹豫是非画坏不可的。在观察对象时,要客观,要冷静,要尽可能给对象做一个恰当的总结。在处理画面时,要灵活,要激动,要独裁,要我就是上帝!”这非常强烈地体现了他的主观能动意识和人格魅力。
尚辉(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美术》主编):
我觉得20世纪中国美术史有一些现象,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水彩画毫无疑问是20世纪中国人接受西方绘画最普遍也是最早的一个画种。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姜丹书、吕凤子等人在20世纪初的水彩画作品,当时他们就学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那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接受西画学习的起点。
前不久,我去宜兴的“徐悲鸿纪念馆”,有幸看到了徐悲鸿在出国留学前的水彩画作品。很显然,水彩画应该是中国人最能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一种西洋绘画。
大家都知道,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水彩和炭笔素描的联姻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擦笔水彩”,这体现了水彩画舶来之后的快速本土化过程。客观地说,水彩画能够被中国人很快接受,存在着一个文化心理上的优势。这就是水彩画的水性和中国画的水墨能够形成异质同构的关系;不仅如此,水彩画的笔还可以发挥和毛笔一样的“写”的精神。
因此,我们看到几乎整个20世纪水彩画的发展,都借鉴了中国画对于“水”和“笔”的运用而形成的审美特征,比如,强调用水的“灵动”和用笔的“洒脱”,可以说“灵动”“洒脱”“秀雅”“润泽”也几乎是一个世纪中国水彩画的整体审美特征与审美追求。
而且,江南是中国水彩画的大本营,哈定、哈琼文、李剑晨、杨廷宝、杨云龙、范保文等都是20世纪中国水彩画的大家,影响了几代人。
这个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作为舶来品的水彩画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被中国画的审美特征同化的现象。其问题是,近百年来的水彩画实践优化了“水性”而遮蔽了“彩性”。
另一个现象是20世纪末,到了1999年第九届全国美展的时候,水彩画的整体面目发生的一次颠覆。这次大的变革就是由原来注重水彩“水性”的发挥,变成对水彩“彩性”的拓展。水彩画原来注重的“水性”而形成的灵动、洒脱、秀丽、婉约的审美特征,突然在九届美展中呈现出整体性的颠覆,水彩画的“彩性”具有了油画那样浓烈而坚实的造型强度。
那几乎是对水彩画色彩的丰富性与坚实性的深入探索,虽然有些作品过于追求油画的彩色张力,但毫无疑问,干笔水彩与多重肌理语言的运用着实展现了水彩画一个世纪以来被遮蔽了的色彩表现魅力。
当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整个广东地区在水彩画“彩性”语言方面显示出的整体实力,水彩画的一些主要奖项也几乎花落广东。这个现象概括地说,就是水彩画的中心由原来的江、浙、沪一下子转移到广东、山东,甚至东北地区,那么发生这个现象的缘由是什么呢?
今天在这里召开百年王肇民学术研讨会,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阅读五肇民先生的水彩画作品、回顾王肇民先生的水彩画探索之路。我们突然醒悟到广东水彩画的发展与王肇民先生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教育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广州水彩画在20世纪末的异军突起,中国水彩画在20世纪末因强调“彩性”张力而发生的价值判断的重大转换,都肇始于王肇民先生。
王肇民的水彩画,应该说是我们今天能够接受并更能构成审美认同感的一种水彩画。刚才看到郎绍君先生给他的评价是“小画种画出了高品位,大风格”。
这个评价非常到位、也非常准确。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水彩画是“小画种”,便于户外写生,长于画小风景,捕获人物动态神情,很难提升到艺术创作的深度上,更难以进行主题性创作体现宏大的现实与历史主题。但当我们看到王肇民的作品时,恰恰产生了相反的认识,改变了我们对水彩画抱有的成见,这说明了王肇民艺术追求和艺术风格的不同凡响和时代的前瞻性。
马书林(中国美术馆副馆长):
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我与王肇民先生素未谋面,也不曾有过任何形式的接触。只是我在鲁美附中做校长时,恰逢王先生的女儿王季华在广美附中做校长,算是有一点儿间接的工作情分。虽然很遗憾的与先生素昧平生,但做为晚辈我十分仰慕先生的艺术作品。
我对王先生的水彩画作品并不陌生,以往就因为喜欢而比较关注。尤其是王先生的水彩静物就更为欣赏,甚至可以说是敬仰。因而我来中国美术馆工作不长的时间就与典藏部的同志主动去广州美院登门拜访王肇民先生的子女——王季华和王越,希望中国美术馆能够多多收藏王肇民先生的作品。
来为中国美术史添写重要的一笔,因为我认为王肇民先生的绘画作品尤其是水彩静物画毫无疑问在当今中国美术史应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对21世纪的中国美术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王先生也是当之无愧的可誉为中国水彩画最高成就者之一。
王先生作品所表现的主题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反映主旋律的或历史或现实的重大题材,我们看到的王先生的作品大都是静物、花卉等生活中极平常物品的水彩画,但王先生的作品小中见大,用轻松的笔触和谐的色调表现日常普通的现实生活,朴实无华的画风使人容易产生共鸣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反倒使人印象深刻。
作品毫不张扬的默默的散发着平实的美,静寂的美,深沉的美,厚重的美,单纯的美,整体的美,强烈的美。
其实我们都知道越是普通的事物越难表现,因为每个读画的人都熟知生活原型,象与不象,对与错,都会有认知。但王先生的作品中是该表现的一笔不省,不该表现的一笔不多,从生活中来到画中去,轻松的逾越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鸿沟。
邹佩珠女士(李可染的夫人):
我没有什么准备。但是王肇民同李可染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不能随便同你们谈一些学术的问题,我想到什么就谈些什么。
我看前面写的有一八艺社,西湖艺术院什么的。这个就是李可染同王肇民是同学。不光是同学,李可染是徐州的,王肇民是萧县的,也就是徐州的。从前萧县也属于徐州府,徐州今天划到江苏,以前也划过安徽、山东。所以他们既是老乡,又是同学。
这两个人个性都很强,要谈问题的话,谁也不能说服谁。两个人的性格都很强,你别看李可染平时不说话,你要谈学术问题,他绝对不会让,王肇民呢?他也不会让。我经常见他们两个在家里说话,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个反映了什么呢?这个就反映了他们在学生时代讨论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么直率。因为,他们两位都很有成就。他们这个成就也反映了他们的个性。所以两个人都是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追求。不光是他,我们还知道成都的沈福文,还有西安美院的王占飞。
这几个人都是性格都很特别。因此都各有各的成就。所以我对他们都很敬佩。刚才,我一进屋就看很多静物,有很多苹果。我说,这里面有的苹果就是我给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开放,美国画家张尚普,他偷偷地把美国的几个苹果摆在箱子里面,要检查的话是不让他们带的,他见李可染的时候就把这个苹果送给我了,正好王肇民同志来北京写生,而且住在我们家。
他好画画,随时随地都要画画的,我就把所有的苹果都给了他,我们一个都没有舍得吃,就是那个最紫颜色的。
后来我见到他,他说:你晓得吗?拿到这个苹果回到广州,一直画到烂的时候。他还舍不得丢,烂了他就画烂了的样子。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就是他一种执著的追求艺术的一种精神。这是同李可染一样的,李可染找到一个构图,他反复画,十遍、二十遍,他都画,画到他自己满意为止。今天看起来他们这种精神太厉害了。
刚才我见了郎绍君同志,我说这些作品,就如同金子!现在清华科学园说什么钻石工程,我看王肇民的画就是金子,是钻石,不仅仅是画。太精粹了!精粹在哪里?就是刘曦林同志刚才将的,他的东西就像我们杂技演员的稳、准、狠!
你们去看他的作品没有一个犹豫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他探讨钻研的结果。刚才有同志说,他是干擦什么的。我看没有一点干擦的。那一笔下去非常肯定,不是擦擦弄弄。当然了,李可染的中国画里面有积墨法,这笔画了以后再加几点。
积墨法的原因,就是要把山画得厚重,同古人有所不同。李可染学习了王老的东西,既要有厚重的东西,还要同我们时代的精神结合,强烈、光亮,叫你们看了以后有一种精神。王老的这个东西,我看没有一点犹豫,好多同志谈到他的那个整体感。
你们去仔细看,没有一点渣子,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他有高度的修养,没有这个修养,做不到。我看的画太多了。家里的人说,你岁数那么大了还老去参加什么画展,我就是要去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功夫下在哪里?是不是像二十世纪的一些老人下的功夫?浙江美院七十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改成中国美院吧。
我参观了他们附中的时候他们正好在研究,在我们这个时代二十世纪还能不能出那么多的大师。
后来我一看,他们那个附中的素描非常好。我说,有希望。后来我又参观了他们的教室,我心里就打折扣了。为什么?我看他们的教室里面画的是什么?画的是速写,生活的速写。他那个生活速写是一笔一笔凑起来的。
这样的话,将来要上升到大师,那就难了。为什么?你画速写就是抓他的精神,你抓不到那个精神,你画什么?我们艺术是干什么的?我们艺术就是要反映我们心灵里面、客观事物里面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精神。用李可染说的话,为什么改革中国画的时候,他有两句话“可贵者胆,所要者魂”。
这个魂,就是艺术的价值。你给予别人的影响力问题。你没有这个了,还有什么价值呢?只是画物,画东西,好像是枝枝节节。你在生活里理解了什么?没有抓到。
你看,王老画的静物,静物里面有神,有精神,有他的性格。他的东西非常单纯。你们再去看看我们好多的中国画里面,虽然一张很好的画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败笔,有很多不应该有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李可染同王老他们都有一个精神,要把艺术追求到最高境界,才会对社会起到真正的作用。
李可染所以有这个,因为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在家乡听过一次堂会,全国的京剧界里最有名的人都到徐州去,为一家有钱人的母亲做寿,演了一个晚上一个白天,李可染在看,京剧界最精粹的都集中在徐州演出。其中听到程砚秋的唱腔,那个婉转呀,他说我多少日子都忘不了。这个就是他一辈子追求的艺术。不到这个高点,起不了更大的作用。
当然了我们的艺术是逐步地成长的。但是,作为他们两位来说,我们看到他,他的境界,艺术的境界不管是人品、画品都在自我的追求。从他的诗词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达。我一进来看到王老成为教授是1981年,非常诧异。
这个就是刚才刘曦林同志没有直截了当说的,就是说,他是在坎坷中成长的。那一年李可染的作品到广州去展览的时候,他没有接到请柬,他好激动的,后来就到了宾馆里找到我,同我聊了好半天,最后,李可染的画展快完的时候,我又去回访他。
他们两个是真正的好同学、好朋友、好战友。我去了以后,他可能有意的布置了一张中国画,画的是什么?画的是猫头鹰。猫头鹰是晚上出动的,因此他的背景很黑,我说你比李可染还要黑。他们到最后,还是黑到一块儿了。
他们同学的时候,在徐州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倒霉也倒霉在一起。抗日战争,王肇民还有倪小渔,他们的东西都摆在李可染那儿。他哥哥怕抗日战争时候的战火,就把一箱子他们三人早期的作品都沉到了河底。这就是前面有同志说看不到王肇民早期作品的原因,他早期的作品都沉河底了。
杨小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系主任):
今天能为我的老师王肇民开研讨会,很高兴。在座的都是国内一流的美术理论家,相信他们对王先生的成就已有定评。我今天打算说一些与亲身经历有关的事。梁江我学兄,我们都是广州美院油画系毕业的,都受过王先生的教诲。我是广州美院文革后油画系的第一届学生,二年级王先生教了我们一年素描,之后他就正式退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班王先生正式退休前的最后一届学生,虽然他后来还一直在教学。
现在想起来,当年我在广州美院油画系读书时,算不上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学生,学画画当中碰到很多困惑,希望能够得到更深入的解释。我后来之所以从事美术理论,当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想给自己解惑。当时有很多事情不太理解。比如有人说,你的画感觉不太对。我听了就很迷惑,不知道什么叫“感觉不太对”。我想得到更具体的答案。还有人常说要“到位”,我也不知道这“到位”具体指什么。
回想当年读油画系,对王先生的教学方式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年以后,我检索自己当年所记,才发现当时向王先生问了很多幼稚的问题,而他都做了精彩的回答。他的回答有不少都在《画语拾零》中写出来了,不过,对比成文的画论,我觉得还是他在课堂上的回答更直接。
回想起来,王先生在教学上是很有特点的,而且他终其一生,都是美术教育家。到现在为止,作为教育家的王肇民,还很少研究。以后我想还是会做相应的研究的。作为老师的王肇民,他有几个特点在美院的老师当中是很少见的。
第一,王先生每天肯定在7时45分准时到达课室,从来没有迟到过,也从来没有一个星期只来一、两天这样的现象。他告诉我们:“你们跟我学画画,第一条就是要准时上课准时下课。”他自己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甚至包括课间休息15分钟,他也认真地告诉班长,说要去图书馆15分钟。果然,15分钟后他就回来了。所以,他上课的一年,是我们在美院的宽松学习环境里最紧张的一年。
第二,王先生第一天上课就对我们说:“老师重在言传身教,你们画多少张我就画多少张。”我们第一堂课画的是石膏,我们画一张,他也果然画一张。当时不觉得怎么样,现在想起来,才知道这非常的了不起。王先生告诉我们说,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跟学生一起画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我现在翻看他的画册,尤其是素描画册,有一部分太熟悉了,因为是一起画的缘故。
第三,王先生上课的时候非常反对摆模特。我们过去总是有一种传统,就是想把模特摆得优美一些,好画一些。王先生却说,摆模特儿干什么?我们是学画画的,又不是学摆模特的,那么优美的姿势,对画画没太大用处。王先生的画是有反优美倾向的,这一点甚至贯彻到他的教学当中。
第四,王先生在教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恐怕是他所强调的“读画”。我记得我们上课不久,有一次他问我们:“你们去图书馆吗?”我们说:“去啊,去那儿看画册。”那个年代画册刚刚开始对学生开放,可以从中读到不少世界名画的印刷品。
他接着问:“你们是怎么看的?”我们说:“就是借一堆画册过来翻看啊。”他又说:“你们能不能一晚上只看一本画册?”后来又补充说一晚上只看一幅画。后来又说一周只看一幅画。他提醒我们注意他到图书馆的情况。
这样我们去图书馆时就真的注意起王先生来了。我们常常见到他呆在图书馆里,翻开一本画册,放在桌子的小架子,然后一动不动地看上半天。如何才能做到一周只看一幅画,我去问王老师,他告诉我要把一张画分开看,今天晚上看色彩,明天晚上看构图,后天晚上看构思,等等。此后,我真的就养成了读画的习惯,这恐怕和王先生的教诲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