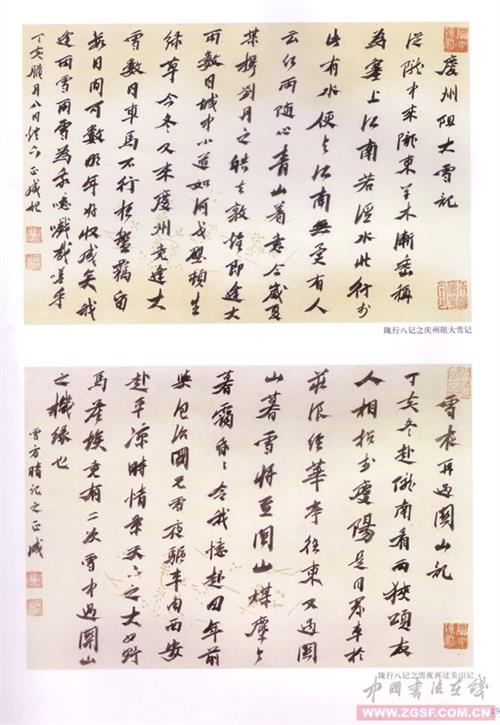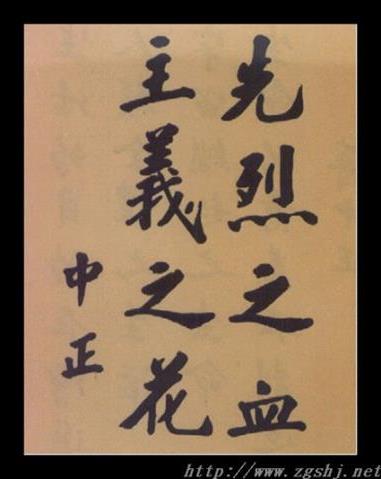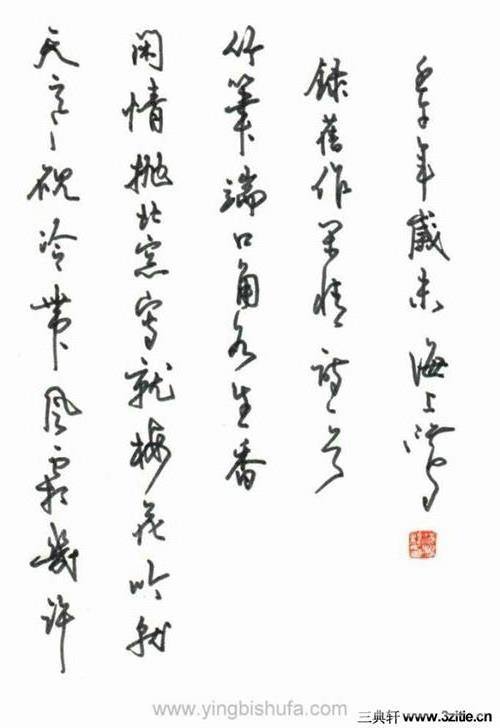中国书法简史叶培贵 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源头、母体和通脉
以往各种版本的《中国书法史》,基本上只是“汉字毛笔书法史”。说什么“中国的书法艺术不过是拿毛笔蘸墨汁书写汉字而已”(见叶培贵《中国书法简史·绪论》),完全无视更比毛笔书法源远流长的“汉字”硬笔书法。这种荒谬的观念可以归结为四个字:“书唯毛笔”。
“书唯毛笔”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西汉戴德《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载,周初,姜子牙述《丹书》之言,武王闻之,退而作《笔铭》云:“豪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所谓“豪毛茂茂”,所指显为毛笔。
但遍检先秦文籍,皆不载西武王有“豪毛茂茂”之铭。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指出:“《大戴礼》遗逸之书,文多假托,不立学官,世无传者。”(见《毛诗注疏》卷十六《大雅·灵台·序》孔颖达《疏》);宋·王应麟亦指出《武王践阼篇》“谶纬不经之言,君子无取焉”(王应麟《武王践阼篇集解》);明·王世贞更指出,“‘毫毛茂茂’是蒙恬以后事也,必非太公作”(王世贞《弁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艺苑卮言(二)》)。
宋·易简《文房四谱》卷一曾引《太公阴谋》书中载此《笔铭》。
《太公阴谋》即《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所载《太公》百三十七篇中的《谋》八十一篇。班固早已指出此书“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从知“豪毛茂茂”之铭,当为秦汉以来方士托古之作,虚妄无稽,不足取信。
后世多不知古用硬笔写字的实况,曾有据此《笔铭》而谓西周武王时已有毛笔,于是推想西周时已用毛笔写画。清末发现甲骨文,见甲骨片上偶有朱、墨色书字,学者囿于“书唯毛笔”的习惯观念,臆断为毛笔所写,把毛笔写字的历史又提前到殷商时代。稍后,发现新石器时代彩陶,考古家又臆断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也是用毛笔绘制而成。于是将使用毛笔的历史更提前到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将“书唯毛笔”观念发展到“书、画唯毛笔”,大大强化了这一错误观念。
要破除中国书法史即“毛笔书法史”的错误观念,必须从写绘源头上进行清理:一要辨明新石器时代素陶刻符及彩陶图案的刻划或绘画工具是不是毛笔?二要辨明甲骨文、大篆(包括钟鼎文、石鼓文、剑戈及货币铸文)、古隶(包括盟书、长沙帛书及战国简牍)、秦篆、秦隶(秦简)等先秦古字的刻划、书写工具,从而判明上古诸种书体的属性。对上述两大关键问题,我在《敦煌古代硬笔书法 附编》中已有详论。但“书唯毛笔”的错误观念已经流行两千余年,偏见经久,凝为偏执,而余说面世未久,多有不甚知闻,愿借此机会,再作申说。
一、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的刻、画工具是硬笔,不是毛笔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纹饰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刻划符号及纹饰,一类是彩绘图案。其制作工具大同小异,须分别言之。
远古陶器,先有素陶而无纹饰,后乃渐有刻符(插图1)及刻划图案(插图2,插图3,插图4)
刻符及刻划图案悉皆阴文,刻线凹入陶胎,无疑为坚挺锐利的工具所为。在尚无铜铁的原始时代,凡是可以用来划道显痕的硬物——如指甲、竹签、木锥、鱼刺、角尖、骨锥、骨针、石片、石锥之类,都可以用来进行刻划。这类用来进行刻划地坚硬工具,如果可以视为原始之笔的话,无疑只能称为“硬笔”。原始陶器上的刻符及刻纹,就是用这种“硬笔”直接刻划出来的。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世人: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符及刻绘,尽属硬笔作品,与毛笔全无瓜葛。
继此之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进一步出现彩色纹饰图案。前人对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彩色纹饰图案,一概释为毛笔所绘。而笔者经过反复研究,却发现原始彩陶图案纹饰属硬笔蘸色绘制而成的“硬笔画”,一反前人旧说。
概而言之,原始彩陶纹饰图案皆属平面画,尚未出现三维立体画。而平面画之黑、白、红、赭涂色,仅能显示颜色的差别及彩色的对比,不足显示所画为何物。若要显示所画为何物,决定性环节不在涂色,而在于勾勒所画之物的平面轮廓。脱离式样轮廓的涂色,除了在视觉上造成色块感觉之外,不足让“感觉”升华为某种特定的物形和式样。所以不在特定轮廓内的涂色不堪称为绘画,只能称作涂抹。由此可以断言,新石器时代平面图的制作,最基本的要素和决定性的工序,乃是勾勒轮廓,可以简称为“勾廓”。至于涂色,则是从属于勾勒轮廓的辅助性手段。上举河姆渡文化陶钵上刻划的猪纹图案(见插图4),只刻划出猪的形体轮廓,并不涂色,已足以显示出所画为猪。这件实物,足以说明勾勒轮廓在原始彩陶图案制作上至为重要的意义。
新石器彩陶图案的勾廓,是用线条作成的。而线条一般细而匀适,不见类似毛笔之类的软笔无意间出现的提捺、抖颤之迹。由此断定勾廓线条必是硬笔所画。
我们又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案也有融勾廓与涂色为一体的手法,如画线、画圆、画方之类,只见黑色或其它颜色的线条或色块,色线或色块外围并无勾廓。这一现象,似乎打破了前面所说勾勒物体轮廓为制作原始彩陶图案“最基本的要素和决定性的工序”的说法,其实,这不过是按照预想的造型将勾廓与涂色合而为一,寓造型于涂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