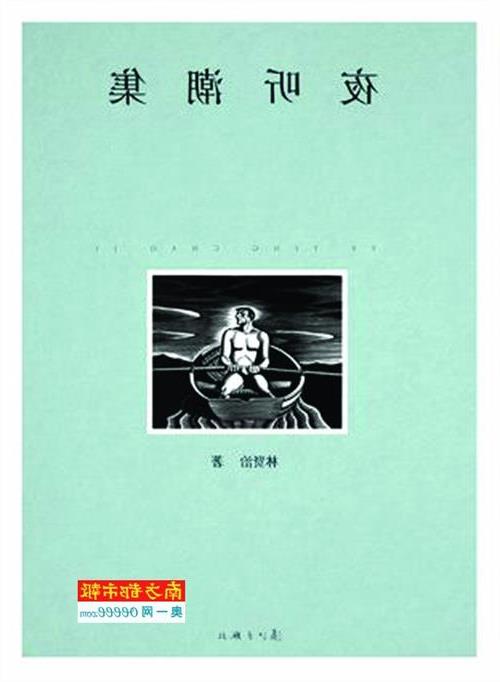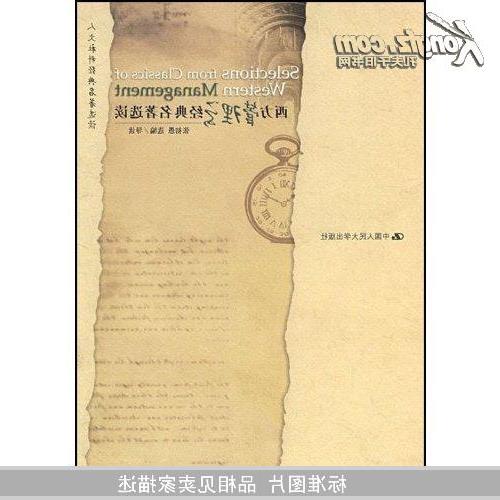林贤治语录 读林贤治的长篇随笔《革命寻思录》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海外,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止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结果立刻引起章太炎的不满,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多年后,才首次出现全面系统的驳论———林贤治的长篇随笔《革命寻思录》。
有评论称:“在告别革命论被民众普遍接受的二十一世纪,《革命寻思录》是第一本关于革命的书。”说这是二十一世纪第一本关于革命的书,当之无愧。可说告别革命论被普遍接受,尚待分辨。或许在社会心理层面上,这一主张得到了所谓大多数人的认同,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的声音时有耳闻。然而,各方对革命含义的理解并不一样,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底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理由是什么?革命的方式是什么?革命还会不会发生?这些核心的问题,直到林贤治的《革命寻思录》,才有完整的论述。
林贤治的书名用“寻思录”,而不是“反思录”,或“沉思录”,是非常准确的。“沉思”是一个中性的词,代表作者中立的态度;“反思”是回头、反过来思考的意思,是告别论者的立场;而“寻思”带有寻找、探求、探索、追求之意,正如后记所言:本书的“目的无非在于辩护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这部三十万言的大书,虽采用随笔的形式,却有着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架构。作者首先从“词源学”和“本体论”上阐释“革命何为”。林贤治把革命与自由联系起来,自由是革命的灵魂,“革命的”即是“自由的”。书上多次醒目地引用孔多塞的话:“‘革命的’一词仅适用于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
革命是手段,不是目的,自由才是目的,这个道理是有必要辨明的。尤其是在我们多年接受的革命教育中,似乎没有人强调这一点。记得多年前有一位演说家,在全国各地的巡回演说中,引用革命诗人殷夫翻译的革命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竟然将“若为自由故”改为“若为革命故”,可见那些以革命自居者,是避讳自由的。林贤治重申革命与自由的关系,尤其发人深省。
林贤治说:“我始终认为,真正的革命是解放人的,是自由的化身。”在他看来,自由一词的本义不难理解,倒是一些学者将其弄迷糊了。追求自由,就是反对强制,反对奴役。革命之路,是通向自由之路,而不是通向奴役之路。所以,只有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则,把手段当成目的,也发生了马克思所谓的“异化”。
世界上所有革命的起源,无论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以自由反抗暴政,但结果不尽相同。这取决于特定的环境、形势和文化传统,更直接的原因还在于革命者是否违背了革命的初衷,也即自由是否得到尊重。
人民有义务也有权利,如果只要求尽义务而漠视权利,那就只有奴役,没有自由,根本上违背了革命的宗旨。为此,林贤治特别强调“人民主权”的概念,强调人民始终保留至尊无上的权利。
所谓人民主权,是相对于国家主权而言的。在林贤治看来,许多情况下是国家主权至上。“主权属于国家,人民却是赤身裸体”,这种现象是值得警惕的。当然,关于人民,关于国家,也会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例如,人民是个体概念的还是集体概念的,国家是民族概念的还是政府概念的。林贤治却无意陷入这些琐屑的争论,他通过对世界革命的宏观考察,指出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这就是国家,如果不能保障其人民的自由,革命就会不期而至。
争取自由方式有许多种,有革命,也有改革。革命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有暴力,也有非暴力。在这些问题上,林贤治的观点旗帜鲜明。他认为,一些人主张改革,其实是放弃人民主权,而强化国家主权。因为改革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而国家又不会完全放弃现有制度和既得利益,寄希望于统治者自觉主动地进行一场全面彻底的改革,只能是一种幻觉。因此,与其说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毋宁反过来说,革命是改革的替代物。也就是说,当改革宣告无效时,革命自然成了替代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革命成了自由得以实现的唯一理由”。
暴力的问题,历来是反对革命的借口。告别革命论者表示特别憎恶暴力,康有为说革命残酷,伯克说革命恐怖,都是这个意思。林贤治则主张,不可无区别地一味谴责暴力,而是要揭开暴力机制的复杂性。他指出,反对暴力者,往往只是借反暴力而反革命罢了。他们反对来自人民的暴力,却能容忍来自国家的暴力,显然是有失他们自诩的公正。革命暴力的合法性,在于它根源于人民主权。革命暴力的正当性,是同人民反抗的合法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探讨革命是否终结的问题,这似乎并不复杂。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我们一些学者也以“告别革命”作为呼应。然而,福山的论点,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他的历史终结论,如果可以理解为革命终结论的话,那也是就西方社会而言。他认为,自由被认为是全人类的目标,而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体,在世界各地涌现出它的合法性,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但由于并非全世界的国家都已达到自由民主,他又认为,“历史”持续在世界一些不自由的地区进行着。福山还指出,国家主义这种政治力量会消退,因为自由民主是“人性的需要”。可见,历史终结论的理念,与告别革命论并不一致。
林贤治真正要驳斥的,并非历史终结论,而是告别革命论。他认为革命不能轻言“告别”,也不能妄加预测。革命的发生,与之相关的政体模型是带根本性的。关于人民主权的思想观念,自进入新世纪之后,不是离人们更远了,而是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最终,不是人民适应统治形式,而是统治形式适应人民。由此观之,林贤治为革命辩护,实际上就是为人民辩护,为自由辩护。
托克维尔在法国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写信给在英国在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林贤治出版了《革命寻思录》,也可以说,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爱读这本书的,恐怕也只有自由的朋友们。至于人数是否屈指可数,那就要看当下有多少人真心地热爱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