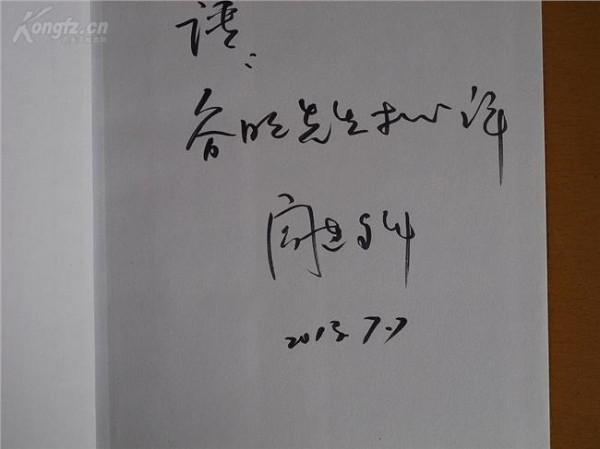阎连科恐惧 阎连科:对死亡的恐惧
我内心一直充斥着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问题。
我在河南农村长大,小时候经历了太多的神秘。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想起一件事情,是少年时去深山区我姑姑家发生的。姑姑家门口有一棵几个人都抱不过来的皂角树,关于这棵树,有很多神秘传说。
有一天,传说变成了不可思议的现实。午夜时刻,听完一个老人讲故事,我和哥哥一起回家。路过皂角树下时,一块碗大的石头从树上轰隆落在一旁的草房上,紧接着是第二块、第三块。
这些石头从黑暗的树上滚落到我们身边,我和哥哥撒腿就跑,还可以感到石头在后边追着我们滚动。后来,姑父提着马灯去找,没有发现任何痕迹。但我和哥哥都确定这不是幻觉。
这些经历,也许对我作品中的“神实主义”会有些影响。
我很少描述光明与团圆,因为我从没相信过任何大的理想和图景。
有人问,为什么你的小说都是关于权力、饥饿、革命和性?因为这些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记忆。其实在我的小说里,更多的是革命、推翻或打碎,我很少描述关于建立新世界的光明与团圆。
这是因为现实中,我从没相信过任何大的理想和图景。你看,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来源于一段又一段的革命。没有经历过的人大约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一切语言方式、行为方式,都跟当年的革命密切相关。
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告别革命。
知青下乡时,我才十几岁。今天我们谈论知青的悲剧时,没有看到另一群人的悲剧——农民。知青下乡是一代人的悲剧,但农民是世世代代的悲剧。我们要承认这个客观的不对等。《我与父辈》出版后,里面关于知青的看法引起争议,但我只是想说我所看到的和体验的。
那时候,农村真的太苦了,我一门心思想当兵,想进城,想远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后来,我如愿进了军队。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我对权力的认识比别人更为深刻和复杂。
在写作最初那几年,对究竟这一生是写作还是去当官,我有过惶惑。
有一天,军长出外学习回来,他在家属区走来走去,黄昏时对身后的参谋交代了几句话。次日凌晨,军机关的人发现家属区所有的鸡、鸭、鹅都被毒死在院子里。每个军官都沉默如死,然而出操时,每个人又都向军长敬礼和微笑。
当然,军长毒死家禽是因为他想让军营更像个军营,而不是人的生活区。但这桩事情太过残酷了,它使我突然觉得权力的无意义。因此,我决定还是长久、一生都回到文字的温暖中,我在写作中对权力也有了一种新的审视和打量。
我想,上世纪80年代是我们国家巨大的一个转折点,充满理想和浪漫。很多人怀念80年代,是每个人都在怀念青春和理想。每个人都在美化自己的青春时代。
现在的我只想平静地过日子。每天六七点起床,写作两个小时。写作之余,我到大街上打眼一看,每个人都患了集体的精神匆忙症,脚不沾地地往前奔,无非就是到前面喝杯咖啡。
这也是我在《炸裂志》里所描绘的人们:每个人都患了某种精神病,都被无意识的匆忙所控制。如同人人要赶车、人人都害怕追不上列车,但这趟列车要去哪,谁也不知道。也如我们走到一个精神病院,所有人都处于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里。
我的写作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被禁、被争议,好像是走在一条没有光的胡同里。但我相信,对现实的讽刺和批评,其实也是一种正能量。就像医生告诉你生了病,你能说这个医生是负能量的人吗?为什么要把正和负分得那么明白呢?
2011年,我在北京丰台区花乡世界名园小区(711号园)过了一段梦一样的日子。不过也真是一梦而已了,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都来不及留下,那里已经被拆光了。
我自认非常懦弱,从青少年时期一直到军队生涯,从面对艾滋病村到面对拆迁,再到面对书出版的争论和禁止,我总是习惯性地妥协再妥协。但是我知道,身为一个小说家,至少得表达一点正直心。
当下作家面临的政治风险并没有那么大。说实话,现在的作家随便写两集电视剧,也够满足生存了。只要有相对小康的生活,作家可以做得更纯粹一些。文不以载道,但可以载着一个人最淳朴的正直心。
能否对这个世界有独立的表达,更多的是人格问题。每个作家应该自问:就算有香港、新加坡那样自由的环境,你能写出好东西来吗?对世界虽然灰心,但我们还有写作这个出口。
在《炸裂志》的写作中,我的态度是偏于轻松、幽默的。试图在写作中举重若轻吧。没有倒下——这算是我活了大半辈子的唯一收获。在这个世界上,你很清楚所有事情都不会改变,但人不倒下,人生就不太会幻灭。
一次春节,我们县的老宣传部长给我打电话,他直言:“阎老师,你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我们县威信有多低。”这时,另一个人把他的电话拿过去,说了一句“他喝醉了”。
有时,连家人都会问我,为什么不写电视剧?在央视黄金时间放放多好啊。但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不介意别人对我的评价,我更在意自己对自己能不能有清醒的认识。
从农村走出来的人,都不应该要求留在土地上的人理解你。反过来,我们一定要尽量理解那里的人。如果作家失去了跟现实土地的联结,就不可能继续写作下去,也不会长进。尤其是我。我最亲的亲人都活在中国现实中,我自然不能逃开对当下现实的关注。
前段时间,我专门跑到电影院去看《小时代》,遗憾的是已经下线了。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它。不可否认的是,今天多数中国人已经被金钱和欲望所控制,无论城里人还是乡镇人。
终于到了这一天,现实的荒诞和作家的想象通道赛跑了。赢的是中国的现实,输的是作家的想象力。你有多大的想象力都无法超越现实本身的疯狂、炸裂和传奇。
我很怀疑自己的作品总有一天会被时代抛弃。这承担的不是政治风险,而是艺术风险。如果太贴近现实,作品没几年很有可能遭到淘汰。
屠格涅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年他的《父与子》引起了左右派近两年的热烈争论,但今天人们更爱看托尔斯泰,看他作品里的人性和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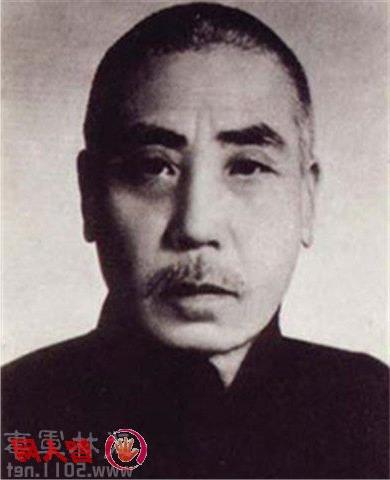

![阎红彦后代 阎红彦将军的最后岁月[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f/00/f000a9357b0b55f65770930baaa02cd4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