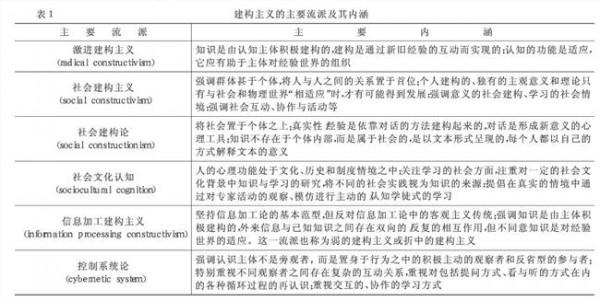秦亚青的理论发展 【理论研究】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
作者:秦亚青(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
内容说明
本文根据秦亚青教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期刊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高梓菁,胡传荣,杨晔对本文整理做出的贡献。
秦亚青院长
本文简单地谈一谈当前国际关系的现状,主要涉及学科方向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希望可以从中发现机会,找到落脚点。
第一个现状是出现了三个回潮,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层面都存在这个问题
第一是权力政治回潮。这在美国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美国战略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却引起了很大反响。
文章称,“过去的坏日子回来了(The bad old days are back)”,亦即以往的权力政治时代又回来了,所以美国需要以权力政治对抗权力政治。
冷战之后,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在美国迅速崛起,这也表现了当时美国的一种乐观情绪,但是现在美国确实感到很多事情并不是靠其想象和能力就可以做成。我参加过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者中有两位知名现实主义学者,一位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另一位就是斯蒂芬·沃尔特。
他们提出两个现实主义标志性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何必把关注重点放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面?伊斯兰国再可怕,至多杀数百个人,国家才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行为体,崛起大国才是美国需要关注的重中之重。
所以,美国仍需把战略重点放在崛起大国上面。第二个观点是美国仍要依靠实力主导世界。
我作了一个发言,发言结束之后,米尔斯海默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美国)来管理世界呢(Let us run the world)?
集中精力对付崛起大国是现实主义的根本战略取向。权力政治回潮确实十分明显,去年我梳理了一些美国关于对华关系的研究文献,其中大多数都强调应当对中国强硬,并且这种强硬不是制度或理念上的强硬,而是实力上的强硬。
第二是国家中心论回潮。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消解,国家中心论有些弱化,至少不像原来那样明显,当时很多声音是强调全球治理、国际制度、国际社会、公民社会等等,但现在国家中心论观点再度出现,认为唯有国家方能真正把握和运用实力,唯有军事实力才有最终发言权。
在俄罗斯、乌克兰等问题上尤为明显。领土主权问题格外突出,形成的热点难以降温,引发的矛盾难以消解。因此,“国家”重又占据了国际关系很多战略和理论的核心位置,成为国际关系话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
第三是民族主义回潮。就其实质而言,这与国家中心论相关联。涉及到民族主义的一些言论和行动,都明显地表现出来。
且不仅表现在原来民族主义较为有基础的地方,例如亚洲等,在其他地区,如欧盟一些国家,都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仅是在类似于希腊这样的欧盟边缘国家,也包括在一些欧盟核心国家。
国家性民族主义突出,认为国家自身利益至高无上,没有必要去帮助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也没有必要去管别人的事情。总体而言,这三种回潮势头还是比较强劲的。造成这几种回潮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加剧。中国迅速崛起,美国高度防范,凸现了大国博弈问题。尤其是中美战略互疑,很多事情都会引起猜忌。
例如说在太平洋容得下中国和美国,这本来是说想与美国谈合作,但美国则认为这是要同它分权。我接触一些美国人,他们对这些问题疑虑很大,其中包括美国的官学两界,也包括原来对中国较为理性的一些专家学者。
除此之外,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还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的都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实力对抗型博弈,这是出现回潮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全球治理成效甚微。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全球治理本应是一个可供大国合作的巨大平台,但这件事情没有做好。
在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WTO 谈判十分艰难,各国受阻后纷纷转向小多边和双边,创建地区、周边、双边自由贸易区(FTA)。
这些无不表明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制度建设在全球层面上严重受挫。在其他领域,如美国着力最大的反恐领域,也是“越反越恐”,现在出现了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更为可怕。
我曾在会议上遇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记者,她采访了不少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这些人就是要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最残忍的手段,挑战当前以美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他们针对的并非某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某几个政权。这个记者也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西方需不需要反思?
还有,这些恐怖组织以前主要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已延伸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成为国际秩序中高危因素。
第三个原因是国际合作出现新的阻力,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受到质疑。冷战结束伊始,新自由主义在战略政策领域强劲崛起,与现实主义形成针锋相对的理论流派。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以多边国际制度促成国际合作
认为战后由美国建立的一套制度能够有效维持国际秩序,可以容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
当时桑顿(Thornton)的一篇文章刊登在《外交事务》杂志,其观点即为美国所建立的制度具有强大的同化功能,中国完全可以被纳入其中。
当时这种乐观的情绪弥漫在整个美国的政界和学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以国际制度协调国家之间的行动,从而促成国际合作。
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国际合作仍然举步维艰,所以人们开始质疑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效度。可以说,以上三个原因直接导致了现实主义回潮。
第二个现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重要进展,即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兴起。
起始点应是 2005 年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Acharya)联合发起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R theory)”这一研究项目。
该项目原本希望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地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与前景,首先在亚洲找了一些国家,其中有中日韩,还包括东盟的几个大国。项目于 2007 年完成亚洲部分
但结项的时候,发现东盟几个成员国,包括印尼,几乎都没有完成。东盟国家除新加坡外,其余各国多是研讨政策,很少做理论。涉及理论问题,也多是使用西方现有的理论。
项目的最终成果发表在《亚太国际关系》杂志(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上,共计六篇论文,其作者除阿查亚和布赞外,还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学者。我参与这一项目有两个很深的印象。
一是大家形成了两个共识:第一,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理论也应该是多元的;第二,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话语主导造成的。这一项目的成果后来集结成书,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引起很大争议。
对这一项目提出的问题,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都需要作出回应。2015 年,阿查亚担任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 ISA)主席。阿查亚原籍印度,所受的教育来自西方,曾在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多间大学任教。
就阿查亚本人的学术成就而言,主要是在建构主义规范议程内从事东盟研究,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际规范在东盟可被接受,有些则不被接受。
他的代表性论文是“谁的理念更为重要?(Whose Ideas Matter?)”。他发现,当国际层面上的规范性理念与东盟地区自身的理念相吻合时才会被接受,如若不吻合,东盟会先接受地区的规范性理念。阿查亚使用了两个规范的例子,一个是共同安全,一个是人道主义干预。
共同安全与东盟的规范相吻合,东盟很容易就接受了。人道主义干预规范与东盟自身规范不能很好地吻合,东盟就难以接受。
阿查亚主张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担任ISA 主席时发表了一个主席讲话——“全球国际关系学和世界中的区域(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该文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包含六项内容:(1)国际关系理论应表现为具有普适性的多样性(universal diversity);(2)世界史不是西方史,而是包含多个地区历史;(3)国际关系话语同样是多元的;(4)地区和本土产生的理论要有普适性,不能完全拘泥于本土或区域;(5)不能奉行例外主义,不能奉行美国例外主义或中国例外主义;(6)所有的体系,无论是话语体系抑或理论体系、社会体系,一旦封闭必然停滞,体系必须开放。
ISA会刊 IS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杂志近期会出版专刊,发表一组文章,主要围绕全球国际关系学展开辩论,卡赞斯坦、米尔斯海默、布赞等重要学者参与讨论。
这一组文章发出之后,估计在国际学界会再度引发较大的争议。目前是国际关系发展十分关键的时期,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机会。
当然,根本而言,还是我们是否能够生产出真正优秀的研究成果。非西方学界不仅仅要提供成熟的观点,还要提出核心概念、进行理论建构、完善理论体系
第三个现状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关注以实践本体为核心的理论研究。
所有的知识都基于共同体的实践。如女性可以形成实践共同体,具有自己独特的实践经历,其感受、思维方式、对问题的建构与男性不同,因此会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非西方文化也是如此。
学术本来就是越争论越有趣,有人指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自建构主义之后便没有提出十分重要的理论,大家整天就围着三大理论转。当然,要看到还是有新的思想出来。
2011 年,以学理研究为重点的剑桥国际关系研究系列(Cambridg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推出了加拿大学者阿德勒(EmanuelAdler)和普利奥特(VincentPouliot)主编的《国际实践》(InternationalPractices)这本论文集,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一系列以专著为主,很少出论文集。
文集的出版一方面说明,注重实践本体的研究可能成为重要的研究议程,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元理论构建上没有重大突破,还没有形成足以与三大理论抗衡的理论。
我觉得这种状况的出现尤其为非西方学者都提供了机遇,也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来机遇。
首先是非西方确实在崛起,不仅是物质上、经济上在崛起,文化上也在发展。印度或中国等大国的崛起,一定会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一些不同于西方的实践和理念,而非仅仅在威斯特伐利亚经验和实践基础上思考问题。
其次是西方学者也发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非西方国家崛起,很多问题再以西方理论进行解释,就会出现理论和现实不相吻合的状况。
阿查亚对东盟规范的研究就发现“国际组织传授、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一主流建构主义规范传播模式存在问题,在东盟就出现了另外的规范传播方式。
再如,均势依然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均势可以维持和平的思想也很普遍。
这一概念的经验依据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但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普遍话语。然而研究威斯特伐利亚之外的国际体系,例如东亚国际体系,就会发现这种均势并不存在。
那么,为什么东亚体系在 1300-1900 年间没有均势的条件下存在相对稳定的和平?再次,整个世界学界的多元意识加强,西方学界内部的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比如,女性主义在西方已经是非常重要的理论。
试想,胡传荣、李英桃老师致力于女性主义研究,如果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加入世界女性主义的研究,参与学术辩论,提出新颖观点,一定会产生重要意义。
这就是我谈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它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启发。有人做战略研究,有人做政策研究,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多的。
但也必须有一部分人从事理论研究,否则中国会在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领域缺位,对中国和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都是一种损失。
现在的一个基本状态是西方学者出理论、出思想,非西方学者出数据,出案例。需要改变此种状态。所以必须要出新东西,但这并不是说新东西就绝对反对旧东西,学习仍然是非常必要的。最后当谈一点的就是期刊。
中国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但存在语言障碍,国际上被很多人看不懂中文。莫言的小说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当然,首先是他自己写得好,这是根本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作品的成功传播。张艺谋将作品改编为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有人将其作品译为英文,而且翻译得非常好,也加强了莫言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没有这两点是不行的。现在国际研究协会希望着手推动三件事情
第一个专门组织、发现真正高质量的非西方学界的英文文章,很多很好的思想不能被共同分享是遗憾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需要非西方学者进入西方一流刊物内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辩论
第三个是收入优秀的非西方学者的非英文文章并翻译为英文发表。
这些对我们而言都是启发。当然这些事情能推到哪一步,有多大的投入都是问题。对我们中国期刊国际化而言,大前提仍然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发表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否则,就难以构建全球层面上平等学理对话的平台(注释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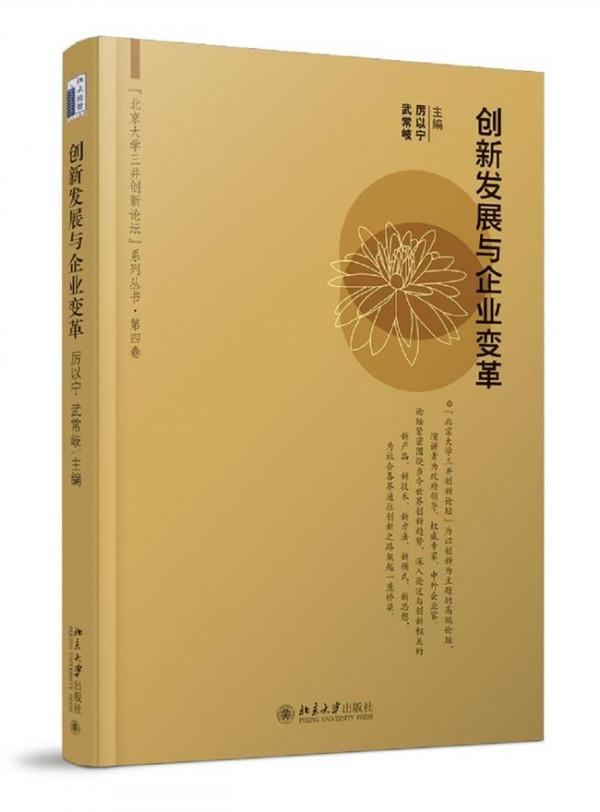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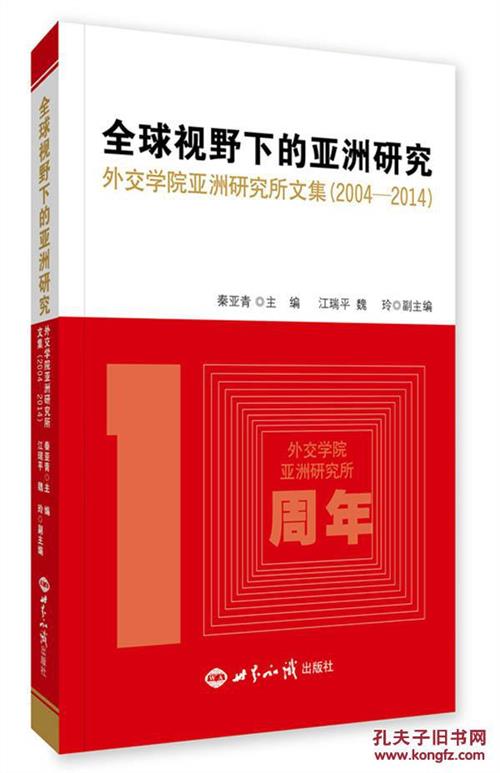







![>外交学院秦亚青 [政治学海归] 美国密苏里大学秦亚青(外交学院)](https://pic.bilezu.com/upload/0/53/05330d06c274f16eebf6ded3ccbd60fa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