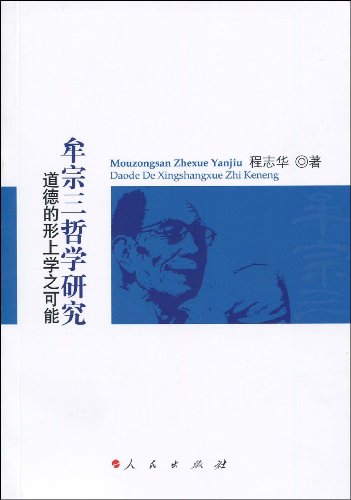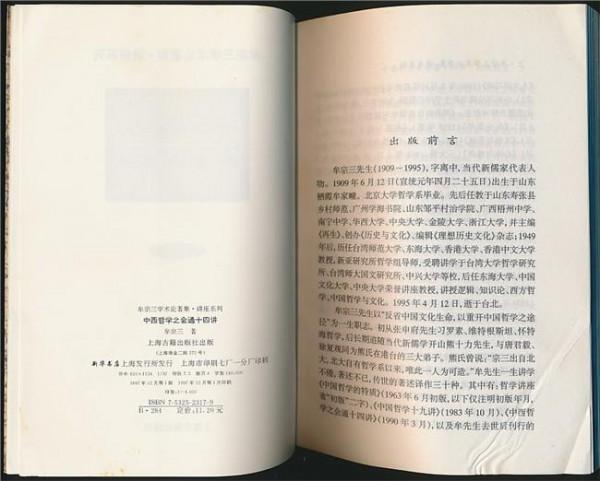生命的学问牟宗三 程志华:生命的学问——牟宗三论儒学之特征
[摘 要]牟宗三将中西哲学作为人类哲学的两大骨干:西方哲学是“知识的学问”,它以“自然”为领导观念,其主要内容为讨论“形成之理”的本体论和讨论“实现之理”的宇宙论;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它以“生命”为领导观念,性理、玄理和空理构成了其主要内容。
在中国哲学中,释、道两家只是“旁枝”,而儒学才是中国哲学的“主干”;作为“主干”,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其主要内容一方面为主观方面的修身,二为客观方面的家国天下。牟宗三认为,因着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儒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故可实现对西方哲学的超越和“转进”。
[关键词]儒学;生命的学问;西方哲学;知识的学问;转进
牟宗三认为,人类哲学除了西方哲学作为一个骨干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骨干。或者说,除了作为“知识的学问”的“外在的形上学”的理路之外[③],人类哲学还有另外一个理路,即作为“生命的学问”的中国哲学。而且,这“生命的学问”由于是“直承心性”而开出,故它可以实现对西方哲学的“转进”。
不过,在牟宗三,这可实现对西方哲学“转进”的“生命的学问”只是中国哲学当中的儒学。而且,在儒学各个派系当中,惟有心性儒学“由内部心性以言道德实践之学,正有其最大之文化上之作用”[1],故“能给西方宗教以开展、以转进”[2]。
在牟宗三,“生命”一词是有特定的指向的,它不是指“生命的外部”,而是指“生命的内部”。所谓“生命的外部”,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所谓“生命的内部”,则是指道德政治层面即精神领域的“生命”。牟宗三认为,精神领域的“生命”是分层次的:首先,它是指眼前的个体生命,即,就如其为生命而观之的“生命”。
这是较低一个层次的生命,在此层次之中,生命会有许多麻烦。其次,它是指诸如佛教所说阿赖耶识、涅槃法身等层次的生命。
这是一个较高层次的生命,在这个层次中,生命的麻烦都已经解决了。牟宗三认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的麻烦是很容易解决的,但“生命的内部”的麻烦解决起来就困难多了。也就是说,虽然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可以安顿好,但精神领域的生命的麻烦却很难安排妥当。
因此,就此意义上看,“征服世界容易,征服自己困难。人最后的毛病都在自己,这个时代的灾难最后也都在人本身,而不是在原子弹”[3]。但是,与此同时,人也有值得赞美的一面,因为人可以由低的层次向上翻,以至达到最高的境界。
换言之,人的生命的层次是变动的,既可以向下堕落以至于比禽兽还坏,也可以一直向上升以至达于神圣。正因为如此,哲学家们为了提升人的生命层次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不过,这种探索主要是在中国哲学中来展开的。牟宗三说:
“征服世界易,征服自己难。”征服自己就是对付自己的生命。这个最深刻最根源的智慧动处,实是首先表现在中国的文化生命里。……中国文化里之注意生命、把握生命不是生物学的把握或了解,乃是一个道德政治的把握。……在如何调护安顿我们的生命这一点上,中国的文化生命里遂开辟出精神领域:心灵世界,或价值世界。道德政治就是属于心灵世界或价值世界的事。[4]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的探索源远流长,而且,正是这种探索形塑了中国哲学的特征。“中国文化生命,则自始即首先把握‘生命’,以生命为对象而期有以润泽调获安顿之。”[5]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哲学的着眼点就落在了关心人自己身上,就落在了“安排这最麻烦的生命”[6]上。
最初的表现就是对“德”观念的清醒认识,比如《尚书》即讲“疾敬德”,要求把提高自己的德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牟宗三说:“《尚书·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
’这当是中国文化生命里最根源的一个观念形态。这一个观念形态即表示中华民族首先是向生命处用心。因为向生命处用心,所以对自己就要正德,对人民就要利用厚生。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事实在就是修己以安百姓两事。
”[7]从“知”的方面看,尽管古人的知识很简陋,根本不能与现代人相比,但古人对“德”已有清楚而分明的观念。后来,孔子就是在这清楚、分明观念的基础上开出了儒家传统。“儒家之所以为儒家,即在点出这一点,亦即在完成这一个‘德’。
当时周文罢弊,儒家之以质救文,即在德性的觉醒。从德性的觉醒恢复人的真实心,人的真性情、真生命,藉以恢复礼乐,损益礼乐,创制礼乐。”[8]虽言整个中国哲学着眼于生命的安顿,但牟宗三实际上对于中国哲学的内容还有进一步的简别。他认为,就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儒家是主流和正宗,道家则是针对儒家而生发出来的“旁枝”。
以这种简别为基础,牟宗三进而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传衍进行了疏解。他认为,在孔子等原始儒家之后,汉学主要是继承了儒家的经典,这是汉学的重要贡献。而且,汉代的典章制度深深影响了后世社会,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政治文物”的主流。
“两汉四百年,为后世历史之定型时期。一经成型,则礼俗传统,于焉形成。”[9]后来,魏晋时代以道家的精神为主,故其名士专谈“三玄”,即《老子》、《庄子》与《易经》。很明显,这个时代的学问由儒家的主流“岔”到了旁的方向。
在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中国的思想主要在吸收佛教的教理上。不过,到了隋唐时期,其典章制度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这样,由魏晋名士谈“三玄”的歧出,再经南北朝对外来佛教的消化吸收而表现出“歧出中的歧出”,这一“歧出”阶段持续了约五百年的时间。
牟宗三认为,大唐盛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种“特殊”表现在其“政治文物”、典章制度是属于儒家传统的,但儒家的义理精神在此时期并无表现,反而,其思想义理的精彩处在佛教。
中国佛教的大宗派都产生在隋唐时期,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等,佛教的教义在此时也发展到了最高境界。尽管如此,唐朝的“政治文物”、典章制度并不是佛家精神,因为佛家精神与治世不相干。
这样,比较地看,汉朝是一个大帝国,它是以经学治天下,即以经学统政治,以政治统经济,它所服从的是“理性原则”;唐朝之所以也能开出一个大帝国,原因在于唐太宗式的英雄与诗这两个因素:英雄是表现生命的,诗也是依靠生命的,唐朝所服从的是“生命原则”,而不是“理性原则”。
不过,“生命原则”并不可靠。牟宗三认为,“生命原则”是“抛物线”,可以从一无所有发展到最高峰,由最高峰又将落下至一无所有。故此,唐朝发展到唐末五代时便一无所有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国家最混乱。因此,一定要在“生命原则”以外重视理性,重视“理性原则”。
惟有如此,一旦当“生命原则”的“强度”开始衰败时,依靠理性便可使生命延续下去。牟宗三认为,这一点可从宋朝的文化反映出来。宋朝开国时国势很差,且其实力一直没有达到唐代的水平,但宋朝却足足维持了三百年之久,比唐朝时间还长。
这是什么原因呢?“此乃靠文化的力量”,靠“理性的原则”[10]。所谓“理性的原则”,是指以理性“润泽”和“调护”生命、国家和社会。牟宗三说:“理性,若简单指目出来,不外道德理性与逻辑理性两大纲领。
”[11]当然,此理性原则主要是指“道德理性”,而非“逻辑理性”。牟宗三指出,宋代儒学后来受到了来自诸多方面的批判,以至于将宋朝亡国的责任推到宋代儒学身上,这是很不公平的。实际上,理学家不能负这个责任。若公平而恰当地了解历史的话,整个宋朝三百年是服从“理性原则”的。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他说:
理学家就是看到自然生命的缺点而往上翻,念兹在兹以理性来调护也即润泽我们的生命,生命是需要理性来调节润泽的,否则一旦生命干枯就一无所有,就会爆炸。而理性就能润泽我们的生命,这样生命就可以绵延不断地连续下去,这一代不行可以由下一代再来。[12]
宋亡后元朝不过持续了一百年,而明朝持续的时间则长得多。牟宗三认为,明朝的“政治文物”和典章制度大体是模仿汉朝,但其实并没有模仿好。但是,总的来看,明朝的时代精神是以理学家为主的,也是服从“理性原则”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王阳明心学的出现给趋于僵化的儒学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使得儒学在明朝中叶以后大放光芒,从而对佛教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王学一出,佛教就衰微而无精彩了。”[13]这样,宋、明两个朝代的儒家因成为儒学的两个高峰,也因共同秉承“理性原则”而被牵连到一起,被共同称为宋明儒家。
由上述论述可见,牟宗三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所秉承的是“理性原则”。不过,在牟宗三,这三个朝代的“理性原则”是有区别的:汉朝是文献经学的整理,而宋、明朝则是儒学义理的阐扬。
或者说,宋明儒家是继承先秦儒家发展的,它是依儒家内部义理讲的儒家;而两汉经学是外部经学的儒学,它所依的只是儒家的经典。基于这种理解,牟宗三认为,“光是六艺并不足以为儒家,就着六艺而明其意义(meaning),明其原则(principle)这才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14]。从根本上看,“儒家之所以为儒家,是宋明儒所表现的”[15]。他说:
儒家对人类的贡献,就在他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开始作一个反省,反省就提出了仁的观念。观念一出来,原则就出来。原则出来人的生命方向就确立了。所以他成一个大教。这个大教,我平常就用几句话来表示,“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本质意义(essential meaning)就在这里。[16]
然而,到了清朝,中国的文化生命受到了严重挫折。清朝把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政治体制破坏了;以前设有宰相,到满清就变成了军机衙门,成了军事统治。牟宗三说:“到清朝就成为军事第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理想丧失了。
所以清朝的知识分子没事可干,就成乾嘉年间的考据。此根本与汉学不同,精神也不一样,不是传统文化的顺适调畅的发展形态,这是在异族统治下的变态。”[17]乾隆皇帝反对以往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认为那是坏习气。
自此,由孔子传下来的知识分子的理想破灭了,它们对于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也没有了,乾嘉年间的学问遂成了“清客”[④]的学问,很多考据家都做了“清客”和“帮闲”[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牟宗三并不是说考据没有价值,而是反对乾嘉年间知识分子“清客”的意识形态。
他说:“清朝是异族的军事统治,对民族生命有很大的挫折,因而对文化生命亦有很大的歪曲。”[18]这种情形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以至于近代中国面对外族侵略而节节败退。牟宗三说:
乾嘉年间以来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是清客。故清末民初西方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我们就完全无法应付。因平常不讲义理,不讲思想,故脑子里就没有观念,没有学问传统,在这样的情形下靠什么来应付呢?只靠一时的聪明是没用的,这种聪明中国人是很有的,清末民初那些人也都有,但只是这种聪明不足应付。因为我们丧失了我们的学问传统,丧失了学问传统就不会表现观念,不会运用思想。[19]
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牟宗三认为,现代中国本应与自己的传统相呼应,保持现在与历史生命的“不隔”。然而,“现在的中国人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太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无存在的呼应。故与历史生命相隔,不能存在地相呼应。
”[20]中国文化是讲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然而,此时却出现了明显的“代沟”,历史与传统之间出现了“断裂”。之所以如此,与中国人的心理习惯有关。牟宗三说:“西方人有许多观念,许多主义,这些观念与主义只是学术上的主张,或是政治上的个人见解,在西方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不会引起什么骚动。
但这些观念与主义一到中国就不得了,每一个主义就成了一个宗教,都想以之治国平天下。就这样地生命固结在某些观念上,而排斥其他的观念,终于对我们的生命造成骚乱。
”[21]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虽然在风俗习惯、社会礼节方面仍遵守典型的中国传统,但中国的思想意识已完全不是中国传统的了。因此,不仅一个人的生命不能和谐,不能一致,而且整个民族生命也“横撑竖架”、“零乱不一”、“四分五裂”。
对此,牟宗三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说:“凡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不能得到谐和的统一,这时代一定是恶劣的时代,悲剧的时代。”[22]而造成这种“恶劣”、“悲剧”的原因,“亦是因为头脑没有概念化而造成的”[23],即,由于没有遵循“理性的原则”所造成。
在进行了上述历史回顾之后,牟宗三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了解一个文化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其内部核心的“生命方向”,但这种了解的前提是不能把“生命方向”等同于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因此,不能被一般流行的浮薄观念所迷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