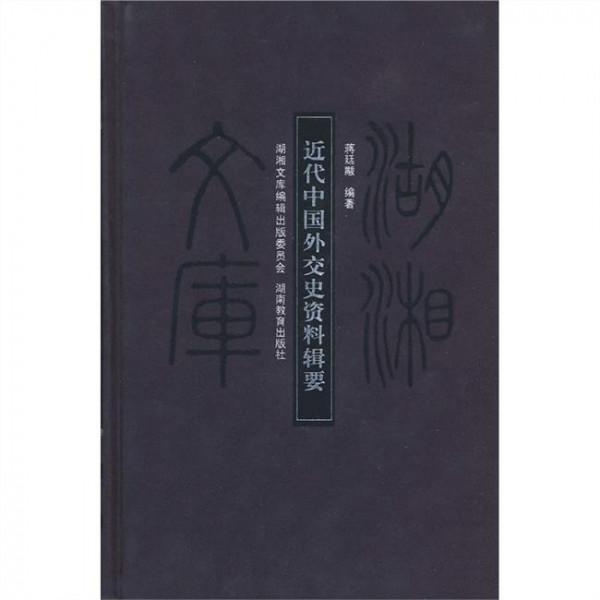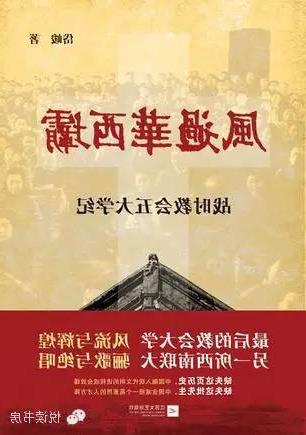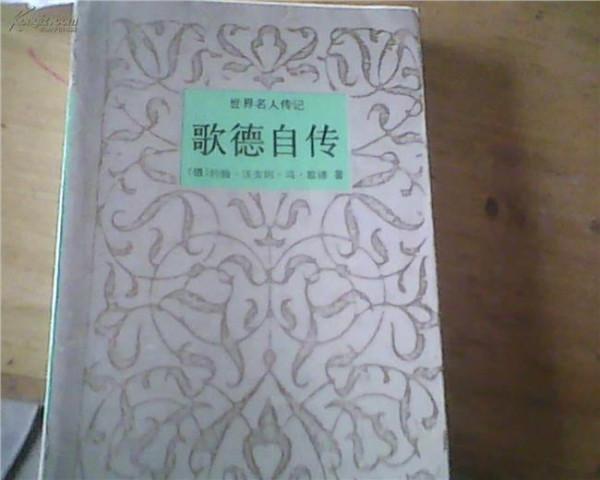薛福成与传教士 晚清士大夫与传教士对进化论的不同回应
原标题:晚清士大夫与传教士对进化论的不同回应
早在19世纪70年代,达尔文的名字和西方自然进化论的观点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但这种介绍还是零星和不全面的。甲午战争之后,严复系统译介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并名之为《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等词语,刺激了爱国者和维新派的神经,敲响了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警钟。
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思想译介到中国后,带来了对传统封建礼教和儒家思想的冲击,加剧了伦理道德体系领域的论争,其中传教士和士大夫对这一思想的不同解读和回应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进化论思想在晚清的引介、传播和接受情况。
严复译介斯宾塞学说旨在“新民德”。他认为斯宾塞把进化思想从生物学领域推到“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也就是从生物学领域推广到社会生活当中,揭示了人类社会进化的“公例”。这一公例就是,“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
”“盖生民之大要有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现代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为高下。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不足以自立,难怪屡战屡败。在严复看来,挽救中国危亡的办法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康有为提出了“德贵日新”的思想,即时代不断变迁,道德亦应随时而变,以符合时代要求。
梁启超在《释“革”》等文章中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谭嗣同在《仁学》中激烈挑战传统道德,主张打破儒家的“三纲五常”,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概括而言,晚清士大夫的道德重建主张与当时救国救民的社会诉求紧密联系,呈现出民族主义特点。
一些维新人士还吸收了斯宾塞社会进化论中竞争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应尊重个人权利的自由竞争等思想,借进化论批判传统儒教以及个人不自由、国家间竞争失败的晚清社会现实。薛福成批评了正统儒家义利观的偏弊,主张引进西方工商兴利致富之术,称“人人之私利既见……通国之公利寓焉”(《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
梁启超针对中国传统以“利己”为恶德的观念,宣传利己之德对社会进步和个体自立的重要意义:“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对于他族而倡爱国保种之义,则利己而已,而国民之所以能进步繁荣者赖是焉。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严复还大力提倡西方“开明自营”的合理功利主义思想,认为:“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薰莸之必不可同器。
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斯宾塞对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体竞争的辩护被晚清维新人士吸收利用,使得传统价值观念中义利对立的思想逐渐被消解。
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可以看出他深知进化论是一种纯自然淘汰论,若以此分析人类历史与社会进化,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并且,中国人并不完全认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法则,尤其是在国族与国族之间的关系方面。
以严复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阶层深知中国处于落后的半殖民地位,国族与国族之间的法则已经掌握在强者之手,但中国能从社会进化论的逻辑中看到变弱为强的希望。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人对社会进化论的选择性利用的态度和回应,表现了开明士大夫阶层在晚清社会现实面前的处境、立场和选择,这其中被动中夹杂着主动,绝望中抱有希望。
严复译介天演论为的是敲响警钟、救国强民,但社会进化论中所蕴含的宣扬个人主义和殖民侵略主义倾向在当时也引起一些人的质疑。1905年《万国公报》发表一篇《道德与哲学》文章,虽未署名,但从全文的立场推断作者应为教会人士。
该文批判了斯宾塞、达尔文学说,“顾沿斯宾塞达尔文之说,其于上帝也,则曰不可思议,其于人事也,则曰万物竞争优胜劣败,以前之说去吾人畏敬忌惮之心,以后之说长吾人嗜欲攻取之念,而平和与慈善之世界一变而为杀戮战厮,强凌弱,众暴寡之世界而不可收拾,未始非斯达二氏之说为之厉矣。
”该文将斯宾塞、达尔文之说泛指为哲学,视为基督教的大敌和社会衰败、青年受惑的根源。“中国之于西方教化根底未深,而哲学之横流已忽焉行入东方,学子骤闻其义,足以涤荡神经,爽利耳目,而非旧道德家言之陈腐可厌或束缚不堪也,遂无不为之心醉,而掷弃所谓道德者,以为将来必能以哲学代宗教之位。”
在华传教士指出,斯宾塞进化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去道德的社会自然法则,必须以宗教道德填补进化论产生的道德危机。传教士林乐知译介的《人学》等书,便是试图以基督教信仰代替进化观作为主导社会的观念,反对盛行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
不同于原书作者李约各,林乐知的译介不在纠正社会上“人学之否极”,也不是为反对强权帝国主义,而回应的是“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对道德风气的影响和对宣教的阻碍。
在华传教士宣扬基督教道德,特别以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观反对社会进化论对个体的独尊。他们尽管赞同社会进化论中道德也是进化的,但不同意这种进化是以个人权利、自由竞争为途径的,主张爱己及人,和谐相处,反对以独而主张以群(人类)为量尺。
这些观点与严复等人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严复等人强调救国保种,所谓“新民德”属于民族内团结、一致对外的德;而传教士以宗教道德来劝诫华人接受世界大同的道德观。在华传教士选择“爱人如己”观为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和代表,与斯宾塞的优胜劣败观针锋相对:“则优胜劣败之说,信不足为社会进化之本,而必在爱人如己矣。
”“故管钥人之社会者,固爱人如己之理,非优胜劣败之理也”(林乐知、范袆:《人学》,广学会1910年版)。
虽然以林乐知为代表的传教士洞察了华人的救国需求,尽量向救国议题靠拢,在译介中加入自己的救国强国建议,努力淡化中西对立,但是这些思想不能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难题。因此,《人学》等反进化论著作的译介也无法取得像在西方和日本那样多次翻印、洛阳纸贵的效果。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本文系“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成果〕)













![张之洞简介 张之洞[晚清历史人物]](https://pic.bilezu.com/upload/0/2d/02d84524811ac835265d643fe33a54b4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