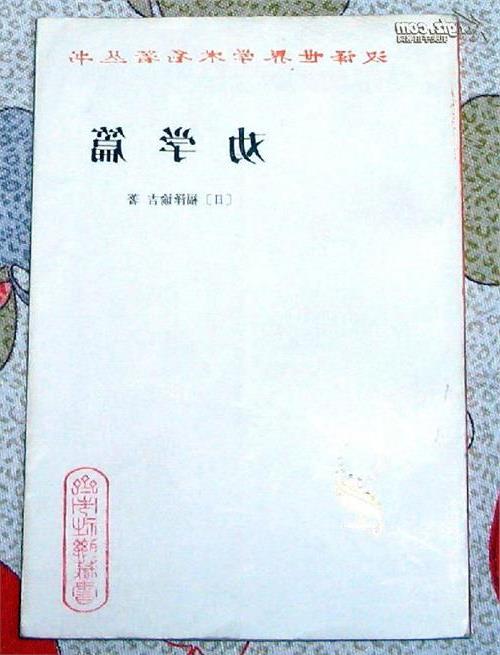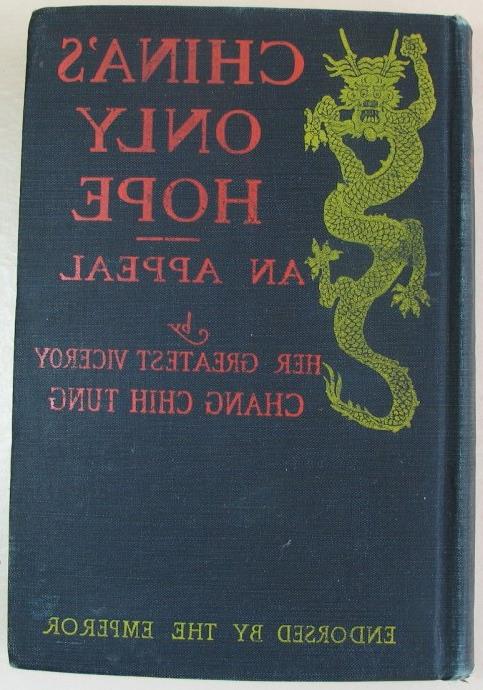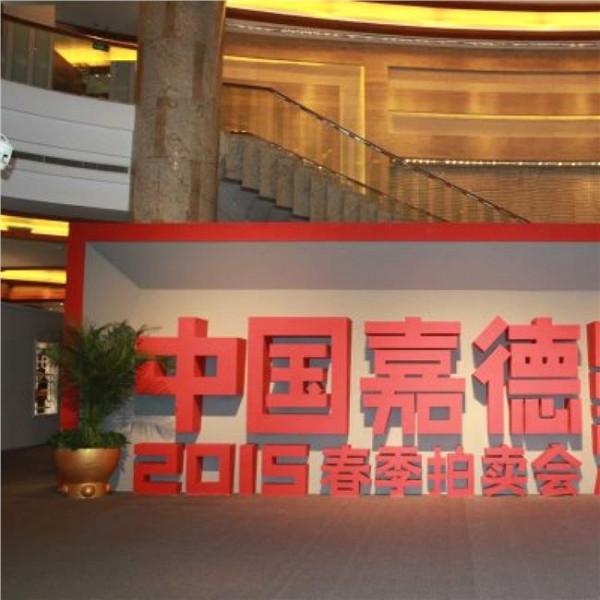张之洞劝学篇影响 张之洞与福泽谕吉两本《劝学篇》:互相冲突的变法思想
19世纪中叶,日、中两国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曾在外国炮舰威逼下签订过不平等条约,都曾从闭关锁国被迫向欧美各国开放通商口岸,都曾在面对“攘夷”与“开国”的抉择时有过激烈的抗拒和论争,都曾在固守传统文化与引入西洋文明之间忧虑彷徨。但因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两国自1868年(明治元年)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其结果是,27年后,日本战胜中国,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而清朝依旧是内政腐败,战乱频繁,民穷财困,濒临亡国的边缘。回首往事,国人莫不扼腕长叹,然时过境迁,任何感慨和怨恨都无意义,惟有找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对于启迪愚氓,儆省后人,或有些许益处。
鸦片战争前后的日本国情
日本是个岛国,在航海不发达的古代,海洋像一道天然屏障,保护日本从未遭受邻国的侵占。
日本国土面积37.8万平方公里,只有清朝的3.38%,比两江、两湖总督的辖地都要小,但海岸线却有3.4万公里,优良的港口比中国多得多,其海运、捕鱼业及航海技术远比中国发达。日本的人口在明治初年增长到3500万,只有同期中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但在东亚已是人口大国,人口密度之大和耕地之匮乏,使得日本已到了自然条件所能养活人口的最大限度,粮食缺口只能通过海洋捕鱼来弥补,而煤、铁等矿物资源的稀缺,使得日本在19世纪工业化来临时,较之中国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除了接受过中国文化,从未受过其他文化体系的影响。日本虽自唐代起就引进中国文化,但并未全盘中化,在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上,一直保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早在秦汉就在郡县制基础上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明、清又在元朝行省制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帝制,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进入了类似中国东周遍地诸侯的封建社会。
整个16世纪,有实力的诸侯都在进行战争和兼并,一百年后,日本才又获得了政治上的统一。胜利者德川家康袭用“将军”这个旧称号,把全国划分为自己的和封臣的领地,“他把全国四分之一农田和全部大城市、海港和矿山划给自己。在245个到290个封臣(数目因时期不同而异)或称‘大名’中,最小的只能生产一万石米。”领地共分为三个等级:有的分给德川家康的儿子和亲属,称作“亲藩大名”;一部分较小的领地封给了早就追随德川的旧臣,称作“谱代”,或“世袭大名”;他的主要盟友和战争中的有些敌人,称作“外样”,或“外部大名”,他们获准保留西部和北部边区的较大领地。“将军”和每个“大名”一样,自己都拥有一大批直属的武士家臣。(参见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pp68-69)
天皇住在京都,表面上受诸侯拥戴,但既无财权、军权,又无治权,只具有象征意义,德川家族的历代将军自17世纪初就是诸侯的最高统治者,将军通过设在江户的“中央政府”——幕府行使统治权。17世纪40年代,德川幕府强制推行锁国令,从1638到1853年,日本除了与中国、朝鲜和荷兰有少量的贸易,几乎断绝了与外国的来往。
清初虽然也实行过闭关政策,但到了17世纪后期,已逐渐开放与外国通商。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海禁,设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比日本早开海禁170年。后来为了便于管理,清朝设立粤海关,把对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地。在贸易上,由于中方长期处于顺差,并不曾认真排斥过外商,直到英商对华大量输入鸦片,两国才发生战争。
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日本人心中的文明大国。清朝战败的消息传到日本,引起幕府官员的极大恐慌。1841年1月29日,老中(作者注:幕府官名,将军的属官,在未设大老时,是负责全国政务的最高官员)水野忠邦在写给他的心腹的信中说:“此次来舶人称,清国严禁鸦片通商不当,引起英国人不满,派军舰四十余艘到宁波府发动战争,现已占领宁波县之一部。此虽他国之事,但亦应为我国之戒也。”(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39)1844年,荷兰国王在致幕府的亲笔信中建议道:“中国抗战无功而败北,结果改变古来的政策,开五港,付巨额赔款;而如果英国来日本要求通商,引起日本人民反对,由此发展成兵乱,则会导致严重的事态,故望日本采取坚定的政策,不要停留在只向漂流者提供燃料和水的阶段,而应开展‘交易’以避免兵灾。”(上书,p39)
攘夷与开国
1853年6月,美国海军东印度洋舰队司令官佩里率四艘军舰来到浦贺,强迫幕府准许舰队使用港口,幕府屈服于美舰大炮的威力,于翌年签订了日美和睦条约,开放了下田、函馆两港,不久,又与俄、英签订和睦条约。在1858年进行的通商谈判中,幕府把条约送到京都请天皇批准,遭到拒绝,当幕府官员告诉美方不能在约定的日期签字时,美国驻日本总领事哈里斯要求幕府高官到军舰上来会谈,他以清朝的失败恐吓幕府官员,要想避免战祸和不幸,在灾难到来之前缔结条约并使列强亦仿效之,方为贤明。幕府顶不住哈里斯的压力,不待天皇敕准就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安政五年六月初一,1858.7.29),又在随后的两个月内,签订了日荷、日俄、日英、日法通商条约。
围绕与欧美各国签订通商条约,幕府、朝廷和各藩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开国,一派主张攘夷。开国派认为,如果继续坚持锁国政策,以武力抵抗欧美各国的通商要求,必然步清朝的后尘,面对欧美各国的坚船利炮,除了接受他们的要求,开港通商,别无选择。
攘夷派则拒绝外国强加给日本的通商要求,主张以武力击退外国军舰,他们认为在外国的威胁下开港,有损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即便以后开港,也要按照日本的意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商务和外交关系,而不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在开国与攘夷的论战中,还交织着另外两种政见的对立,一派主张尊王,他们认为幕府体制已不能适应当今的国际环境,只有把政权交还天皇,建立统一和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应对危局;一派主张佐幕,他们主张坚守传统的幕藩体制,与天皇修好,公武合体,以应时艰。各派势力都在争取天皇的支持,天皇在长州藩的影响下倒向了攘夷派,幕府为了与天皇修好,不得不采取妥协姿态。
1863年5月10日,将军德川庆喜在朝廷的再三强制下,向各藩发布了攘夷令,以后若遇西洋各国的攻击,即可击退。其实,一直主张开国的幕府并不希望各藩主动挑起战争。可就在当天,长州藩在下关海峡炮击了美国商船,随后又炮击法国和荷兰的军舰。6月,英、法军舰进行报复,炮击长州藩炮台,并派陆战队上岸破坏炮台。7月,又爆发了萨摩藩与英国的战争,英舰炮击萨摩藩炮台,火烧鹿儿岛市街。长、萨两藩试图赶走洋人的抗战以失败告终,赔款、开港、签订不平等条约,同清朝的命运完全一样。此役过后,萨摩藩和其他藩国认识到以日本现在的实力,攘夷必败,只有与各国和平共处,引进西洋文明,发展工商,富国强兵,日本才有前途。
攘夷失败,加剧了诸藩与幕府、朝廷与幕府之间的矛盾,有识之士向开国思想转变的同时,也寻求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以取代幕藩体制,领导日本走向维新之路。幕府违敕签约,为席卷全国的倒幕运动提供了口实,一大批反对开国的大名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团结起来,经过十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讨伐,终于迫使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在明治元年(1868)交出政权。
中国的攘夷派都是立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坚信中华文化优于西洋文明,当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民族尊严受到羞辱、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时,便挺身与敌奋战,不惜玉石俱焚。日本的攘夷派更像是机会主义者,攘夷成了一时凝聚人心的口号,一种倒幕的政治策略,大政奉还之后,明治政府的政策立刻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执政者完全倒向了开国派,比幕府时期更加开放。
中国攘夷派的精神支柱是儒家思想和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可以战败,可以割地赔款,可以承认技不如人,但绝不承认中华文明劣于西洋文明。日本攘夷派缺少这种精神支柱,汉学也曾是他们的主流思想,但那毕竟是引进的异域文明,不是自己的根,当他们比较了汉学和洋学的实用价值之后,立即抛弃汉学,接受西洋文明。在促使幕府开国和明治维新时期,提倡洋学的知识分子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福泽谕吉与张之洞
福泽谕吉是日本提倡洋学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与张之洞是同时代人(比张大两岁),两人都以兴办教育闻名于本国,都写过一本《劝学篇》,都曾对本国的变法运动产生过影响,但与福泽的《劝学篇》对明治时期国民思想启蒙所起的巨大作用相比,张氏的《劝学篇》显得黯然失色。
福泽谕吉1835年出生于大阪一个下层武士家庭。武士是社会的上层阶级,享有教育、做官、佩刀、骑马等种种特权,他们在四民(士、农、工、商)中文化程度最高,在幕藩体制下,学者和官僚都出身于这个阶级。日本没有科举制,贵族和武士的孩子自幼入私塾读书,以汉学为主,喜欢西洋学问者则学习兰学(德川时代中期兴起的学习荷兰语或借助荷语研究西方学术的一门学问)。福泽十三四岁才入村塾学习汉学,以《论语》《孟子》开蒙,读了许多中国的文史书籍;19岁,他离开家乡到长崎学习兰学;一年后,他又去大阪,在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办的“适适斋塾”(也称“适塾”)学习。用绪方的话说,适塾把“培养当今急需的西洋学者”作为目标。
1860年1月,福泽谕吉作为遣美使节的随员,乘坐250吨小轮船“咸临丸”号(1857年江户幕府委托荷兰建造的军舰,幕府使节为批准交换“日美通商条约”赴美时,充护卫舰),航行37昼夜抵达旧金山,在闭塞的封建社会生活了25年,突然踏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惊奇和感慨可想而知,在美国旅行的五个月里,他事事留意,眼界大开。同年,他被幕府“外国方”聘用任翻译,出版了《增订华英通语》。1862年1月,福泽跟随遣欧使团赴欧,访问了法国、英国、荷兰、德国、俄国、葡萄牙六国首都,年底回到日本,此行使他的内心经历了无数的刺激、怀疑和苦思,对西方议会政治和它的理论基础——民权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
1867年1至6月,他随遣美使节再度赴美,采购了许多外文书籍。经过24个月的游历,福泽详细考察了欧美七国的政治、教育、军事、工商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当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与西洋各国相比较,认为日、中只是半开化国家,要想步入文明国家的行列,除了接受西洋文明,别无他法。于是,他以启迪国民为己任,向国民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宣传他的新思想,在明治初年,出版了《西洋事情》、《文明论概略》和享誉世界的思想巨著《劝学篇》。
在中国,没有专以培养“西洋学者”为目标的兰学,学生只有“读经-科举-做官”这一条路可走。当福泽在苦学英语时,张之洞在苦练八股文;当福泽在周游世界时,张之洞忙于准备会试;当福泽辞去幕府的职务,创办庆应义塾(一所专门教授洋学的学校,现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时,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步入仕途;福泽立志一生不做官,只从事翻译、著书、教育工作,张之洞则是官运亨通,位极人臣。面对19世纪后期的改革浪潮,作为日、中两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福泽谕吉与张之洞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献身于国民思想的启蒙事业,一个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志向与身份的不同,影响了二人的变法思想,使得二人在各自国家变法运动中发挥的影响完全不在一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