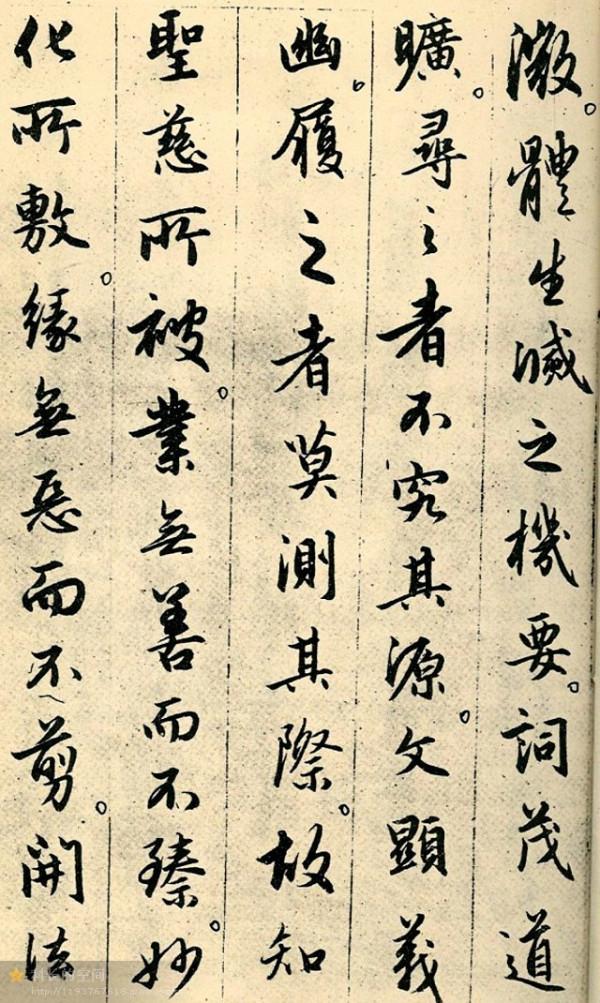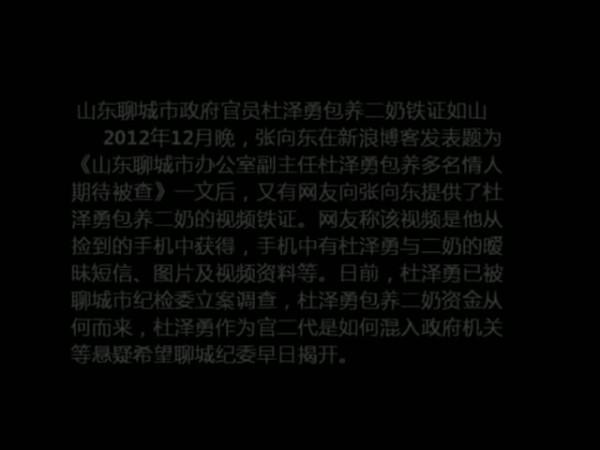杜泽逊绝学 学人丨杜泽逊:志在先哲国故心存古圣绝学
记者:杜老师您好,首先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文献学研究道路的?
杜泽逊:我是奉命。1981年我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时期,我当过外国文学的课代表,读过很多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像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的小说以及古希腊神话等等,当时阅读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的英语不太好,后来,我的兴趣主要还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上。
中国的古代文学面临两个难题:第一是训诂问题,读不懂;第二是音韵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是以韵文为主流,具体说是诗词骈文,都要用韵,都要讲平仄、辞藻,所以音韵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就转而学习语言学,古代汉语主要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我重点来修这些课程。
大学毕业推荐研究生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的,当年中文系招100名,推荐4名。这个事先没人知道,是突然来了这样一个政策。推荐方法,以四年大学必修课的成绩来排名,我是第五,所以只能考了。不过,我没想到我的成绩会这么好,因为我都是靠突击,平常都不准备考试的事情。
那时候我就喜欢泡图书馆,看非常多的书、杂志,有些书别人不看的我也会看。我记得,我看过《联绵字典》,编者叫符定一,《联绵字典》的书稿堆起来比符定一的身体还高。像这些书,我都会看看它的序言、正文都讲什么。这是现在人不常用的书了,我甚至后来也买了一部,影印之后四大册。我也看比较文学,像乐黛云的文章。
▲杜泽逊教授
毕业的时候,本来想考殷焕先先生的研究生,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那是他最后一次招生,总共招两名。假如说当时我进入前四名,进入推免,那么,我可能会选择跟着殷先生学习。但是没有,所以我就要考,考的话我就要考虑命中率的问题。
因为全国招生只招两名,他又是名师,所以就没敢报。当时有个新成立的研究所叫做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教育部批准成立,1985年开始招研究生班。古籍整理人才奇缺,所以要招班。一是两年毕业,不拿学位,光拿研究生毕业证,那么毕业后的一年内答辩就能取得硕士学位。
为什么两年毕业啊?快成才。为什么不要写学位论文啊?因为不要让你花费太多精力写论文,全力地学基本典籍。所以当年导读课比较多,比如《诗经导读》、《楚辞导读》、《庄子导读》、《史记导读》,当时就是全身心的念书。
这个速成班吧,30%留校,班里10个人就留了3个。留在古籍所的就两个,我和郑杰文老师。他是班长,我是副班长,住一个宿舍,床对床。我们俩都属兔的,他比我大12岁。他工作过,我没工作过。
考古籍所的原因,是我感到古籍整理有注释、有标点,它应该属于这个古汉语的应用部分。并且我已经下决心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所以考古籍所也不违背我的爱好。当时招生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古籍整理方向,刚好结合在一块了。
当时没有文献学专业。于是投考古籍所,考上,毕业后留校,所有手续就是老师问“你愿意留校吗?”“愿意。”然后就完了,不用求人,也不用别的。因为有些师兄都是有家有小的,四川的、福建的,人家都不愿意留校,所以没有多大的竞争就留下了。
留校后,组织上,古籍所领导找我谈话,让我跟着王绍曾先生。那时候有助教制,就是新工作的人要跟一个师傅,我就跟着王绍曾先生。王绍曾先生是无锡国专毕业,到了结束以后,他才重新开始学术工作。他没有什么职称,直接一步成了教授,大概83、84年他从图书馆直接调到古籍所,成了研究生的老师。
研究生班10个人是集体指导的,为首的是董治安先生,因为他是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所长是当时的校长吴富恒。教育部直接批的研究所并不多,级别很高,所长都是正处级,和现在的文学院院长是一个级别。
留校以后就跟着王绍曾先生干,王绍曾先生是位什么样的学者呢?他是一位文献学家,主要从事目录学研究,当时正在从事国家项目叫做《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这个工作在我加入之前已经干了一段时间了,有好几位老师参加,我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是专职工作,就是天天睁开眼就干这么一件事,其他的合作者都是边工作边干,都是上班的。
同时加入的还有刘心明老师,那时他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山大古籍所工作。当然王绍曾先生是专职人员。上班就是干这件事情,干这件事就是上班。奉命行事。这个《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干了七、八年之久,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得了教育部的一等奖。这个奖在文科是最高的,等于是国家一等奖了。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它用的书很多,参考书很多。估计得有四、五百种书。这样,我在这个过程中就熟悉了很多书。王先生是搞目录学的,那么我们当然看的书也大多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还有藏书史这方面。这些中文系上课的时候没学过,属于新的学问。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从文献学的小分支学科来讲,是属于目录学,属于史志目录。在这个过程中,王先生又让我写了一百多部书的提要,就是看原书写提要。这一百多部书基本上是版本目录学方面的,就是讲究版本的那个目录。这样我就涉足了版本学。
这一百多部书基本是这个专业的最重要的典籍,这样等于“逼着我”看了这些书。后来,这些提要经改造后收入《世界百科名著大辞典》。当然学术界看到这个词条,每条最后都有我的名字。这些词条大多经过王先生亲笔修改,原件我还存着。
这样我就涉足了目录、版本。版本目录又牵涉到藏书史,所有的稀罕书都是由藏书家来收藏的。藏书史是知道了,但是校勘学没有深入学习。到了一九九几年,就接触到一些新情况,一是商务印书馆委托王绍曾先生整理一部张元济先生的遗稿,叫做《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有一百多册,都是手稿,没有出版过。
我们十几个人整理,经历8年之久,对于二十四史的版本就比较清楚了,比如我是怎么知道杭世骏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什么叫校勘学就一清二楚了。我们校这些经,实际上就是受那个影响,他们校史,我们校经。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这个重大项目约我参加。为什么约我参加?因为我专门研究四库存目。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我对于存目是很了解的。我去中华书局联系《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稿件,就会抽时间去逛琉璃厂古籍书店。
当时买到一部《四库存目》,线装本,上面有人批过,我就考虑要搞《四库存目》。实际上,知道《四库存目》的人不多,搞《四库存目标注》就是注明这个书有哪些版本,都藏在哪里。
这个工作是清朝人开始干的,像邵懿辰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像莫友芝《郘亭书目》,还有王懿荣、孙诒让、缪荃孙他们都做过这个标注。我做《存目标注》也做了好多年,到2007年才整理好。北京大学要搞《存目丛书》,要知道存目书在哪里,这个工作只能我做,海内外就我一家。
这样我就参加了他们的项目,搞了《存目丛书》。《四库存目丛书》是个古籍影印工程,这个工程用顾廷龙先生的话来说是个“有轨电车”,是按照乾隆时期的《四库存目》这个目来找书。第一你要确认是这本书,不是同名的不同的书,你还要确认这本书是传世最好的本子,这就不得不进行版本鉴定。
通过张元济先生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的整理我明白了什么是校勘学,通过北大的《四库存目丛书》我明白了版本学,通过《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这个项目我明白了目录学,而这三者都与中国藏书史密切相关。从那时候到今天,我一直走这个文献学的路。
我最初目标是搞小学,进而通过小学搞古代文学,但是没走通。也就是说我走上文献学这条路是奉命的,不是个人最初的志愿。古籍所领导找我谈完话后,我还特地跑到刘晓东老师那里,问他要不要做,他说要做。因为他是搞经学和小学的。我当时还想跟他学,后来奉命跟着王绍曾先生学。
人啊,不能说设计好了路线就非要一条道走到黑。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基本是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古籍整理是中共中央在文革后提出的重要的工作,当时中央领导之一的陈云提出古籍整理是关系到子孙万代的事业。原因是把这些东西打得太严重了,所以才成立古籍所,招研究生班。我们就是第一届研究生班的毕业生。
记者:老师,您刚才提到《四库存目标注》花费了您十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而《十三经注疏汇校》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个讲究学术速成的时代,您的从容的心态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奥妙么?
杜泽逊:这个没有什么奥妙,就是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这是它的本质。眼前利益就是怎样快快地出文章,快快地评职称,快快地改善工资待遇。过去分房子就是按照你的职称来分的,没有职称你连房子也没得住,并且不能买房,那是很严峻的。
大部分老师都是在50多岁才分到一套小三室一厅,70平米,这是人间天堂了。当时山大老师奋斗的目标,就是在南院能分到一套房子。但是如果真正要搞学问,把它当事业来做的话,就会牺牲眼前利益,无论能不能快速出成果,都得遵从学术规律,不管多么长时间,需要多长就干多长时间。
当年一些爱护我的老师问我能不能先出一本《四库存目标注》。以前黄云眉先生的《明史考证》就是一本一本出的,前后时间很长。但我不同意,因为《四库存目标注》前后体例应该是前后呼应的、严密的,经常做了后面要回改前面,保持体例统一,但如果出版了怎么改?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先出两本,后来遥遥无期,至于后部分出版的时候连封面改了。
前面两册是白皮的,后面出的是有外套的那种,我自己买的这一套都配不齐,前后装潢不一。我不喜欢这样。另外,我特别怕出版社要求我改这改那,我希望把所有做好,连索引一起做好后交给出版社,让出版社没办法提修改要求。出版社让作者改,作者不好不改。这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
所有这些实际上是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二者并不矛盾。当你考虑长远利益,那么你眼前利益也会得到很好的维护,客观情况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的长期项目会有阶段性成果,包括论文、包括其他东西。做项目可以带动你的科研工作,你会不断发现新问题,写出带有突破性的文章。每个大项目都可以带出一大批文章,甚至你写的文章没地方发。
2000年前后,那个时候我核心期刊大约每年发4篇。每年第一个月我会写好4、5篇文章,然后慢慢让它去旅游吧。每年都要写,今年发的可能是前年写的,但是你每年必须写出这么些篇数来,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每年也能发出这么些来。
如果你能保证每年4篇核心期刊,你就很领先了。我要想超额完成的话,我这十二个月都写文章的话,可以写五六十篇,但是没那么多杂志让你发,所以只好少写。大项目能出好成果,而且是你想不到的。一般情况不做项目的话,你写论文首先是设计选题,然后是找材料,在熟悉材料的过程中形成你的观点、形成你的文章,这是一般的常态。
这样的论文和项目滋生出新发现来不是一回事。通过大项目来引发成果,在我看来是最好的方法。
记者:杜老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进行的《十三经注疏汇校》这个项目,分享一下“为往圣继绝学”的继承方法吗?
杜泽逊:《十三经注疏汇校》是属于校勘性的,是为经学服务的。也就是说经书中的义理是不归我们管的,甚至于说校出的字对错与否都是我们无暇顾及的,所以在一般人看来这种工作是很浅的,但这么浅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呢?像海外的《圣经》、《古兰经》、还有庞大的佛经都经过了系统的校勘,还有莎士比亚全集、中国的《红楼梦》等等。
但是儒家的十三经却没有经过这样详细的校勘,我们现在用的还是清代阮元主持的校勘记。但在校勘学上讲究的是追求较早的版本。
傅增湘曾在给张元济的一本书《校史随笔》写序的时候,举了个例子说,他的老乡张森楷先生校勘《史记》,校勘全史,他的手稿在南京图书馆,没有出版。他说张先生二十年来孜孜不倦地校勘,却没有见到宋元版,晚年才见到嘉靖本。
一般校汲古阁本和南北监本,南北监本是明万历年间刊刻的。张先生在去世前曾经托付傅增湘整理遗稿出版,但傅增湘说“不堪问世”。这就是方法上的错误,也就是校勘学第一要素是要得古本,没有古本就不用校了。
但清朝也有些学者没有得到古本也要校,他们的校属于选校,是感兴趣地发现问题,而不是大面积地毯式地去校,要想那样的话必须得有古本。阮元也知道这点并努力地去做了,但仍然有大量的古本没有找到。
这是因为当时没有图书馆,没有对外交流,日本藏的、其他藏书家收的,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借不来,这样就造成了信息方面的闭塞。但是现在社会发达了,信息发达了,早期的或重要的能找到的大部分都能找到,还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武英殿本阮元都没有校。
这个武英殿本整体上来说比较高明,但为什么没有校呢?可能是属于当代的。其实有些错误校了武英殿本是会容易发现的,但没有去校。这样的话它在最早的版本方面不占优势,也不注重当代的。
▲校经处一隅
现在《尚书注疏汇校》已经完成了,我问同学们阮元的校勘记完成的工作量会占到什么比例呢?有的说不到十分之一,我觉得大概在十分之三以下。他完成的工作量太小,当然他是做了是非判断和考证之类的。现在我们的汇校收集到的主要版本有十九个,都要校三遍,把所有不同的文字汇进来,第一,汇众本之校,第二,汇前人旧说,把阮元的校勘记一字不落地囊括进来。
汇校的目的有三个:一个是纠正流传在世上的各种版本的错误,希望将来形成错误较少的、流行的标准本,这是我们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
如果文字上就错了,研究了半天得出来的结论有可能是不堪一击的。第二是它对我们历史上曾经对《十三经注疏》的出版做出贡献的人的历史地位有个很好的评定。像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三经注疏》,遭很多人批评,但现在看来整体上是不错的。
还有像顾炎武骂万历北监本,那也是不对的,不是它先错的。我已经发表过文章,对《日知录》已有所商榷,这个是铁证如山的。怎么样才能有更好的定论,必须要形成信息链,当形成这个链条的时候,你才知道它在这个链上处于什么地位,它有不足的话,看它之前有没有这种情况,它有所突破,突破又在哪儿。
在这之前没有大规模的穷尽式的校勘,你就不能形成信息链,有了信息链才知道发展的轨道,这对中国出版史和版本史是很重要的,也是大量的版本学家所做不到的。
所以,一要鉴定版本的年代,二要总结版本的源流,三要辨定版本的是非优劣,做一个超越时代的是非评断。这些都有赖于校勘,所以版本学和校勘学是从来不分家的。《十三经注疏汇校》是不是“继绝学”不敢说,但是我觉得要有现实的考虑。
你做了这个职业,就要有所研究。教学相长,要想当好老师,你就要当一个好专家。你不做深入的研究,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做老师又能刺激你的研究,你有不懂的就要去钻研,去探索,然后才能拿来去教你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