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图片 于是之力辞大师之称 名片五个字:演员于是之
1月20日下午,86岁的于是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话剧表演的“于是之时代”,正式谢幕。
话剧观众中有句话:想起《茶馆》就想起于是之,想起于是之就想起北京人艺。以《茶馆》为代表的好戏,以于是之为代表的好演员,以北京人艺为代表的好剧团,绘就了解放后中国话剧发展史上的巅峰辉煌。本报资深记者唐斯复与北京人艺渊源颇深,她曾于1988年参与策划、促成了北京人艺携五台大戏赴上海演出这一轰动性文化盛事。
当艺术家远行的消息传来,她记忆犹新的是,于是之在上海的三次“登场亮相”和他对沪上观众、文艺界、新闻界的深切情意。
在沪演《茶馆》闭门不出,滴酒不沾
唐斯复说,于是之和上海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一”:在上海拍过一部电影《秋瑾》,演过一次话剧《茶馆》,出席过一次高规格的京沪文化交流座谈会。
1983年,于是之接受谢晋导演的邀请,来到上海参演了电影《秋瑾》。他在里面饰演一个名叫贵福的官员,这个角色一开始慈眉善目,“变脸”后凶神恶煞,于是之的戏份虽然不多,但演得活灵活现,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1984年,于是之凭借这次“触电”获得了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
1988年,于是之以他的本行——话剧演员的身份再度来到上海,这次演出既让他一偿夙愿,又给他添了不少“自我折磨”。唐斯复回忆说,于是之早有此念想,对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艺艺委会副主任的英若诚没少嘀咕:还没来站过上海的舞台,还没来上海演过戏。
为什么要来上海?一个大原因是,近现代以来,上海的舞台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试金石”,好演员都想来上海这个码头淬一回。一个小原因是,于是之的舅舅石挥,解放前在上海滩红极一时,被称为“话剧皇帝”;作为后辈,心底里或许有点儿沾着亲切的“上海情结”。
就是艺术家的这么一个念想,最终促成了北京人艺携五台看家大戏赴上海演出的壮举。鲜为人知的是,于是之原本在两台戏中担任角色,一台当然是《茶馆》,另一台是与朱琳联袂合演的《洋麻将》,可是背台词的任务太重,而61岁的于是之那时已偶尔显露出身体不堪重负、记忆力早衰的迹象,结果心脏病犯了,住进了医院。
没辙,《洋麻将》换下,《哗变》换上。于是之出了医院就赶到上海,住进宾馆,闭门不出,滴酒不沾。“要演戏就要演好”。
5场《茶馆》非常顺利,上海观众的热烈反响给了于是之极大鼓励。庆功宴在和平饭店举行,酒入樽中,顷定,老先生擎起小杯,细细把玩度视,尔后大呼好酒。一杯饮尽,那种兴奋、愉快和过瘾,至今让唐斯复历历在目。而在上海举行的京沪两地文化交流座谈会上,于是之发言前,向上海的观众深深地躹了三个躬。
没有“官”样,拒作大师,只做演员
尽管他后来担任多年主持北京人艺工作的副院长,但于是之一辈子只认“演员”二字。于是之的老朋友、评论家顾骧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于是之当过“官”,做了十几年的“副院长”,但他从不像“官”。登龙乏术,无袖可舞。
掏出名片,只有五个字:“于是之·演员”。要论当代话剧表演艺术家,一定要推举大师,恐非他不属;然而,他力辞“大师”之称。他有一句挂在嘴边的话:“不可能大师满街走!”朋友们相聚,谈笑间戏呼他“于大师,于大师……”他总那么当真,一脸惶恐,连连摆手,口中还念念有词:“别,别,别……”他不是矜持,不是故作谦虚,他是实实在在在心底不承认“大师”之说。他就是“演员”,演员于是之。
唐斯复告诉记者,为了演《龙须沟》里唱单弦的程疯子,于是之整天踩着破自行车在北京集聚着卖唱艺人的天桥那一带转悠,还专门跑到最“底层”的胡同茶馆里去听最便宜的曲艺演唱。因此他的“程疯子”手上带着那个八角鼓,每个小动作都是从生活中浑然化出,绝无凭空生造的生硬和突兀。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他绝对是好演员,下的功夫不是别的演员能做到的。”
回想当年于是之初演《茶馆》时,不仅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茶馆》的作者、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也为他的表演之“活”而非常兴奋,并挥毫亲笔写下一个条幅:“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
为舞台“抽干”生命,将自己名字忘怀
于是之确实成功了,但也为舞台生涯付出了代价。“演戏伤神,要调动自己所有的精神、情感;尤其是激情迸发的戏,非常容易引起脑充血。‘死在舞台上’绝非一句戏言。”唐斯复说。于是之又酷爱喝酒。他们那一辈儿的人在为话剧艺术呕心沥血的时候,所得的报酬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往往一场戏演完就拿到三四毛钱。但他们仍然很高兴,下了班直接去东安市场一家老字号的平民小吃店“馄饨侯”,把钱往柜台上一交,端一碗馄饨,一碟花生米,一杯一毛五分钱的白酒,聊一晚上戏,灵感的火花就在滋味苦辣苦辣的酒杯中冒出来。
“于是之最享受的事就是和编剧们、朋友们一起喝着小酒聊戏。”但多年的饮酒和劳心伤神的舞台生涯也磨损了他的生命质量。人艺老演员朱旭回忆说,1981年,于是之在演《请君入瓮》时已经有些吃力,记不住台词,下来就掉眼泪。
1992年7月16日晚上,《茶馆》在首都话剧院的告别演出。那天,于是之上台前预感可能会出毛病,果然,在这场演了几百场的戏中,他忘了一句词。虽然和他搭档的蓝天野随即补上,观众根本没听出来,但他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谢幕时,于是之脸上又是汗又是泪。他拱手哽咽着说:“最后一场,我没给大家演好。实在对不起。”不少观众涌上舞台,请他在“茶馆演出纪念”的T恤上签名,他写了这样一句话:“感谢观众的宽容。”
自那之后,于是之告别了舞台。他衰弱得非常快,很快就不再能说话,就像是生命的所有情感与力量都已抽干,献给了他的观众和他的角色。唐斯复记得,在文汇报创刊60年的北京文艺界联谊座谈会上,对文汇报有深厚感情的于是之也来了。握笔签名之际,他忽然想不起自己的名字,抬头看着陪同前来的夫人,夫人说:“你的名字是于是之。”他才一笔一划写下了:于是之。
斯人已去。或许他早已将名字忘怀,但在艺术的舞台上会永远定格,这就是于是之,于是之就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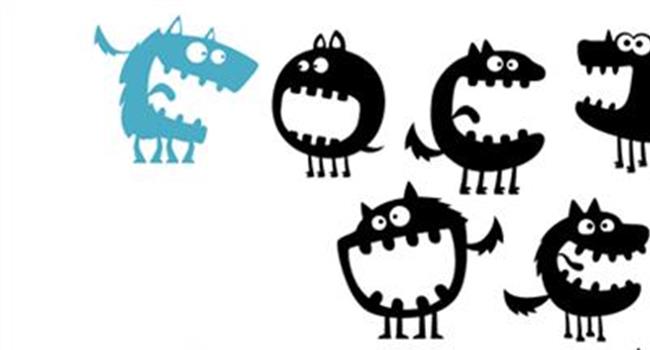






![>卓别林图片 [多图]喜剧大师卓别林珍贵老照片](https://pic.bilezu.com/upload/f/aa/faa36386fbac762ad6a95db1cf316831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