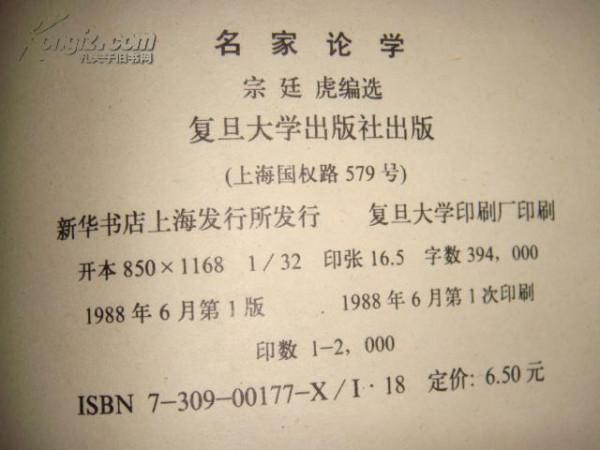萧马与俞平 俞平伯的觉醒与周汝昌的蛰眠
在中国近代新红学史上,俞平伯与周汝昌是胡适旗帜下两位顶尖级的红学大家,也可以说是胡适红学模式的左膀右臂,护法将军。两位大家都是将其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红学研究,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他们所走的红学道路却是极不相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
概括起来说就是:他们都从同一个起跑线出发,但一个走的是觉醒者的道路,终于成为学界崇敬的楷模;而另一个则是一直处于一种“蛰眠”状态,成为执迷不醒、顽固坚持错误红学观念的典型。
胡适先生1921年发布《红楼梦考证》,旗帜鲜明地竖起新红学派的两根重要理论支柱:“前八十回雪芹自传说”和“后四十回高鹗续书说”。紧接着俞平伯先生又出版《红楼梦辨》(1923),对“自传说”与“续书说”进行更加深入的具体论证,使“红楼二说”得以确立。从此这“红楼二说”便成为新红学派的基本观念,以及区别于其他红学流派的重要标志。
对于胡适提出的“前八十回雪芹自传说”,俞平伯先生开初是绝对相信的。他在1921年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得明白:“看你来信底意思,颇有些疑惑‘雪芹即宝玉’这个观念。但这个观念却是读《红楼梦》底一个大线索,若连这个也推翻了,那些推论(按即指续书说的推论)更无存在底价值。
”(见《俞平伯论红楼梦》)在《红楼梦辨》中也曾反复宣称:“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
……既晓得是自传,当然书中底人物事情都是实有而非虚构;既有事实作蓝本,所以《红楼梦》作者底惟一手段是写生。”不难看出,俞平伯写作《红楼梦辨》时,从来没有怀疑过“自传说”的“正确性”;而且他集中笔力论证“高鹗续书说”,也正是在“自传说”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种种推论,可知其当时对“自传说”深信不疑。
然而事隔未久,俞平伯便开始“自悔其少作”,对“自传说”深自怀疑起来了。1925年初,当《红楼梦辨》刚出版一年多,他就在《现代评论》上公开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明确提出“最先要修正的”就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
当时俞平伯的主要想法是:“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而“自传说”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分不清“历史与历史小说的界线”。
他认为“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如果一定要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
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因此,只有打破“自传说”,才能把索隐派“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窠臼完全抛弃”,也才能“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
应该看到,俞平伯虽然最先开始对“自传说”的“修正”,但他此时对“自传说”的否决还是很不彻底的。他直言不讳地说:“所谓修正只是给它一个新解释,一个新看法,并不是全盘推翻它。
”这就是说,在俞先生看来,“自传说”固然是错误的,但如果认为《红楼梦》是“自叙性质”的小说,则不谬矣。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对“自传说”的“修正”,几乎都是沿袭这种认识。例如《红楼梦辨》改题《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他在《序言》中就说过:“《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自传行状看”。
直到他八十高龄撰写《乐知儿语说红楼》,经过对红学研究的深层次反思,才彻底摆脱“自传说”的阴影,明确认识到“我深中其毒,又屡发为文章,推波助澜,迷误后人。
这是我平生的悲愧之一。”他在1986年发表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尖锐指出:“《红楼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
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红楼》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自不能否认此书有很复杂的情况,多元的性质,可以从各个角度而有差别,但它毕竟是小说,这一点并不因之而变更、动摇。
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虚构原不必排斥实在,如所谓‘亲睹亲闻’者是。但这些素材已被统一于作者意图之下而化实为虚。故以虚为主,而实从之;以实为宾,而虚运之。此种分寸,必须掌握,若颠倒虚实,喧宾夺主,化灵活为板滞,变微婉以质直,又不几成黑漆断纹琴耶。
”只有到这时,俞平伯先生才终于弄明白《红楼梦》既不是作者“自叙传”,也不是“自传性小说”,而是出于虚构的(亦即‘化实为虚’的)纯粹的文学作品,从而胜利完成了红学观念的更新。
和俞平伯比较起来,周汝昌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先生的红学研究起步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观点直承胡适和俞平伯,将“自传说”与“续书说”推向极致。周氏的第一部红学著作,是1953年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新证》。
这部书被红学史家誉为新红学考证派的“集大成”之作。周先生在书中宣称,《红楼梦》的根本性质就是“写实自传”四个字;而《新证》的“惟一目的即在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自传说之不谬”。
《新证》将作品“本事”的考证与作者“传记”的考证“合而为一”,以贾证曹,以曹证贾,把历史上的曹家与作品中的贾家等同起来,确指《红楼梦》“原是当年表写的”,“不独人物情节是‘追踪摄迹’,连年月日也竟都是真真确确的”;甚至说“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引者按:即脂砚斋)”,足见《红楼梦》是一部“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书中的人物声口,以致极细微闲事闲话,也皆系实写,而非虚构”。
于是《红楼梦》也就成为曹寅家世和雪芹生平的不折不扣的“写实自传”。
《新证》刚出版不久,即逢“批俞运动”,口诛笔伐“自传说”。周汝昌当即在《人民日报》1954年10月30日发表《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表面承认自己在“考证方法”上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并说“我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处处以小说中人物与曹家世系比附,说小说中日期与作者生活实际相合,说小说是‘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就是最突出的明证。
”其实周先生在骨子里并不承认“自传说”是错误的。
七十年代《新证》再版增订本,虽不得已删除个别刺眼的话,其实还是原来的基本框架。至1986年撰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重申“自传说”,大讲特讲“自传说”如何如何“正确”,如何符合“中华大文化”的精神,只不过已从“生活实录”降调为“自传性小说”罢了。
直到1998年为华艺出版社出版“周汝昌红学精品集”写《总序》,明确概括出“本人的‘红学’观点的核心即是‘自传说’。”这句话,无疑是周先生对其一生研治红学,亦即从头至尾、数十年如一日所坚守的中心观念的自我总结。
在新红学派的“红楼二说”中,“后四十回高鹗续书说”比“前八十回雪芹自传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胡适所确立的“新红学”模式,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腰斩”《红楼梦》的红学模式,其核心问题就是将《红楼梦》拦腰斩断,把一部完美的文学精品活生生地劈成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互不相容的两截,并只把前八十回的著作权判给曹雪芹,而将后四十回定为“高鹗续书”。
从此“曹著高续”说便成为胡适红学模式的总体框架,也因此而造成《红楼梦》艺术整体性的长期失落,使红学步入“反《红楼梦》”的歧途。
论证“高鹗续书说”,是俞平伯从事红学研究的重点课题。《红楼梦辨》就是根据胡适的发明,集中全力探究“高鹗续书说”的。他一开始就说:“《红楼梦》原书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后面的四十回,是高鹗续的。
这已是确定了的判断,无可摇动。读者只一看胡适之先生底《红楼梦考证》,便可了然。”于是他在这个基础上着重解析《红楼梦》的文本,专挑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之间的矛盾,断言后四十回从回目到正文都是“兰墅先生底大笔”。
并进而谴责程高的“序言”和“引言”是“故意造谣”,“全是鬼话”、“谎话”,是“合伙作伪”,“欺罔后人”,“万万相信不得的”;而后四十回作品则是“乱七八糟”,“文拙思俗”,“面目虽是,神情全非”,“文笔拙劣,情事荒唐”,“专说些杀风景的话”,“处处不能使人满意”,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随后“修正”《红楼梦辨》,开始对“自传说”产生怀疑,但仍坚信“续书说”不谬,说“我比较略能自信的,在高鹗续书及其回目这一件事,现在尚然坚持着”,“我们从各方面看,高氏续书的证据着实不少;如竟翻全案,应怎样解释它们呢?”所以直到《红楼梦研究》出版,还全面保留着并加强了对“高鹗续书”的批驳。
并在当时发表的不少文章中,反复重申“高鹗续书说”的旧观点。
1954年的“批俞运动”,“高鹗续书说”未曾受到冲击,相反论家一致肯定了俞平伯“辨伪存真”的贡献,使“后四十回高鹗续书说”几成“定论”。然而正是从这时起,俞先生开始了对“高鹗续书说”的自觉反思。
他在当时写的《读〈红楼梦〉随笔》中,一方面重申“后四十回无论回目或本文都出高氏之手”;另一方面又感到“乾隆末年相传《红楼梦》原本一百二十回”,“跟程伟元的话有些相合”。还进一步指出:“我从前以为这是程高二人的谎话,现在看来并非这样”,“可能是事实”,“这样便摇动了高续四十回的著作权,而高的妹夫张船山云云,不过为兰墅夸大其词耳”。
这说明,俞先生已经意识到“高鹗续书说”有问题了。
1956年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中又说:后四十回“不很像程伟元高鹗做的”,“或系真像他们序上所说从鼓儿担上买来的也说不定”;“高鹗补书只见于张问陶诗注。所谓‘补’者或指把后四十回排印出来,更加以修改罢了”。
1959年在《略谈新发见的〈红楼梦〉抄本》中也说:“在程高未刊红楼梦以前约两三年,已有全书‘秦关百二’的传说,即已有了一百二十回本”,“这后四十回,不很像程伟元高鹗做的”,“大概可以证明,后四十回并不是高鹗一手做的”等等。
1961年在《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中又说:“程氏刊书以前,社会上已纷传有一百二十回本,不像出于高鹗的创作。高鹗在程甲本序里,不过说‘遂襄其役’,并未明言写作。
张问陶赠诗,意在归美,遂夸张言之耳。高鹗续书之说,今已盛传,其实根据不太可靠。”1963年在《谈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中还说:“甲、乙两本皆非程高悬空的创作,只是他们对各本的整理加工的成绩而已。
这样的说法本和他们的序文引言相符合的,无奈以前大家都不相信它,据了张船山的诗,一定要把这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塞给高兰墅,而把程伟元撇开。现在看来,都不大合理。从前我们曾发见即在后四十回,程高对于甲、乙两本的了解也好像很差。
在自己的著作里会有这样的情形,也是很古怪的。”1982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发表王昌定的《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问题》,文末“附记”中说:据俞先生亲属讲,“俞先生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观点,近年来有很大的改变,也开始怀疑后四十回中确有曹雪芹手稿作为依据”。
此时的俞平伯,心中充满深刻的矛盾。他越来越感觉到“高鹗续书说”靠不住,难以成立,又不能彻底抛弃自己付出一生心血的研红成果,真是痛苦不堪。所以八十年代又出现过一次较大的反复:1986年到香港讲学,重申后四十回“相信是由高鹗续写的”老观点;同时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明确肯定“将后四十回从一百廿回中分出,为考证的成果”。
经过长期痛苦的反复思索,余先生终于还是战胜自我,获得新生,临终留下珍贵的遗言:“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从而彻底抛弃旧说,旗帜鲜明地捍卫了《红楼梦》的艺术完整性。
而周汝昌先生则完全相反。周先生从胡适、俞平伯那里接过“高鹗续书说”的“接力棒”继续往前跑,比胡适、俞平伯跑得更远。早在《红楼梦新证》初版中,周先生就以声讨“高鹗伪续”后四十回为中心内容之一,攻击高鹗是“卑鄙”的“败类”,扬言“我们应该痛骂他,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字纸篓里去,不许他附骥流传,把他的罪状向普天下读者控诉,为蒙冤一百数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写实作家曹雪芹报仇雪恨!
”
及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再版《新证》(增订本),对高鹗的批判逐步升级,明确断定“高鹗之伪续,是有后台授意的,是有政治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用续书(冒充‘全本’原著)的方式来篡改歪曲曹雪芹的思想”。
周先生振振有词地编造了一个故事:曹雪芹的《红楼梦》出现以后,统治集团“大感恼怒恐慌”,“这便找到了才子高鹗,干脆将八十回后原稿毁去,另行续貂”。因此,“高鹗的续书,绝非‘消闲解闷’的勾当,也不是‘试谴愚衷’的事业,他从事于此,完全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
从他的续书中反映出来的思想体系来看,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为其封建统治主子的利益服务的。”也因此,高鹗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而现存于世的《红楼梦》则是一部的“存形变质”的“假《红楼梦》”。
为了“证实”上述“推测”,周先生终于找来几条“证据”:1980年发表长文《红楼梦“全璧”的背后》,根据陈镛《樗散轩丛谈》和赵烈文《能静居笔记》等的传说偶闻,经过精心的想象、加工和发挥,断定《红楼梦》的出版是“和珅取得了乾隆的默契,重金延请文士,炮制‘全本’,功成以后,进呈邀请钦准,用武英殿聚珍版(御赐嘉名)的势派,予以印行——所以都下立即轰传,风靡一时。
”换句话说,在周先生想来,《红楼梦》的问世,是乾隆指派和珅,重金聘请“文化特务”程伟元高鹗,“删改”前八十回,“抽撤”原著后半部,而后“伪续”四十回,“凑成全璧”,由御赐武英殿(而不是萃文书屋)版行的。
直到近年,周先生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述他的这一“高鹗伪续”论。例如他在《红楼小讲》中说:“这部《红楼梦》印本并不是曹雪芹的真全稿,只不过是由程伟元、高鹗等人伪续了后四十回书,而托名号称‘全本’的。
而这个伪全本的炮制和印行,本是有政治背景后台的,并非一般文人好事者的偶然‘遣兴’。”又如他在《红楼十二层》中也说:“本人强烈反对歪曲、破坏雪芹原著真笔、大旨要义的任何做法。
我的研究严格限于八十回古抄本即接近原笔的本子。一百二十回假‘全璧’是个有政治背景的文化骗局。诚望‘看官’的明断,给沉冤文海二百数十年的雪芹平反,给这位中华文曲巨星申冤吐气!”再如他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中还说:“《红楼梦》是乾隆末年和珅‘呈上’的,我立即想到:和珅就是那位‘名公巨卿’无疑了”,“伪续后四十回是阴谋(也偷改前八十回原文)。
所以‘全本’一出,士大夫‘家置一部’,天下风行——是官方的事啊!”并举出所谓“硬证”:俄国人卡缅斯基都说程本是“宫廷印制”的,可见“程高本正是武英殿修书处的木活字摆印的”,云云。
我们在上面粗线条地勾勒出俞平伯与周汝昌两位红学大家,在新红学派的中心观念“红楼二说”上,几十年中所走过的大致历程,不难看出,他们的路向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俞平伯先生所走的道路,很明显是一个觉醒者的道路。
而且,他对“自传说”与“续书说”的反思,都不是出于外在的压力;也就是说,他不是在遭到别人质疑、诘难乃至“批判”的情况下,才“检讨”自己,被迫抛弃原有的观点。相反,他完全是自觉地进行自我解剖,自我超越,不断更新自己的红学观念。
每当他发觉自己的观点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敢于自觉地进行“修正”,自觉地“忏悔”,表现出一个大师应有的学者风范。诚如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所说:“小师形而下,重实,大师形而上,尚虚。
求实,则重眼前,为适应利害,必然会训练出许多小聪明,小机智;尚虚,则高空邈远,浮想联翩,有所思考,便有所颖悟,心灵的自由要高于物质的一切。”又说:“小师的目光,常常集中在饭碗之内,大师的视线,有时就会超越到饭碗之外。小师生怕饭碗打翻,饿肚子,大师哪怕饿肚子,敢扔掉饭碗。这就是为什么俞平伯敢于否定自己,敢于与从前的我决裂而毫不顾惜”(《楼外谈红》)。
然而,俞平伯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博大胸怀,却很引起一些人的误解。例如周汝昌先生在《还“红学”以学》中就这样评论道:“俞先生最末期的表现,也很奇特,例如:(一)他自己批评说,早年的‘自传说’观点是错了;(二)他最后留言是:把《红楼梦》分成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一种‘犯罪’——这和他在《红楼梦辨》中的论点也正是针锋相对!
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覆覆。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因此我们评价起来也感到困难。
”周先生准确指出俞平伯“末期”的观点与早年“针锋相对”,事实确实如此。俞先生正是在“自传说”与“续书说”两个基本观念上,敢于自我否定、勇于纠正错误的。
但周先生说俞平伯的看法“表现奇特”,“反反覆覆”,“很难捉摸”,“评价困难”,则很明显带着浓重的“贬义”色彩。在周先生看来,俞平伯对“红楼二说”并无“确切”定见,仿佛一时说对,一时说错,让人“捉摸”不定,值不得“评价”。
其实俞先生对“红楼二说”从肯定到否定,完全是有迹可寻的。例如“自传说”,他“修正”最早,这主要是因为他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着眼,发觉‘自传说’无论如何讲不通,不符合《红楼梦》作为“小说”的特质,且与索隐派的“猜苯谜”无异。
所以他曾对余英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二十年代以后,我根本就不写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文章。”(见《红学世界》)这分明是出自一个文学大师的俞平伯先生的肺腑之言。
鉴于俞平伯对“自传说”的否定,有理有据,精辟透彻,已获得人们的普遍赞同,至今仍坚信“自传说”的人也不多见,本文即不再细加评论。这里着重要说的是“高鹗续书说”。俞平伯对“续书说”的怀疑是从“证据”开始的,因为他终于弄明白这是一个“实证”问题,而不是一个“推测”问题。
他经过长期、反复的甚至痛苦的思考,越来越感觉到“高鹗续书说”的“根据不太可靠”,单凭张船山一个可能出于“意在归美,遂夸张言之耳”的“补”字,是根本不能为“高鹗续书说”提供硬证的。这才斩钉截铁地得出“腰斩《红楼梦》有罪”的结论。
周汝昌先生对俞平伯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很不以为然。他从来就不理解俞平伯内心世界的矛盾、痛苦和挣扎。他以自己之心度俞之腹,奚落俞平伯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实际上不外乎是为了表明自己“坚持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周先生的确是这样,他的许多红学观点,几十年来几乎一直受到不少学人的质疑和批评,但他都置若罔闻,不但从不接受,甚至耿耿于怀。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例一:1958年林语堂先生发表《平心论高鹗》,对胡适、俞平伯和周汝昌等鼓吹的“高鹗续书说”提出尖锐批评,指出他们“高续说”的“证据不能成立”,并将周汝昌列入“以个人之好恶,定书之真伪”的“主观派批评”加以驳斥。
林文肯定周氏《红楼梦新证》“获新材料,整理之勤,用心之细,自有它的地位”;同时指出周氏“是不配说高鹗的人,因为他是裕瑞一系统来的,只是恶骂,不讲理由,而所恶骂,又完全根据平伯,不加讨论的”。
并认为“胡适俞平伯尚保存学者就事论事态度,斥其作伪,却同时称赞高鹗补作之极端细心审慎。到了周汝昌,又变成了高鹗一味糟蹋曹雪芹到不可收拾的田地”。林语堂的批评,引起周汝昌的“愤怒”,他在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的“重排后记”中,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批判“洋式老爷”林语堂:“只因我批了高鹗,使他极大不舒服,在文中对我破口大骂,并且辱及先人。
这可以证明,在林老爷的感觉上,我批高某,却比批了林某的祖宗还可恶。”
例二:1980年第6期《艺谭》发表严云受先生的文章《高鹗续书功过辨——〈红楼梦新证·议高续书〉质疑》,对周汝昌《新证》(增订本)“议高续书”部分提出全面质疑。严先生从:一、高鹗百二十回本是一部“存形变质”的假《红楼梦》吗?二、高鹗续书使《红楼梦》“才子佳人化”了吗?三、鲁迅先生是怎样说的?四、高鹗续书是“上命差遣”吗?等四个方面,对《新证》诋毁后四十回提出批评,指出周先生认定“百二十回本是高鹗当时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对原著进行歪曲、篡改的产物”,而后四十回则是“高鹗拿了封建统治者的银元之后蓄意炮制的遵命文字”等观点,都是十分错误的,缺乏事实根据的,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经过充分的说理批评之后得出结论说:高鹗续书“基本成功”,“功大于过”,应该重新给予评价。由于严文是从“高续说”的基点出发的,只是不赞同随意贬低后四十回,似乎并未引起周先生的反感。
例三:1981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发表王昌定先生《读〈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与周汝昌先生商榷》一文,对周先生咬定后四十回是乾隆、和珅“重金延请”程伟元高鹗“伪续”的“政治阴谋”的观点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周先生根据陈镛、赵烈文等人的“道听途说”,“连‘事实’都够不上的记载”,再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断”,对程高和后四十回进行“望风捕影的定罪”;并对周文的“想当然”成分逐条加以分剖,恳切地提醒周先生:“做学问应有的态度是: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不能凭借只言片语,作想当然的揣测,尤其在做政治结论时要十分慎重,对古人做政治结论更应当加倍慎重。
”最后还热切希望周先生“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摆脱‘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派考证方法的影响,一方面能够从曾经弥漫于学术思想界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彻底解放出来”。
对于这些善意的批评,周先生照例“嗤之以鼻”。他曾在《桐花凤评语与探佚学》一文中借题发挥:“最奇的是某刊物登出‘商榷’文章,说我是用‘四人帮’的‘极左’的罗织罪状的手法来诬陷程高伪续者。
”(见《红楼梦与中华文化》附录)且至今念念不忘:“有人竟发文说我是‘极左’的‘罗织罪名’!”(《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以上只是随手举出的三例。就笔者所见所闻,对周先生的红学观点做出指名的或不指名的、公开的或背地里的批驳者,实不在少数。周先生对别人的意见,要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屑一顾;要么冷嘲热讽,奚落挖苦,反目相讥。
总之是从来不肯听取别人的任何哪怕是善意的批评,从来不曾认真解剖过自己,并对自己的红学观点稍作反省。不管别人怎么指出他的谬误,他照样侃侃而谈,自说自话,婆婆妈妈,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翻来覆去地、并且津津有味地重述着他的那些悬空的“猜想”和“揣测”(诸如什么“曹雪芹原著108回”呀,“警幻情榜108位脂粉英雄”呀,“脂砚即湘云”即曹雪芹的小老婆呀,等等)。
就算是“谎言”吧,只要“重复一千遍”,难道你还不相信是“真理”吗?无论是“自传说”还是“续书说”,他都自视为“绝对真理”,坚信其“绝对正确”;你要是持不同见解,他就说你不懂“中华大文化”,不懂曹雪芹“原著”的“真精神”。
他近期提出的与俞平伯“对着干”的新口号是:“反伪续反到底,永不回头”!(《和贾宝玉对话》)口号固然很响亮,殊不知这个口号的前提条件却是“伪续”。你“反伪续”,首先得拿出过硬的证据来证明后四十回确实是“伪续”,又是谁的“伪续”?《新证》抄了几百种书(就像俗话说的“抄一人,是抄袭;抄众人,成学者”),有哪一种能构成“高鹗伪续”的“铁证”?难道只凭“一口咬死”,就能给“高鹗伪续”定罪吗?直到最近,周先生做出总结:“我则相信张问陶在《船山诗草》中所记的一则诗注,明言《红楼》后四十回皆高所补。
……且张是高的内兄,其姊(?)张筠嫁与高鹗,两家至亲,备知底细。”(《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说来说去,不就是胡适早年提出的张问陶那个模棱两可的“补”字吗?这且不说,单看2001年四川蓬溪县发现《遂宁张氏家谱》,已经确证船山之妹所嫁的“汉军高氏”并非高鹗,而是一个名叫高扬曾的人(见《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3辑),周先生还在重弹“两家至亲,备知底细”的老调,又能“证明”什么呢?周先生号称“考证派”,辛辛苦苦“考证”了几十年,其实什么问题也没“考证”清楚,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大堆“推测”。
就像严云受先生所说那样:“历史应当有事实根据的,无法证实的推测显然不宜于用来作为评价人物、评价作品的论据。
我们仔细地阅读了周汝昌同志著作的有关部分,希望能看到他为这个论点提出的证据。最后都失望了。”(《高鹗续书功过辨》)
与周先生的口号“反伪续反到底,永不回头”相对应,俞平伯的口号则是“腰斩《红楼梦》有罪,保全《红楼梦》有功”!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截然相反的口号,也是代表两位红学大家的不同精神境界、不同胸怀气质、不同学术品格的口号。
环视百年红坛,俞平伯这个口号,只有俞平伯敢说,别的任何人不敢讲。这是一个保卫《红楼梦》的口号,保卫全璧程本的口号,保卫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瑰宝的口号。有人说,俞平伯的临终留言是“病中梦呓”,“走火入魔”,这未免太不理解俞先生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气质了。
我们赞同这样的说法:“这毕竟是用笔写在纸上”的“书面语”,“不但意思完整,连语病也没有”,“不宜于一笔抹煞”。
(王湜华《俞平伯的后半生》)有人又说,认为俞先生的遗言否定“高续说”,是随意“猜测”、“想象”和“发挥”;那么请问:所谓“腰斩”《红楼梦》,不就是指人为地把《红楼梦》劈成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两截吗?这不是否定“高续说”又是否定什么呢?
我们认为,俞平伯先生的临终遗言,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俞先生的遗言,是他对其一生研红的自我总结,表明他已经自我觉醒;有这么一句话,他一生“腰斩”《红楼梦》的所有“罪过”,都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谅解。
另一方面,俞先生的遗言又是有针对性的,这在我们看来,主要就是针对周汝昌先生“腰斩”《红楼梦》“到底”的错误倾向而发的。在当今红坛上,数周汝昌先生“腰斩”《红楼梦》的匕首最快,“反程本”亦即“反《红楼梦》”也最为坚决彻底,而且始终执迷不悟,因而他之于红学研究,不仅无功,相反和胡适、俞平伯一样“有罪”、甚或“罪加一等”的。
由于周先生的“高鹗伪续”论还有一定市场,人们更期望他能够猛醒,争取从新红学的误区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