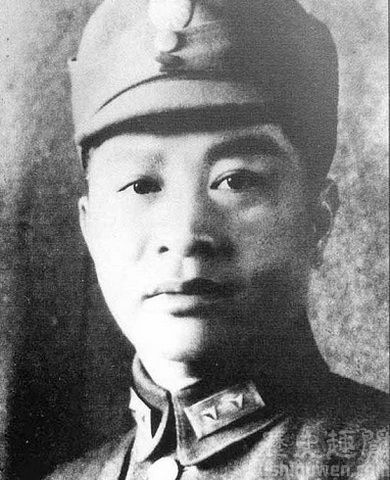叶挺夫人李秀文 叶挺与夫人“准女兵”李秀文在皖南生活一段罗曼
“另一方面,党中央为加强四军领导,陆陆续续从延安调来大量的干部到军部工作,而这些同志当时在八路军机关和部队里,大多数也都是师、团、营、连级干部,自然都要给予合理的职务安排他们,以便掌握军政权。这也是项副军长在部队整编前向党中央提出来的。
由于四军组建之初部队兵员少,必然挤掉很多当年在南方打游击的原红军干部职位,他们对军部这种安排很不高兴,不好说叶和项,而是说中央这种安排就不对,就是不信任我们,长征前我们被抛弃了,现在我们又成了多余的人。
比方刘厚总,就是后来杀害项副军长和周副参谋长的叛徒。刘参加四军前,曾在湘南游击队当队长,手下号称三四百人,在湘南一带名气很大,当地那些替国民党政权办事人只要听到他的大名,心里就寒。
他枪法准,个头高,会武功。刘经常在军部吹嘘,说有一年国民党部队有一个营剿他们,他叫大部队先走,自己仅带八九个人担当阻击任务,因为子弹缺乏,他吩咐留下人员专门给他装步枪子弹,他一人躲在一棵大树后,一连打死二十个敌人,吓得敌军从此再不敢向前了。
整编后,他的部队改编为军部特务营,他仅任副营长。当时部队条件差。军部进驻南陵县土塘时,特务营承担保卫军部机关工作任务,自然也驻进土塘。土塘是个小村,一下挤进那么多人,其条件之差可想而知,睡在四面透风的破屋里,每人一双布鞋穿烂了,只有穿草鞋,而且还要亲手打;每人二套军装,土布单薄;吃的是大锅饭,八九个人围在一起,一个木盆将着季节寡菜汤各一,大多数像猪食,有时苦的连酸咸菜也难吃上,就是这样每天还要东奔西走,深入农村第一线进行新四军抗战宣传,组织民众团体,团结抗战,十分艰苦。
想当年他在山上打游击,那可是老子天下第一,有肉有鱼,晚上还可以招来女人陪着睡觉。现在到了新四军,这些条件自然没有了。
“于是,他在湘面打游击时养成的坏毛病,自然而然地也会经常犯,嘴馋了,他指派营部警卫人员抓老百姓鸡烧了吃,到老百姓菜园地里拔菜吃(当时许多游击战士也有这个习惯),还随意打骂士兵等旧的习气。
“军部在南陵土塘时,刘厚总随军部邓副主任到南陵县政府与国民党搞统战工作,闲来无事,见县政府大院里一个女子正在读书,又是一个好看的学生女子,上前说了几句话,就动手动脚,乱摸了那女子,这个女子正是县长的千金,哭着向县长说了此事。回到军部,项副军长一气之下将他遣送回家。
“刘厚总当时还不在呼,说走就走,老子到了哪里也会有饭吃的。刘果然离开云岭走了,先回湖南,刘小的时候也是穷苦出身,父母亲死的早,从小由其唯一姐姐养大,刘在姐姐呆了一个多月,觉得今非昔比,面对全国抗战形势,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上山游击,占山为王,成一方小诸侯了,但要是在家种田,做工又实在不甘,左三四想最后觉得还是出去革命才有出路。
接着他去长沙找徐特立同志,后被徐安排到延安学习。刘本想在延安呆下去,不久便认为延安没他一点地位,他没有多少文化,延安更没有熟悉他的人,他无法在延安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于是,他乘延安遭到一次日军飞机轰炸时私自出逃,他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办事处仍安排他再次回四军。
项没有办法,考虑多种因素,先让他到在军部教导营学习一段日子,接着分配军部副官处任副官。这样他更加没有权利了,心里依旧有一股火。”
“我记得许多游击老战士只要聚在一起,就会说延安干部怪话,经常发牢骚。胆子大的,趁着酒性直接找项副军长论理,说好位子都让他们霸占了,延安不相信我们,你当政委的难道也不相信我们的?难道就不能替我们说说话?老战士们喊项叫政委。
“延安同志也有苦恼,同样也是牢骚满腹。偶然间,我们与红军游击队干部和战士相聚一起说事,说着说着,双方就会吵起来。延安同志对游击战士理论时总是这样说:我们在延安,谁不是师团营连级?到了这里降了一、两级任职,有的还降了三级,我们心里好受吗?被叶军长枪毙的那几人就是因为不满四军安排,这才老想着要回延安。
叶道志在延安部队曾任师长,师政委。他是从延安抗大学习时被才选调来的,想不到在四军仅当为副团,实质仅为营长降了几级,我们心里能气顺吗?而且当时人多,人与人之间相互不熟,军部机关又老是移动,驻无定所,生活条件自然要比延安差多了,尤其不准沾女人边。老实说,心里的气也是很多的。
“一开始,大多数游击战士行为说话很鲁莽,整天一副吊儿浪当的派头,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流民散乱气息,延安同志很是看不惯,总想要以正规军的方式管理他们,教育他们。但他们的抵触情绪很大,比方最简单的上早操,新参军的战士都已经立队齐刷刷站在操场上了,而不少老战士还在呼呼大睡。
于是,上下级之间经常发生争吵。在延安正规军下级与上级发生争吵的情况一般是决不可能的。但游击队战士就敢吵,因为他们有资格。这种现象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八月,军部从南陵土塘村移驻皖南泾县云岭罗里村和中村,军部总算得到国民党三战区的认可不再移动,才相对安顿下来。
通过一段时间强化整训,军部领导人又积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情况这才渐渐趋向好转。
另外,这时期也是四军大发展阶段,特别是陈老总带部队到达苏南,在苏南广大城乡间掀起了一股强烈的要求参加四军抗日热潮,由于去延安路途太远,到皖南参军就显得十分方便。更多的是仰慕叶军长的名气。于是,大江南北许多知识精英们抛弃城市舒适的生活纷纷来到云岭参军,加上城市众多参军知识青年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文明的生活方式,也给红军老游击队战士产生无形的压力。
同时新兵增多,那些老游击队战士相应有了一官半职,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老革命,是要以身作则做榜样了,于是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习,情况逐渐好起来。
“你见过叶军长的夫人吗?听人说军长夫人李秀文好看的不得了,是这样吗?”
问话的是夏兰。她是个胖呼呼的女孩子,颧骨有点高,眼睛很黑,鼻沟两侧有几颗雀斑。她不识字,原先在上海一家纺织厂做女工,但她性格泼辣,嘴皮子利索,说话直来直去。
桂英笑笑,没有责备夏兰突然间的插话,这是不礼貌的。桂英不喜欢说话时别人胡乱插嘴。
C:叶挺与夫人“准女兵”李秀文在皖南生活一段罗曼史
桂英说:
我当然见过,而且不至一次。因为叶夫人曾两次跟随叶军长来云岭的,第一次是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二月底三月初,她伴随着叶陪同周恩来副主席来云岭视察的。最后一次是在民国二十八(1939)年秋,她从澳门送枪械来云岭的。
那次来云岭,她大约住了小半年。身为女人,她将自己心爱的孩子放在澳门,何必老是跟着丈夫东奔西走呢!为这事我们女兵经常一起悄悄议论,最后一致认为军长在四军里工作不开心,她是专门来皖南陪军长的。再说男人总要有个女人在身边的,不然会出事的。
叶夫人在军部住的时间较长,时间一长不仅军部上下人人谁认识她,就连军部附近老百姓也认识她。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多岁吧,听说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人还是那么漂亮苗条。她天生一副瓜子脸,白白净净的,这样的脸型,是我们大家公认最受看的,一双黑黑明亮的眼睛,很大很大像月亮,一天到晚水汪汪的,她要是一笑,两个小小的、浅浅的酒窝,有点像小林的酒窝,圆圆的特招人怜爱,她不论往那儿一站,总显得文静、优美、生动、亭亭玉立、端庄秀丽。
任何人见到她,心情再不好也会舒服的。
她喜欢同叶军长一起到处走走。叶夫人气质好,衣着风格,穿着打扮,自然同我们一天到晚穿着灰军装的女兵有天壤之别。她随叶尽常去中村教导总队,只要一看见她来了,我们女兵就像火一样,呼啦一下围上来,同她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十分开心。
有时见军长不在身边,我们会私下缠着她,要她讲讲她同军长是怎么认识相爱和结婚的。对这事她倒挺显得大方,笑笑地对我们这样说:“你们这些小丫头们呀,是不是想从我这儿取点恋爱的经验呀!好,反正我老了,也不怕出丑。我说一点儿。于是,大大咧咧地说上一堆趣事。
她说:她年轻时也当过兵。北伐时,军长在肇庆组建独立团,她在西江政治研究会工作,穿着军装同你们一样挺俊俏。不过在四军,我只能算一个没穿军装,没有入籍的女兵了。
她说:我是民国一十二年(1923)同军长认识的。一个女子爱上一个男子是要一点缘份和机遇的。那一年,军长担任孙中山先生总统府警卫团二营营长,有一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到警卫团团长李章达家里做客,刚好那天我身着水红色的短衫、腰系葱绿色长裙、白色的丝袜、米黄色的皮鞋、留着一头整齐而乌黑的秀发在李团长家对面楼上逗我的侄子玩。
于是,无意中我让军长发现了目标。当时军长见我从楼上提着长裙下来,宛如天仙一样的姿态,一下子就把军长迷住了,他就那么呆呆地瞅着我抱着侄儿接着上楼不见了。
李团长目睹了一切。看见了这一切,笑嘻嘻地上前拍拍军长的肩膀说:“希夷,这姑娘不错吧!”
当时,军长脸红了:“团长,你都看见了?”
李团长点点头说:“你也不小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喜欢不喜欢那个姑娘?要不要请我当红娘”
军长脸更红了说:“团长,你不要耍笑我了。”
李团长认真了:“我说的可是真话,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女孩子。她叫李秀文,目前是执信中学的一名学生。她的父李少村是我的同乡好友,我们都是东莞人。清朝未年,李先生曾做过小官,过去攒了一些钱,民国初年开始做生意,老人虽然是商人,但知书达理,对革命也很支持,多次拥护过周副主席和聂荣臻。老人有两个女儿,秀文是老人的次女。”
于是,从那时起,军长心中记住了一个我。李团长说到做到还真一心想当红娘,后来果然几次带军长到我家做客。我父亲知道军长的心思后,心里也很满意的。那一年我十六岁。我父亲鼓励军长:一个年轻人要好好学习,多多学点本事,将来有出息了,还愁没有女朋友?
对于军长上门求爱,我是知道的。老实说我从见到军长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定要同这个英武帅气、神采飞扬的军官联在一起了。那天夜里,我失眠了,兴奋和激动像一把毛刷折磨了我一夜。这么说吧,我已经情赎初开了,我已经成人了,我知道什么叫恋爱,什么叫情感。虽然觉得我的父母并没有当着军长的面,要把我许配给他,但从父亲欣赏军长表情和眼神里,我分明感受到父亲暗中会有一天把我许配给这个叫叶挺的军人的。
因为从那以后,我父母并不反对我私下同军长交往和约会。并且我还多次把军长约到家里来做客。父亲常常同军长在一块谈论天下大事,母亲和我在厨房里为两个男人做好吃的饭菜。有时父亲与军长下围棋,我会小鸟依人般坐在军长身边观战,还不时地为军长出谋划策。
有一天,李团长同军长私下谈心,李团长问军长同我之间一事可有下文?军长说,秀文说她没意见,只是她父亲一直没有松口。我想这事要办成和话,你当团长的还要亲自出马几次才行。
李团长当仁不让。果然约见我父亲直言一说,父亲也直言相告:等到叶挺当了像你一样的官,我会给足你面子的。真想“若要洞房花烛夜,必须金榜题名时”啊!。
北伐开战前,军长从苏联回国前,就已经在苏联悄悄地参加了**。回国后,军长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伐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军长回到肇庆筹建独立团工作时,我父母果然不失言,同意我参军,到军长身边协助他工作。民国一十五年(1926),军长觉得他与我之间的婚事也该有个结果了。
这一年二月间,我俩在独立团团部所在地肇庆督办署内举行了婚礼。由于方方面面条差,婚礼相当简朴,只有双方的亲友、同事和独立团连长以上的军官参加,另外还来了一些机关团体的代表一共七十多人,前来参加我们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
征婚人是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刚刚宣读完祝婚词,蒋委员长披一件拿破式的斗篷和陈诚出现在婚礼场上。委员长笑着地上前对军长说:“希夷,我来迟了!恩来,你也给我保密?”
周副主席笑着对蒋委员长解释:“司令您公务忙,我怕您走不开,所以我就没有告诉您了。”
蒋委员长说:“我再忙碌,希夷的喜酒,我还是要吃的。”
周副主席对蒋委员长说:“司令既然来了,您讲几句话吧?”
于是,蒋委员长在大家的掌声中这样说:“我首先祝贺叶挺和李秀文女士结为秦晋之好,新婚快乐。我这次来,由于突然得知今天是我们的叶团长大婚日子,也没有准备什么贵重东西送给这一对新婚夫妇做贺礼。刚才,我和陈诚路过一个古董店,见这一对花瓶很好,就买下了,且当作礼物,送给这一对新婚夫妻做个纪念吧。”
话音一落,陈诚指挥卫士将一对明未清初的花瓶送上。花瓶绘有凤凰戏牡丹图,虽然年久远头依旧十分艳丽,光彩夺目,上面书有“百年合好”的行书。
当时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委员长,对一个刚刚新任职的团长竟送如此大礼,的确让在场的众人对军长刮目相看。军长和我当时也很激动,甚至有些意外。我们小夫妻双双给委员长献上一怀红酒对委员长说:“司令,谢谢您!这一怀酒是我们夫妇对您的一片敬意,请您赏脸。”
在众人掌声中,蒋委员长对军长身边的我笑着说:“新娘子的酒,我一定是要喝。”
喝完。蒋委员长在众人的掌声下说了一番话:“今天,我为什么在十分繁忙的公务中抽出时间赶来参加叶团长大婚?第一,我原先的确不知道今天叶团长结婚日子,我所以来迟了,请各位原谅;第二;我们马上就要北伐了,我要借这个地方告诉大家一个喜讯,我们已经决定,这次北伐,我要叶挺独立团担当四军先锋。
我曾多次观察过独立团各种军事训练,这次北伐战有独立团承担开路先锋,我想我们的北伐一定能够取得大捷的。最后我祝贺叶团长和秀文女士新婚美满幸福;祝贺叶团长在北伐中多打胜仗,为国立功。”
新婚不久,我和军长双双回到惠阳老家,去见见我的公婆,还有我的大姐黄春,这是必须要去的。黄春姐并不是我姐,出不是军长的姐,大姐是军长的前妻。因为大姐是军长父母包办的,军长一直不喜欢她。虽然军长曾在父母的强迫下同大姐结过婚,但新婚几天后,军长就离家出走考进保定军校。
军长任孙先生的总统府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兼一营营长时,曾回家一次同大姐离了婚。婚虽然离了,但大姐哭着一定要军长答应她一个条件,说她从今往后虽然不是军长妻子,但她死也不想离开叶家。大姐说:我进了叶家的门,生是叶家人,死了也是叶家鬼。当时军长征求我的意见,我没反对,我当时从心里还很感激大姐。因为从今以后大姐在老家可以替我去尽做一个儿媳的孝道。
北伐战争终于在民国一十五年(1926年)七月打响了。战斗打响前,我由于身孕便离开部队回到娘家。住在娘家日子里,我的心却一直悬着,像一只称砣时刻系在军长身上。虽然不断耳闻军长传来汀泗桥、贺胜桥、平江战役以及攻克武汉等一列系的大胜喜讯,“叶挺独立团”威名震荡了全国,但作为妻子的我,内心总也轻松不起来。
战争是残酷无比的,尤其作为先锋作战部队,死得人会更多,许多好战友都牺牲了,仅武昌一役就有曹渊等十八名排以上的军官和一百七十三名士兵牺牲,至于负伤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独立团出征前有二千多人,北伐结束后只有不足一千人活下来。老实说,我不知多少次背着家人哭过。我现在是妻子,一个做妻子的女人谁不想同夫君长相厮守?过一个女人的平静日子,但我不仅不能阻止军长,我还要支持他,我在自相矛盾只有听天由命。那些年军长跟随孙先生很多年,东征陈炯明、北伐吴佩孚、孙传芳。男人之心抱负远大,我做女人唯一的就是时刻牵挂着军长。
原以为北伐结束了,国家安稳了,不料国共两党又开始翻脸。两党你死我活、真刀实枪相互又打起来。军长作为一名**员,自然不会站在蒋委员长一边。**在南昌举行起义前夕,军长被临时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官,而起义军有关许多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并不知情,起义因为仓促失败后,军长又在广州发动起义再次与国民党宣战,不料起义再次失败。
事后,军长奉党的指命去苏联学习,在莫斯科军长受到某些同志的打击,把南昌和广州起义的失败原因统统强加军长身上,军长有口难辩,军长更不善辩,又不是那种喜欢推卸责任的人,一气之下,军长离开了莫斯科回到家里。军长回家当时对我来说,我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夫妇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这一晃就是十来年,这十年我们在国内和国外到处游山逛水。去过法国,但在德国呆得最长,我们喜欢德国的风景,在那里结交了很多朋友,骑马、打球、游泳、散步,与友人聚会,我们很开心真,有点乐不思蜀的意思。
这期间我们有了扬眉、正大、正光、正明等儿女……这一切真是我所想得到的。我父亲自从内地迁到澳门经商后,生意上更好。记得德国期间,我们曾经开过饮食摊,其实主要上觉得好玩。偶然也为家里的生意采购一些货物,从德国或者从法国发往澳门,比方药品,器械等。每次都能赚一些钱,我发现军长也很会做生意。
我曾多次夸奖军长:希夷,想不到你做生意也挺精明的,如果你要是这样做下去,一定比我父亲更出色。
军长笑了笑,他这样对我说:其实,你还是不了解我啊!
我能不知道军长的心吗?俗话说知夫莫如妻。不过是我不想点破而已。我知道别看军长整天同我和孩子们快快乐乐、说说笑笑,一旦平静下来,他的心就不会平静,他的心一直在飞,飞到中国内里。军长原先的信仰并没有泯灭。很多的夜晚,我们看着明月,我与军长丈夫说到这些,军长先是长叹,接着是检讨自己,为什么就那么轻率地离开自己的党呢?
在澳门,我们住在贾伯乐提督街七十六号一幢小楼里,这是我父亲赠给我们住的,门前有一个小花园,十分安静,在这抗战烽火的年代里是最适合避难地。家里时常有客人来,最多的是国民党一些军政要员,同时也军长老同学、老熟人,老战友,我记得有几次来人说是奉蒋委员长指示叫军长到他身边做官。那时候,国民党正在清剿中央苏区。军长对来人说:你们同**打内战,我不想这样做。
军长送走这种客人回来,总是坐在沙发上抽烟一言不发,默默地喝着剩下的茶,显得很沉重。我过去安慰军长,军长抓着我的手说:秀文,我虽然不是**员了,但我过去是啊!北伐时,我与战友们每次作战前,我们都会在自己的遗书上写着:‘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牺牲’的豪情壮语,他们要为党无私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现在要是参加了国民党,我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吗?
有一天,军长侄子叶钦和来澳门,军长听说钦和在国民党军中任职,军长很生气:‘你要是没有饭吃,就去跳海,也不要为国民党做事。’
军长曾给阳翰笙写信,说他想同周副主席见见面。还多次写信邀请过去战友和同事来澳门叙旧。民国二十六年(1937)‘卢沟桥事变’一爆发,军长马上从澳门奔赴上海,竟外之中真得与周副主席偶然相见了,周主席问他是否就任新四军军长一职时,军长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了。
一开始,这消息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竟味着是一桩喜事,我高兴不起来,凭感觉我认为现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不可能再像往年,现在的合作是被日本逼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是很深刻的。我曾经对军长这样说:希夷,你又在铤而走险啊!你要是任了四军军长,你在国共两党里面都没有根基,你行吗?
军长安慰我:我是在为国家,是为抗日、是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我不是为那个党作战的。我怕什么?目前,我任何党派也不想参加,我不要任何根基,就像当年北伐一样,带兵打日本。
我还是坚持说:你现在手下的四军将士,可不是当年你的那帮患难与共的兄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