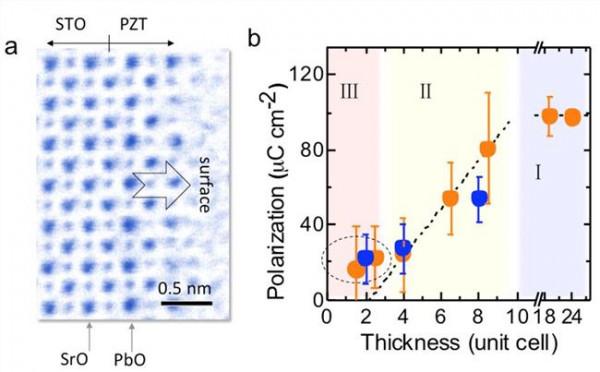万献初易经 万献初:国学名师与经典背诵——并记石声淮先生一二事
本科毕业二十多年了,我们华师七七级中文系的同学聚会,主要话题是怀旧,尤其是有关老师和课堂的趣话轶事,总是津津乐道,兴味盎然。酒后评选当年授课教师最有趣的话语,排第一位的是先秦文学的石声淮老师讲《诗经》时点同学起来背名句子,同学不会,老先生总会摇头晃脑地慨叹:“书生哇!
书——生——哇!” 我们的书读得很生,而先生的书实在是读得很熟。先生多才多艺,会多门外语,钢琴弹得好,绘画也很精,所讲古典文学经典都烂熟于心。
他给我们讲课从来不带书,有时带几张卡片也是用英文、法文写的。讲课时先大段地背诵,然后边讲解边信手在黑板上画速写,数笔画过,人或物神形毕肖,直观而形象,易懂而有趣。 先生重视、强调背颂经典,背书是他的基本功课,数十年如一日。
他曾要求自己的研究生每天早上必背诗文,下午亲自检查,一一背来,别想蒙混过关。背书是有方法的,先生一日傍晚散步,顺便到我们住的宿舍(二食堂对面二楼左边第一间)聊天,告诉我们,背书先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反复朗读,边读边加深理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理解透了也就背会了。
“会背书者背结构”,是先生的经验之谈。篇下有章,章下有段,段有层次,层次由句子组成。由句到层,由层到段,由段到篇章,由零到整,有步骤有规律,容易背熟,且记得牢实。
石声淮先生有家学渊源,兄弟三人都国学功底深厚。石声河,解放前任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教师,与蔡尚思等曾为同事。石声汉,早年饱读诗书,青年时期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后任西北农学院教授,撰写农学专著达15种之多。
石声淮先生是著名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的乘龙快婿,也就是钱钟书的妹夫。
华师广传钱基博选石声淮作女婿的轶闻:钱基博的女儿钱钟霞美丽端方,二十五六岁还侍伴老父而未论婚嫁。这时钱基博的得意门生石声淮也是单身,但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然老师却非常喜欢这个才华出众学生。一天,钱基博在家里一手牵过女儿,一手拉过石生淮,把俩人的手放在一起,郑重地宣布俩人结为夫妻。
钱钟霞本不情愿,但不敢违抗父命,只好依从。能得钱老夫子如此钟爱,可见其国学功底和才气非同一般。 其实背诵经典是国学大师们的基本功,也是华师教授们的传统。
章太炎少年烂熟于群经,黄侃在北大背诵、讲解《文选》形成“黄调”,钱玄同五岁就在乃父严格规定下每日背《尔雅》多条等等,是众所周知的故事。建国后的华师,有家学渊源深厚、熟读群书、数年不下藏书楼的张舜徽教授等国学名家,在背诵经典方面最突出的,是文革前中文系的系主任、元明清文学专家方步瀛先生。
他是1953年院系调整时随原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先生调过来的。有关方步瀛先生背诵经典的趣闻很多,如说他每年除了背经书外要把前四史全背一遍,从大年初一开始。
他不住在校内,而是乘公汽来校和回家,从教学楼到校门口要走很长的路,于是师生们总是看见他旁若无人地一边走一边背书的样子,乃当时校园一景。
再说他60年代初曾出考试题为“默写红楼梦第22回”,学生都傻眼了,考试不能进行,经学校领导做工作,才换了考题。又说他在“李清照学术讨论会”上一气背诵李清照词作及相关佐证性诗词百数首,各地与会的专家、教授无不叹服。
还说他参加学术会议,凡论文报告中出处不明的引文,他都能当场补出版本、卷次和页码,等等。不一而足。 对比起来,我们今天治国学、学国学的人们的确是“书生”。书为什么生?有人认为老先生们从小就只是读经典背经典,而我们要学数理化、学英语和计算机。
可石声淮先生不是还通那么多经典之外的知识和技能,石声河先生不还是学问卓著的农学家么? 有些事情很令人费解,比如我带的国学、古文献学研究生,要他们默写一下《说文》五百四十部首,背一背《广韵》的韵目,都会“哇……哇……”叫一通,不得已而为之。
可考起雅思、托福来,那巨量的生僻单词要背熟,没有人“哇”叫,而是不厌其烦地百千次反复记诵,一旦考过,都扔到爪哇国去了。
背熟常用的国学经典,实在比背托福单词容易得多、有趣得多,也一劳永逸的有用得多。可为什么“哇”叫而不爱背、不肯背?可见有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流行趋势问题,说到底是观念问题。背诵经典的好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就是真下苦功去做到的人太少了。
如今我们工作在国学教育的第一线,比石声淮先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学生们“书生”的程度。要改变观念,就需要真正的“重视”,比如从娃娃抓起、经典文章在教科书中的分量、教学和工作以及学术上的强调,等等。
背诵经典的意识不断增强起来,“书生”的程度才会逐渐减轻下去。 因为在同学聚会上谈起石声淮先生,有了感慨,才写了这些话。还有一个动因:我还在咸宁工作的时候,先生以七旬高龄应学生们的邀请前往讲学,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务长和我,正好是先生三个不同时期教过的“书生”。
空闲时,我陪先生游览温泉、竹海,先生一路说了好多话,有学界趣闻、做人道理,当然还有“书生”和背书的问题。
我那时编了一本《中国饮食文化品鉴》,先生看过书稿,写了一篇序。如今,先生仙去道山已久,音容笑貌宛在,“书生”之慨盈耳。而我的书至今还未出版,自己翻开来看,实在浅陋,羞于付梓。然先生的《序》是遗世手笔,不可淹灭。
遵同学李大玖之嘱咐,录出并附真迹照片,公诸网页,以示书生恳念先生并努力读书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 万献初同志细致地把“吃”的资料贯穿我国的文化,整理成这本书。
它既富有趣味,又让读者增益许多知识,是一本中等文化的读者的好读物。古人说:人莫不饮食也,能知味者鲜矣。比起“知味”来,由“食”而理解它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重要得多。读者将会感谢万献初同志的细致工作,向大家介绍了有关文化的“食”的问题。
我于一九八○年春才认识万献初同志。那时他是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中文系的学生,我教过他古代文学。把古代一些片段的资料,加以连缀、整理、发现和说明问题,在这方面,万献初同志走在我前面了。 石声淮一九九三年六月志于武昌华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