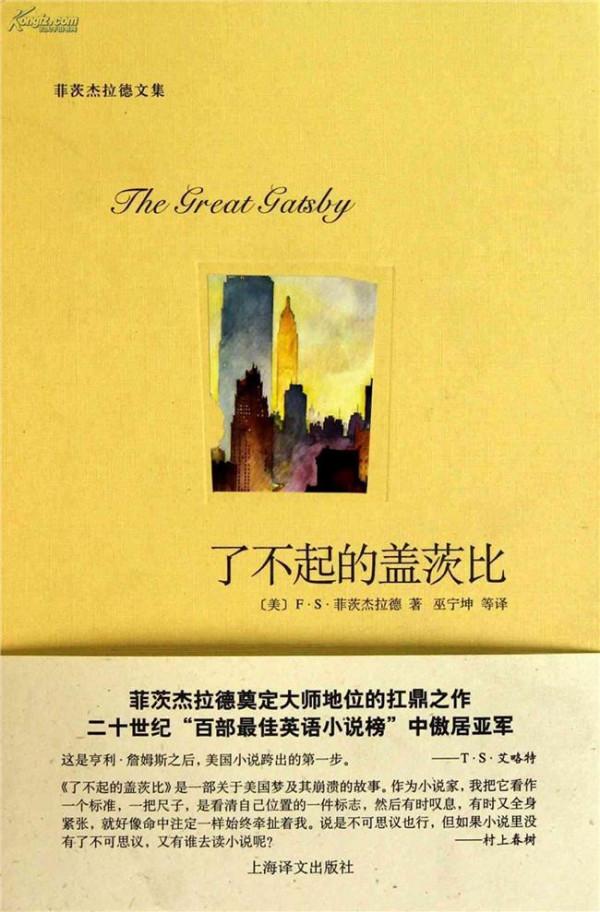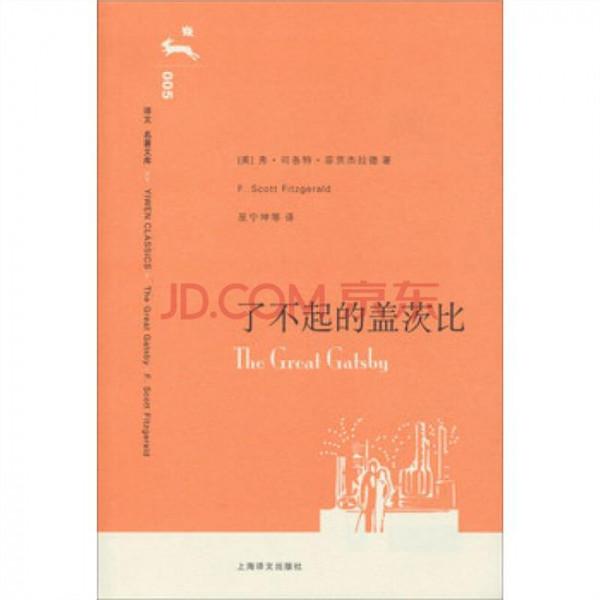巫宁坤教授 巫宁坤:一江春水向东流——记张春江教授
1974年初,托新的一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福,我在安徽和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四年之后,被分配到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
自从我1966年5月底在合肥安徽大学外语系上完最后一堂英语课之后,一转眼七年半过去了。大学学制从四年改为两年,招生办法不再是通过统一高考择优录取,而是从工、农、兵中选拔,条件是阶级出身好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金榜题名的称为“工农兵学员”,以别于“文革”前的“资产阶级大学生”。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统称“上、管、改”。
外语系副系主任、张副教授分配我教英语专业二年级一班精读课。全班二十人,其中一半是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下放几年期间靠收听英语教学广播节目自学过英语。其余的是由公社、工厂、部队选拔的,没学过英语,多半对于英语也无兴趣,只想混张大学文凭。
英语教师中惟一留过学的是张春江老师。他当年留美攻社会学,回国后在上海沪江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多年。1949年上海解放时,他兼任校务委员。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沪江作为教会大学停办,同时社会学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张老师被重新分配到安师大,不是当教授,而是作为一名没有职称的英语教师,月工资66.50元,相当于一个助教的待遇。从此以后,每逢政治运动,他就被抓起来,送到劳改农场,运动结束后又放回来。如此三进三出,莫须有的罪名都是在沪江大学任校务委员时曾抗拒接管。
张老师是虔诚的基督教浸礼会教徒,久经无妄之灾却从来没有怨言,从来没有顾影自怜。这时候他已六十多岁,他的座右铭是“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每次出狱后,他就马不停蹄,以同样天真无邪的热情为他热爱的国家服务,竭尽全力帮助学生和同仁。他教授英语口语,许多学生都热爱他,不仅因为他操一口完美无缺的美国英语,更因为他真心诚意关心他们的学业。打字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他一有空就去打字室帮忙,要么清理积压的工作,要么赶印一篇几小时前刚发表的党中央重要文件或者《人民日报》社论的英语译文。他的十个指头在一台古老的打字机键盘上飞舞,快速惊人,节奏优美,准确无误(他也会弹钢琴)。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劳动从来没有得到过表扬,数十年如一日的工资待遇一成不变,他也从来没有指望过任何奖励。
我第一次在外语系露面,春江就轻快地走过来,张开双臂欢迎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失落多年的兄弟。他住在校园里一座小山顶上两间破败的小屋子里。他的夫人是艺术系的钢琴教授,也曾留学美国。我们两人都没课时,他就会带着我很吃力地爬上山去他家。我们俩一边喝杯清茶,一边聊天儿,有时吃点零食,有时吃一顿他亲手做的便餐。他从来不提他多年来遭受的苦难。他爱谈的是如何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他那份忘我的献身热情令我感动。在后来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我们俩都受到冲击,成了难兄难弟。
另外那位张老师,全系惟一的副教授,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他是30年代从武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可惜他好像并没有从武大外语系几位名教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入党升官。他随着每个政治风向的变动,紧跟当时党的路线。作为党员,他担任分管教学的副系主任,而自己却并不教课。我每天上课以前,他发给我一枝粉笔,对其他教师也一样。他在早晨第一节课的上课铃响以前走进办公室,从来不在下午5点以前下班,天天如此。光凭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从不迟到早退这一条,他年年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贵为副教授,他享受全系最高的工资待遇。有一天,系办公室一位年轻干部感叹道:“我真想知道老张每发一枝粉笔,国家要付出多少代价。这是党员教授为他每月一百几十元工资干的惟一的工作。”
这话其实不完全公平,因为党员教授还有许多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不久前,在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中,张春江老师受到一名工农兵学员的批判,这个积极分子指责张老师在讲授英语虚拟语气时用的例句是“我若为王”。他被控两条罪名:一条是“指鹿为马”,另一条是“怀有反革命复辟的梦想”。党员教授一向以英语语法专家自居,在业务服从政治的原则下,站稳立场,此时毫不含糊地站在工农兵一边。
“十年浩劫”过后,张副教授不幸因病逝世。张春江老师的“冤假错案”终于平反,恢复原教授职称和工资待遇。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更加精神焕发,更加全心全意扑在英语教学工作上。对过去整过他的那些人,他心中毫无芥蒂。
1979年暑假期间,江西省教育局,为了提高中学英语教师的专业水平,在庐山举办一个英语讲习班,为期一个月,由南京大学的梁思成教授主持,春江和我也应邀去任教。教师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令我们感动,我们每天上下午都讲课,有时我觉得很累,春江长我十岁却永远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使我感到惭愧。清晨黄昏,我常和他在山间漫步,听他谈英语教学,谈英美文学,谈《圣经》,真是如沐春风。他那超凡脱俗的身影,仿佛和庐山的苍松翠柏融为一体了。
在他献身半个世纪的安师大,他是大学校园里一个活的传奇。对于那些毁了他的大半生又利用他的才能和爱国热情的人们,他也是活生生的、无言的谴责。两年前,他终于结束了坎坷的一生,但张春江教授真如一江春水,在一个漫长的严冬流贯过不知多少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