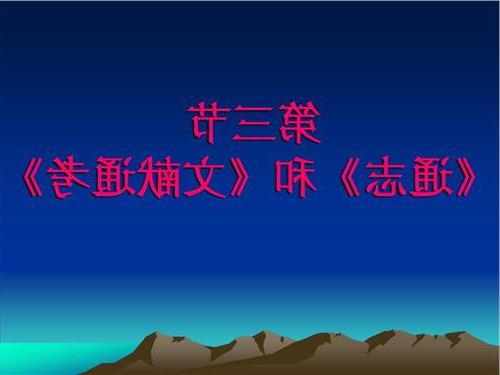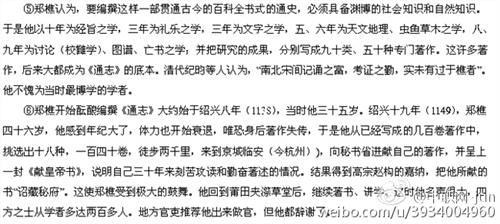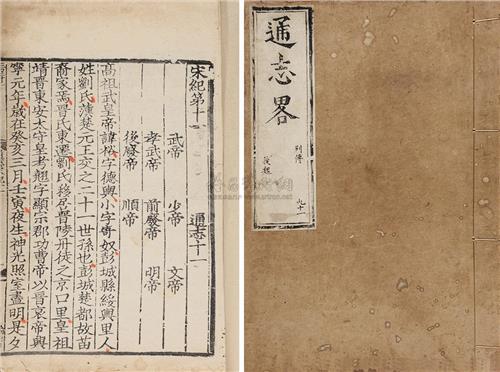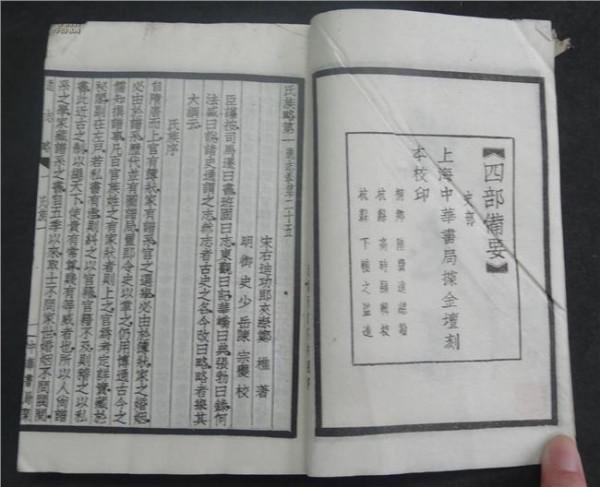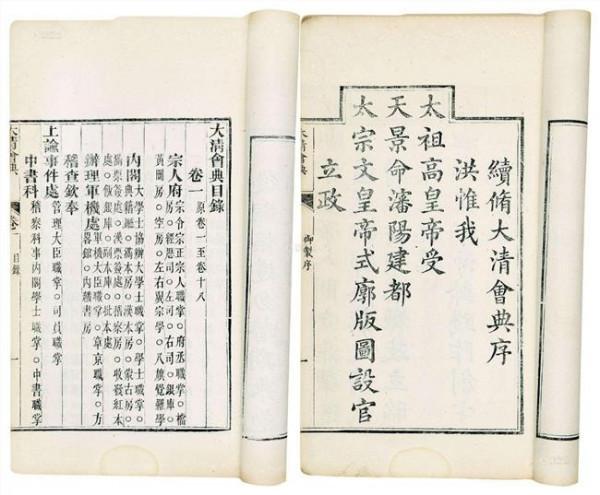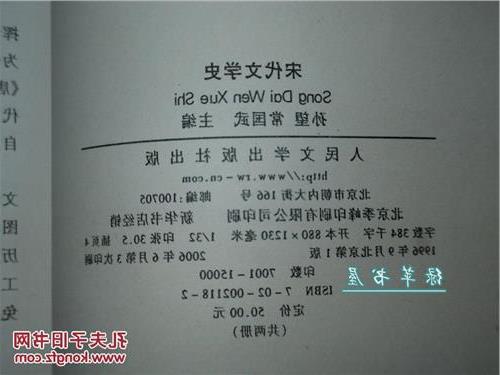郑樵作品 郑樵整理文献的工作程序
前文中已述谢贵安先生认识到郑樵的校雌学包括了求书、校书、分类编目等工作,但并未完全认清郑樵的校雌活动,也没考虑到郑樵校雌图书的最终目的,就指出郑樵校雌学的特点是"它具有求书一校书一分类编目三个阶段,以及这三个阶段所反映出的前后相接的系统性和与辑佚、校雌、目录相关的联系性。
郑樵校雌学的三个阶段所构成的系统表明,从求书、经校书,到分类编目,这一系列工作,都属于其校雌学的范畴。"最终判断,郑樵所谓之校雌学虽然打破了狭义的封域,将校雌推广到包括求书、校书和分类编目的广义范畴,但并不等于后世之文献学,未能真正地理解郑樵的实际校雌工作。
谢先生之所以有疏漏,是由于其尽管认识到郑氏之校雌学包含求书、校书以及分类编目等活动,却不知道郑樵之校雌与前代刘向等人之差异。
所以,他在分析郑氏校雌学的特点时,认为其对典籍进行了求书一校书一分类编目这样三个前后相接的工作程序。张舜徽先生等前代学者在总结刘向等人的校雌活动时,好言其先求书、次校书、后编目,后发展为版本学、校雌学和目录学,成为文献学的三大分支,即文献学的三位一体之说。
谢文将郑樵的校雌活动分为求书、校书和分类编目三个先后相续的阶段,并以"编目"为终结,盖受前代学者三位一体之说的影响。
应注意的是,郑樵的校雌活动与西汉刘向等人是不同的。首先,郑樵是属于私人之校雌,而刘向等人是属于官府组织之校雌。关于刘向之校雌 , (隋志》载:"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就,向辄别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误,叙而奏之。
刘向广收天下图书,每校一书,便编撰该书之叙录,最后总成《别录》一目。而郑樵一生未人秘书省供职,所以也未参与过宋朝廷组织的校书活动。既然未参加过朝廷组织的校书活动,怎么会有先求书、次校书、后编目这样三阶段呢?后世以"求书一校书一编目"为序进行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的,亦仅清纪的主持编纂《四库全书》等寥寥数次耳。
其次,郑樵的编目工作并非以校书为基础,这两项工作程序已经分离。
西汉刘氏父子校书先求书、次校书、最后编目,后世遂将此工作程序奉为典范。但是,随着图书的增多、学术风气的改变,这种工作程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编目与校书分为二事,自王俭与阮孝绪已如此。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分析指出:"在图书的数量和物质条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时期,编目的方法也必然要随之起一些变化。
刘向、刘欲时代,先校书,后编目,在校书的阶段编写出揭露全书大意的叙录,成为编目时作简单说明的最好依据,那样把校书、编目做为一个统一的过程,是为当时的图书流通和钞写等物质条件决定的。
荀敲时代只校定了一小部分新书定本,有许多书没有叙录,这就不但使他不能不编没有解题的简单目录,这就把目录的质量降低,而使校书与编目的两个工段不发生多大关系和影响。
宋齐梁三代虽说也曾校书,而与编目已经完全不发生什么连带关系了。而王俭和阮孝绪是在失去校书叙录作为编目依据的时代,而毅然拒绝简单的目录编辑形式,要用个人的力量来编成有解题的全国综合性系统目录,这当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不能达到刘向、刘欲的水平的。
所以王俭采用传录体,以便利用文章志或其它有解题的目录,而阮孝绪则在王俭的基础上,加上个人的最大努力,尽可能揭露出撰人的必要事迹和书本的流通情况,以达到《匕略》所做的简单说明的形式。
""在解题方面,《匕录》的成就是胜于《匕志》的,但在这样的做法之下很难再进一步,所以到了下一时期(中古后期),编写目录的解题和编写校书的叙录分开,编写有解题的系统目录也和编写藏书的登记目录分开了。
笔者仔细观察一下郑樵的校雌活动,会发现其与刘向等人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汉刘向等人校书是在朝廷组织下的活动,其工作程序是先求书、次校书、最后进行编制目录,主要目的是为了校书,即整理西汉以来的大量图书,而最后编制《别录》只是其校雌群书的简单说明。
而郑樵则是以编制目录为直接目的,以通史编纂为最终目的,其利用大量的文献进行著录、编目,使得编目不依赖于校书。
笔者认为除求书、校书与编目之外,郑樵的校雌活动还应包括考证与编纂两个程序。下面从郑樵的实际著述来进行分析:据厦门大学郑樵历史调查组考订,郑樵著述多达八十四种。现存于世的仅有《诗辨妄》、《尔雅注》、《夹漂遗稿》、《通志》以及郑樵历史调查组所整理的四篇遗文。
观郑樵之著述,其多为古籍考辨或据旧材料编纂新书。以今言之,前者为文献考证,后者为文献编纂,有些文献学教材亦列为专门章节,可见其为文献学固有之义。郑樵最终撰成《通志》采前人之书,成一家之言,彰学术之旨归,亦然。
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第十二编《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以"通史编纂"为文献学之指归,岂非受郑之启发软?故笔者认为,郑樵所论之校雌学还涵括考证与编纂两个程序。
章学诚所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近代以目录学家最好言之,俨然此八字唯就目录学言之。然章所事固亦多为编纂,即其所拟《史学考》,曰考不曰目,且收佚书,知与《别录》、《匕略》、《四库总目》异趣矣,亦当视为学术史著,非仅目录而已矣。
关于郑樵的校雌活动,很多学者认为不应当包涵校勘,即校对勘正文字讹误。例如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所附的《校雌通义》中就曾指出,郑樵的校雌"略其鱼鲁尔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雌姚名达先生也认为郑樵之校雌转弃校勘,而是以广义之求书、分类、编目等项为主要任务。
张舜徽先生亦言郑氏从事校雌学"大胆地抛弃了狭义的"校雌,而直以广义的求书、分类、编目等内容为校雌学的主要任务,把校雌的范围推廓得很大。
后谢贵安先生《郑樵校雌学特点论要》提出异议,其据郑樵《校雌略》所载"求书之官,不可不校"等语和《献皇帝书》中郑樵关于自己校雌学研究成果的总结来证明,郑樵所论之校雌包括校勘。
谢氏这一论断是很有意义的,但仔细分析,其所列的理由未免过于牵强。详考之,笔者认为郑樵所论之校雌应包括"校勘"。郑樵一生未人秘书省为官,也未从事实际校勘工作,故其《校雌略》少言校勘之事。
郑樵曾多次上书,而其上书的目的是为了得一校官之职。《献皇帝书》载:"臣伏靓秘书省,岁岁求书之勤,臣虽身在草莱,亦欲及兹时效尺寸。顾臣究心于此,殆有年矣。又《上宰相书》载:"万一使樵有所际会,得援国朝陈烈、徐积与近日胡援例,以命一官,本州岛学教授,庶沾寸禄,乃克修济。
或以布衣人直,得援唐蒋又、李雍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雌,亦可以博极群书。稍有变化之阶,不负甄陶之力。唁,自昔圣贤犹不奈命,樵独何者,敢有怨尤?然穷通之事,由天不由人,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以穷达而废著述,可乎?此樵之志,所以益坚益励者也。
mfsal显而易见,郑樵上书有心求一校官,但遗憾的是其一生未人秘书省供职。
宋代校官主持校勘事务,私人虽有校勘之事,但却无校勘之职,故《校雌略》少言校勘者,非樵有意排斥于外,因其未得校官,未从事实际校勘活动也。又校勘事务性工作耳,郑或不屑言之软?此直待陈垣老才作《校雌学释例》,可见古人之敏于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