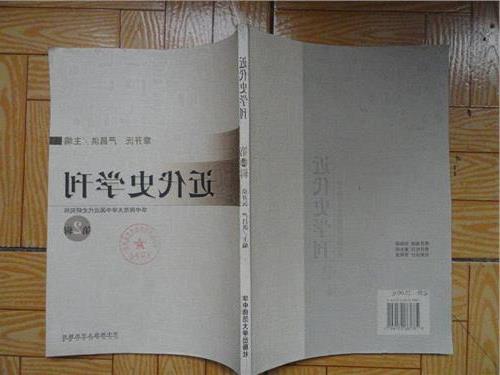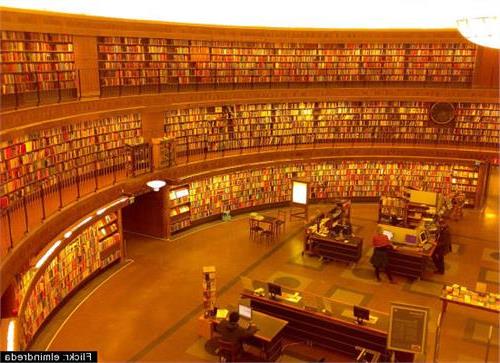近代史两个半人章开沅 章开沅:“半个”中国近代史家的传奇“史话”
曾有人说:“中国近代史家中,如果只能挑出一个人来,我想一定就是章开沅。”此话不免有些夸张,不过,早些年有一种说法:大陆真正的中国近代史学家只有两个半,即陈旭麓、李时岳和半个章开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胡绳生前也曾有相关说法。
尽管这种说法有不同的版本流传,但章开沅在史学界的后来居上,却是不争的事实。时过境迁,天不假年,各种版本中的其他主人已先后作古,当年的“半个”如今已是中国近代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了。
中等身材,声如宏钟,神清气定,目光如炬,宽宽额头上的银发更显资深学者的风采。章开沅出现在眼前时,更立体的形象取代了原有通过报刊与传说所形成的“影像”。初次见面,章开沅给人的感觉往往是严肃中透出一丝威严,让人敬畏有加。这种感觉可能源于他学术的严谨,也可能源于年轻人对前辈的仰望。
“小鲁迅”自文到史的“历史角色”切换
读中学时,章开沅曾勤奋写作,文风冷峭,在同学间享有“小鲁迅”的美称。
抗日战争期间,尚少年的章开沅与其家人沦为难民,逃难到当时的后方四川重庆。父亲因工薪微薄难以养家,便和母亲一起到江西工作,他与兄姐在江津乡下一集镇国立九中就读(该校对于沦陷区学生,有“贷金”维持生活)。1943年7月,章开沅因“思想问题”被中学开除。几经辗转,同年9月章开沅在重庆计政专修班读会计专业,次年5月又因与军训教官冲突被开除。
尔后,章开沅怀抱爱国热情投笔从戎,准备随青年远征军赴中缅边境,在美国史迪威将军率领下抗击日寇,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但不久即抗战胜利,随军远征抗日前线未能成行。
1946年夏,章开沅复员到南京,报考学风好的金陵大学名牌专业农业经济系,却意外地在同年10月被该校历史系录取。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国文突出而被历史系看中。为此,章开沅步入了史学的摇篮。
进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章开沅仍志在文学,好为时论。章开沅回忆说:“我们历史系有一个小小的读书会,曾不定期出一个名收《天南星》的墙报,属于进步学运阵营。”章开沅是这个墙报的主笔,他曾以“文封湘”(暗寓章开沅)的笔名写过《漫话金圆券》的政治评论,据说连经济系的师生也很看重这篇文章,到处打听“文封湘”为何许人。
如果时局未变,章开沅或许会一步步由学生式的记者向梦想中的战地记者靠拢。惜乎在他尚未成为记者之时内战已然爆发,他和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参加了学生运动。不久,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而不得不中断学业。
1948年,章开沅经河南驻马店,只身来到中原解放区。在这里,章开沅进入中原大学从事历史教学。于是,“本想当个跨马佩枪、文武双全的战地记者”的章开沅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与历史建立了不解之缘”。
1951年秋,中原大学自开封南迁武汉而与华中大学合并,两年后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便转任为该校历史系教员,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从此就在华师从一而终。
完成人生转型的章开沅很快就进入了“历史角色”,开始醉心于学术研究与历史教学,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章开沅戏言:“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通常是先恋爱后结婚,我却是先结婚后恋爱。我是在担任历史系教师后,才逐渐增长了对教师工作、对史学研究的兴趣。”
章“开沅”与章“开源”
常有人将章开沅的名字错写为“开源”,这也许是因为章开沅在近代史研究中开荆辟莽地开拓了很多新领域所致吧。在这方面“开沅学派”确是不负此“误”。
在章开沅看来,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求真的学问,真实是史学的生命。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际遇如何沉浮,他始终能保持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和刚正不阿的独立人格。如他自己所言:“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千万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这是楚图南为戴震纪念馆的两句题词。章开沅常以此相赠弟子。
要探究历史的奥秘,就必须要对已逝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通识”。上世纪70年代末,章开沅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就提出“社会历史土壤说”,即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其历史土壤才能产生的。
这个历史土壤就是历史总背景,就是整体历史观,就是史学之通识。“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是章开沅近些年常讲的话题,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他的史观。章开沅不仅授业解惑,还传道,传授学科与学者都应具备的独立品格。
当年,“文革”遗风尚存。文科各学科都要为政治服务的主张,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章开沅在著述和言谈中都加以反驳说,史学有自己独特的学科使命,不能成为政治的奴婢,不应提史学为政治服务,而应提史学和政治都要为中国的历史进步服务。
在商潮涌动与科技至上的今天,史学遭受冷落,人文束之高阁,一方面是时势所因,另一方面也在于史学研究者自身。章开沅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史学研究者应当在坚持学术品格的同时,关心社会,参与历史。从学术研究讲,历史研究者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来设计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去,把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实践中去。
此外,历史研究者不应该单纯埋怨社会冷落历史,而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历史的价值。
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陷和当今社会的腐败等丑恶现象,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无所作为;而应该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努力,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倡导文明与人文价值的重建。
他说:“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
章开沅是“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的倡导者。他说:“我赞成史学必须讲究社会效益,但是不赞成对社会效益作过分偏狭乃至扭曲的理解。史学之所以有社会效益,首先因为它是一门科学,如果史学不再是一门科学,它就顶多只能成为一件可供任何人随意驱使的玩意儿。”
章开沅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三分田”。许多人听了章开沅有关学术报告后都改变了对历史学“呆板”、“古腐”的偏见。一次章开沅在暨南大学“史学沙龙”作学术报告,当学生把一束鲜花送到他手上时,章开沅马上接口:“我以前曾经说过‘历史是没有鲜花和掌声的研究,史学是一种寂寞的事业’,同学们今天是不是要给我个下马威,送上这么漂亮的鲜花,想推翻我的论断啊!
亦或许是想给我一点安慰吧!”短短一句话,拉近了大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会场后气氛显得特别活跃。
章开沅演讲的题目是“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其实这是他思考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当时,章开沅并未准备讲稿,而是随意自由发挥,但他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中口若悬河、娓娓道来,整个演讲条分缕析、逻辑缜密。
他不时引经据典,针砭时弊,声音洪亮、谈笑风生,当时很多听众都觉得意犹未尽,大有未解耳馋之感,以至于到了问答问题环节时,提问者非常踊跃。当有同学问道“您是怎么指导您的研究生做独创性的研究”时,章开沅这样回答:“我的学生知道‘史学无禁区’,我尽我的全力让他们了解,当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遇到问题时,政治结果我负、学术水平你负。”话音刚落,会场响起了持久不断的雷鸣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