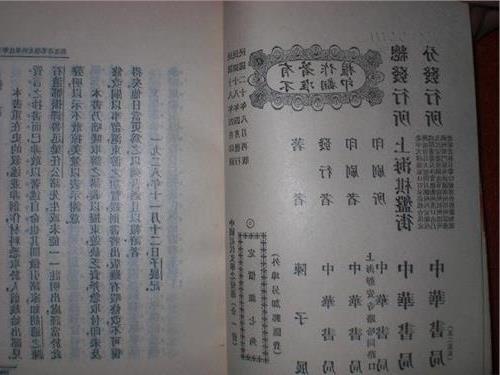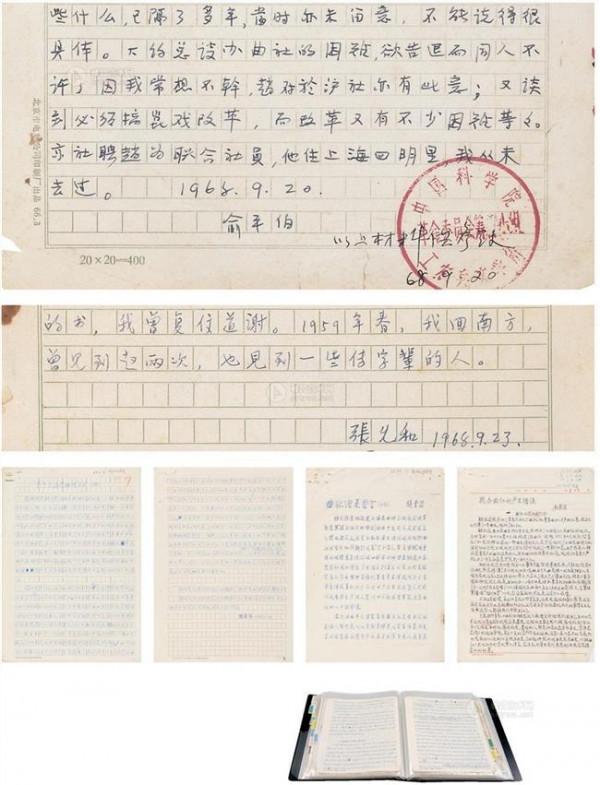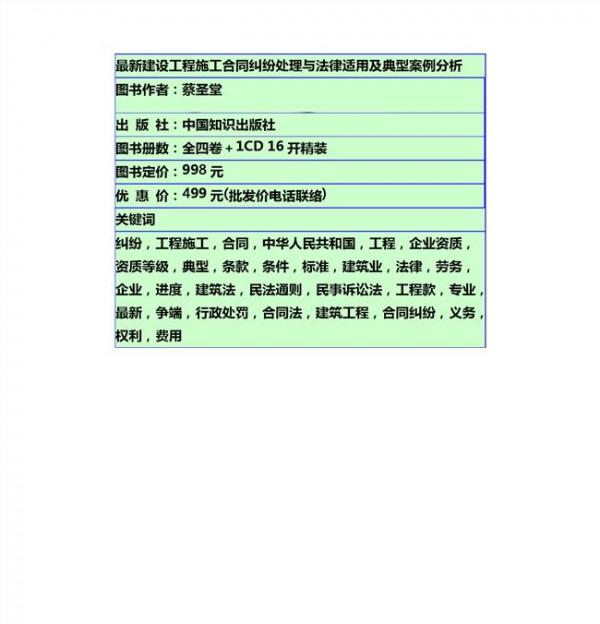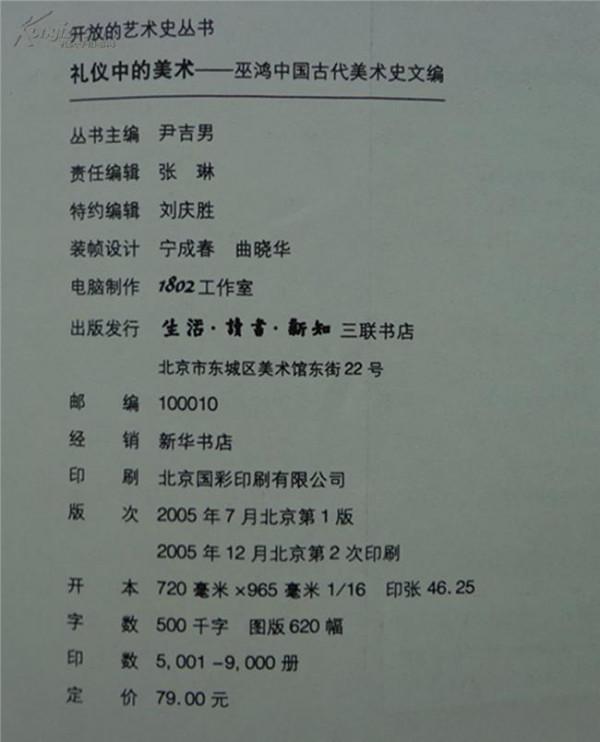张允和戏曲 刘士杰:我和恩师的戏曲缘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2月07日 03 版) 恩师赵景深先生离开我们已有26年了!我对恩师的思念却并不因为时间的久远而稍减。每想起老师,他那慈祥的面容就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记得我第一次听赵老师的课,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赵老师讲的是古典戏曲课,当他讲到昆曲时,详细讲解了昆曲的起源、发展及其鼎盛时期。讲着,讲着,他竟抑扬顿挫地唱起来了,把同学们都镇住了。大家既惊奇,又兴奋,赵老师唱得有板有眼,十分动听。
我至今还记得他唱《长生殿·小宴》中“粉蝶儿”时的情景。赵老师一边唱着:“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一边还做着唐明皇出场时的身段。赵老师声情并茂的演唱、优美动人的身段,把我们带进了昆曲艺术的殿堂,使书本上平面的知识,成为立体的、形象的知识。
正因为听了赵老师的演唱,使从未接触过昆曲的我喜欢上昆曲。 赵老师领导着一个类似京剧票房的社团“上海昆曲研习社”,他是社长。与票房不同的是,该社团不仅是票友们聚会唱唱而已,而且还担负了研究和传习昆曲的任务。
成员不限于本校师生,也向社会开放。赵老师见我对昆曲很感兴趣,便吸收我为昆曲研习社社员。在曲社里,平时由老师教我们拍曲。我们还学了古老的曲谱“工尺谱”。
我学的第一出戏是《玉簪记》的“秋江”一折。曲社定期举行“同期”。所谓“同期”,就是曲社内部演唱的盛会,可谓少长咸集、新旧欣会、名家荟萃,不管是名家还是初学者,都可以上台一舒歌喉。隔一段时间就举行“彩唱”。
所谓“彩唱”,就是粉墨登场,在剧场正式演出了。有一次,曲社在复旦大学登辉堂演出昆曲专场。赵老师演出《三戏白牡丹》,他饰吕洞宾,唱做俱佳。而“赵家《长生殿》”更被复旦师生传为佳话。原来所谓“赵家《长生殿》”,就是赵老师一家参加演出,赵老师饰唐明皇,师母饰杨贵妃,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分别饰演太监和宫女。
除了在曲社活动,有时我还到淮海中路四明里赵老师的家中参加昆曲聚会。每当此时,一进弄堂,就会听见从6号楼上传出悠扬的笛声和着婉转的歌喉。
因为喜欢戏曲,我报考了赵老师的研究生。记得那天下课后,赵老师走下讲台,却没有离开教室,而是走到我的座位跟前悄悄对我说:“你被录取了。” 我惊喜万分,差点跳起来。
赵老师笑着用手示意我不要声张。 然而,当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时,却意外地宣布我被分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文学研究所。我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赵老师不收我这个学生了? 在向赵老师告别时,我提出这个一直困扰我的疑问。
赵老师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并不是不要你,只是我没有分配权。文学研究所是文学研究的最高学府。你研究生毕业后,也未必有这么好的单位。正好你师兄邓绍基来母校招生,我就把你推荐给他了。
文学研究所条件好,你在那里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深造。” 我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赵老师为了培养我,为了我有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真是煞费苦心。 望着慈父般的老师,心中好生不舍,我多么希望继续做他的学生啊!
老师慈爱地说:“我写封信给你师兄邓绍基,让他多多关照你。” 我说:“我再也不能跟您学昆曲了!” 老师说:“在北京,文学研究所的俞平伯先生也办了一个昆曲研习社,你可以参加他的那个曲社。
我也给他写信,你可以拿着我的信找他。”说着,又写了一封给俞平伯先生的信交给我。后来,我拿着着这封信,找过俞先生,俞先生告诉我,因为思想战线形势紧张,曲社已经解散了。直到1979年,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活动,我才由唐湜先生介绍,加入该曲社。
而那时,俞平伯先生已不再任社长,社长是张允和先生。此是后话。 当我向老师告辞时,老师叫住了我,从书柜中拿出一本书,那是他的著作《曲论新探》。他在扉页上,用清丽的笔迹题字:“士杰弟正之。
赵景深。”哪有老师称呼学生为弟的?!而且还用“正之”!老师的谦逊使我惶恐不安。 后来,每当我回沪探亲时,我总要去探望赵老师。 1985年1月7日,赵老师病逝于上海,可惜那时我在北京无法抽身为老师奔丧。
到了文学研究所,我被分到当代文学研究室,当时我很遗憾,看来与古典戏曲无缘了。可是我对戏曲的痴情始终不变。直到我出版了《中国戏曲史话》,总算圆了我的戏曲梦,同时,也庶几可以告慰赵景深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如今再去淮海中路,四明里早已拆除,再也听不到那悠扬的笛声和婉转的昆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