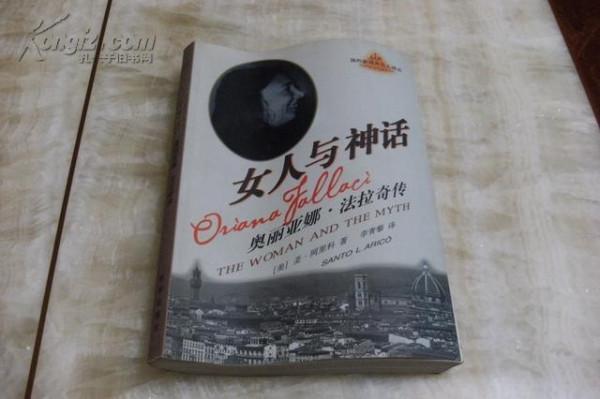法拉奇书信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法拉奇的书
有一个女人,在记者中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她的名字叫做费列奥娜.法拉奇,一个意大利女人。 她采访了多为政要,包括邓小平。她去过战场,即便在战场上也涂着指甲油。她终身未婚,却有过一个未出世的孩子。很难形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她的勇气与职业精神,是给她的后辈的我们永恒的参照物。
她写了本书,说是献给全世界所有的女性的,叫做《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以下是摘抄。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你已存在:为了战胜虚无,一个生命降临到世界。
当时,我睁开双眼躺在黑暗中,我蓦然确信你就在那里。你存在。仿佛一颗子弹射中了我,我的心停止了跳动。当你再一次撞击我时,无限的惊奇便在我心中涌起。我感到我掉进了一口深井,以致一切对我来说都显得那么恐惧、那么陌生。
此刻,我幽闭在恐惧里,这恐惧渗透了我的脸颊、头发和思想。我迷失在这恐惧中。我知道,这不是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因为我不在乎其他事物;这不是对上帝的恐惧,因为我不相信上帝;这也不是对痛苦的恐惧,因为我不畏惧痛苦。
这是对你的恐惧,对突然把你从虚无中抛出,让你附着在我身上的这样一件事情的恐惧。我从不曾急切地期望着你的来临,尽管我知道你有一天终会存在于某一时刻。我在这种意识中,一直在久久地等待着你。
但我仍向自己提出了这样可怕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一天,你会带着责备的心情冲着我大声哭喊:“是谁赋予你权利,让我降临到这个世界?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什么?”孩子,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尝试。
它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它所有欢乐的时刻全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插曲,并且你将为它付出太高的代价。我怎能知道把你遗弃将会更好?怎能认为你的确不愿意返回沉默?你无法对我说这些,因为你生命的诞生仅仅是一团勉强形成的细胞。
也许,它不是生命,而仅仅是一种生命的可能。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哪怕是点一次头,使用一种暗示。我的母亲就曾要求我给她这样的暗示,这也就是她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理由。
你看得出,我母亲并不希望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的生命实际上起始于他人粗心的某一瞬间。为了不让我诞生,她每晚把药丸融在盛水的杯中,然后流着眼泪吞下它。她坚持喝着那种药水,直到那天晚上,我在她身体里蠕动,给了她重重的一蹬,要她不要抛弃我。
当我给她这种暗示时,她正好把那杯子举到嘴边。她立刻翻过杯子,倒掉了杯中的水。几个月后,我便有幸来到了这个世界。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祸还是福。在我幸福时,我认为这不错;当我不幸时,我感觉这很糟。
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即使在悲哀的时候,我也不曾为我生命的诞生痛感惋惜,因为我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虚无本身更糟的事情了。让我再说一遍:我不害怕痛苦。因为我们是伴着痛苦而降生、随着痛苦而成长的,我们已经习惯了痛苦,就像已经习惯了我们的手臂和双腿一样。
事实上,我甚至不害怕死亡。死亡至少意味着你诞生过一次,至少意味着你战胜过虚无一次。我真正恐惧的是虚无,是不存在——那种由于偶然、过失和他人的粗心造成的我生命的不存在。
许多女人都会这样问她们自己,为什么她们要让一个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由此会导致饥饿、寒冷、毁灭和耻辱吗?它会被战争和疾病杀戮吗?她们放弃了那种饥饿将会满足、寒冷将被温暖的希望,否定了人的一生将有忠诚和尊敬相随的期许,抛弃了人会把生命奉献给消除战争与疾病的任何努力。
也许,她们是对的。但难道虚无会比痛苦更可取吗?即使我在为我的失败、幻灭和挫折哭泣时,我也坚信痛苦远远胜过虚无。
如果我把这点推及生命,推及让生命诞生与否的两难处境,我相信,我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会发出这样的呐喊:生命的诞生比生命的遗弃更为美好。然而,我能把这一推论强加于你吗?难道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如果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和别的什么,我没有兴趣让你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我完全不需要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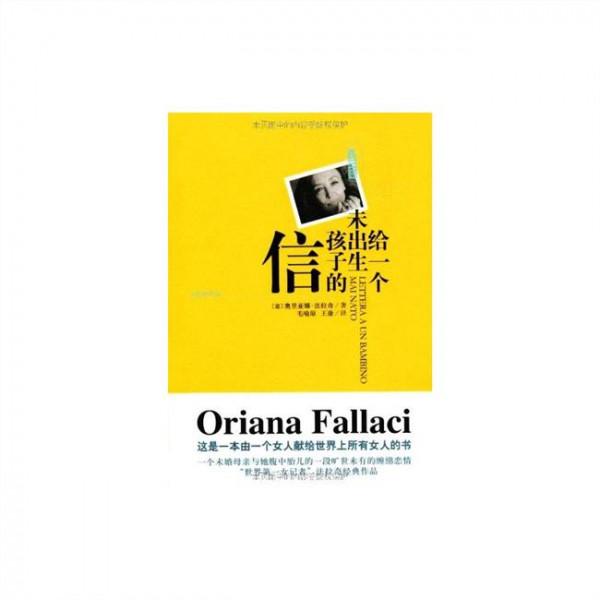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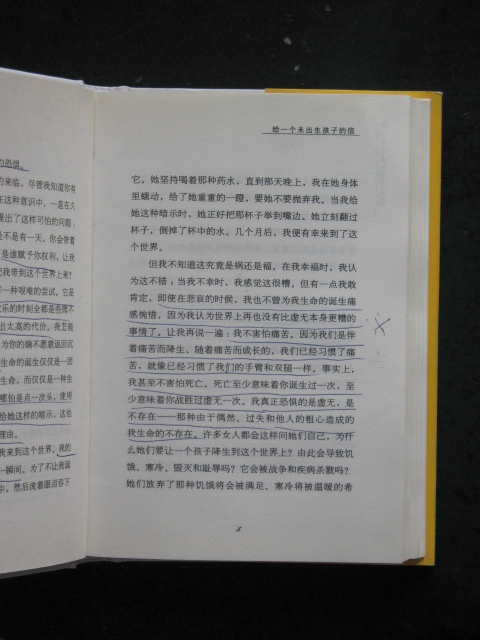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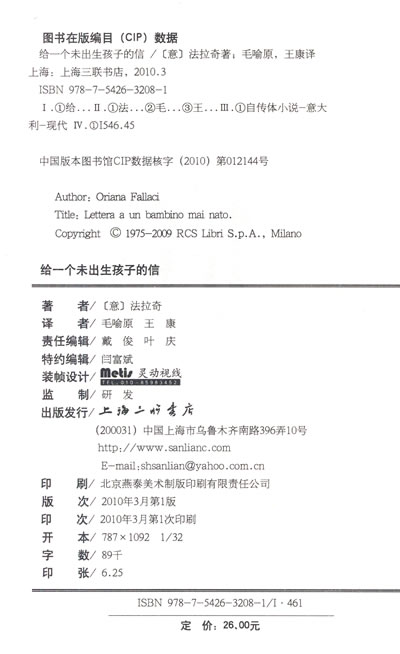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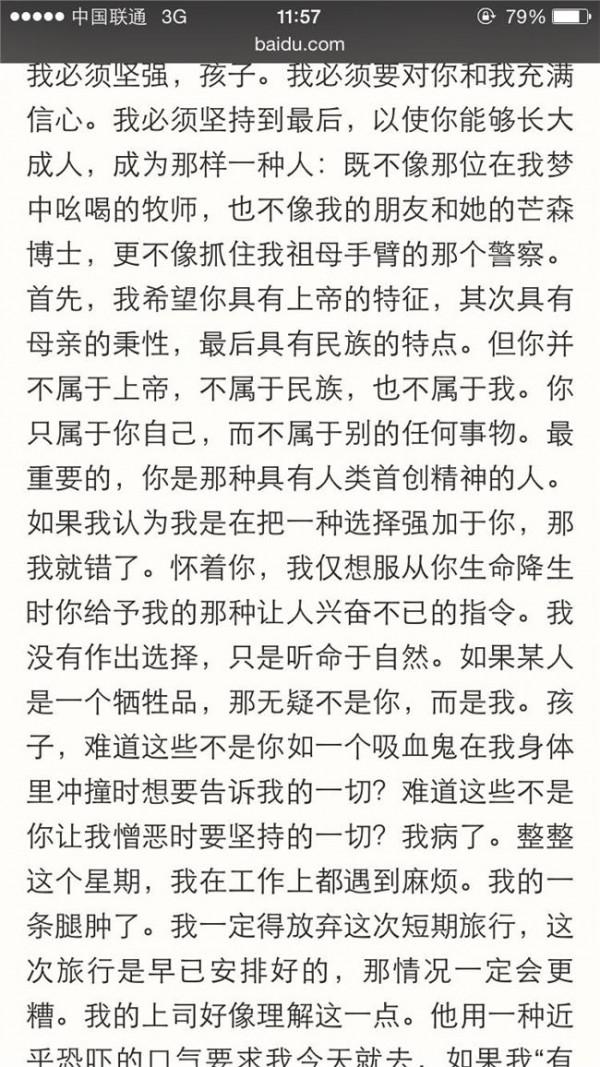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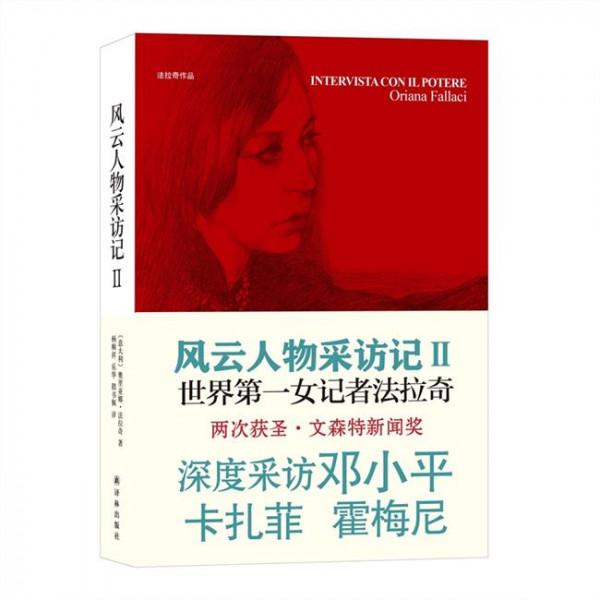
![法拉奇著作 法拉奇作品:男人 [精装]](https://pic.bilezu.com/upload/e/19/e1982697953cb9e2047bbeeb3a15ca87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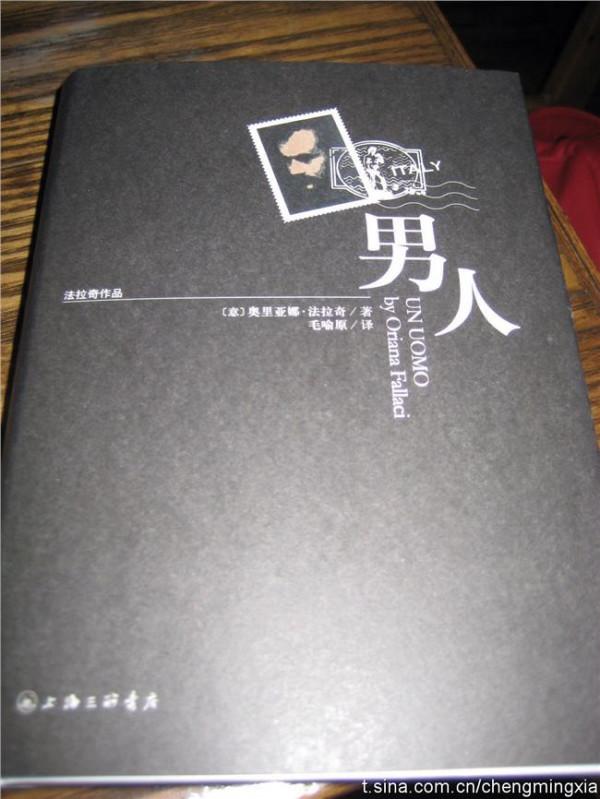
![>一大波电子书来袭![豆瓣评书最高的250本书][epub][内含epub阅读器]](https://pic.bilezu.com/upload/4/14/414d27a4e6008d8d5afa098c199cebe4_thumb.jpg)
![>法拉奇pdf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意)法拉奇 文字版 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b/3b/b3b54f631f6595a28682778d076edc3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