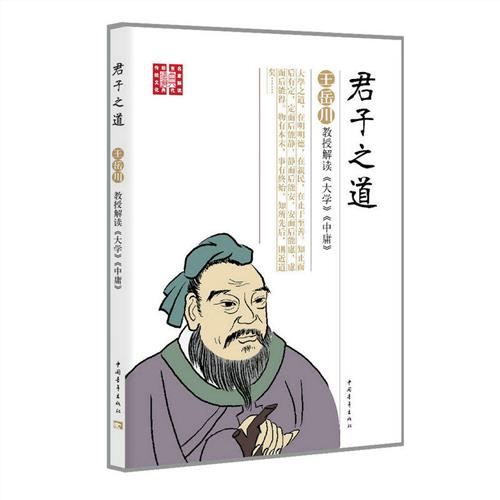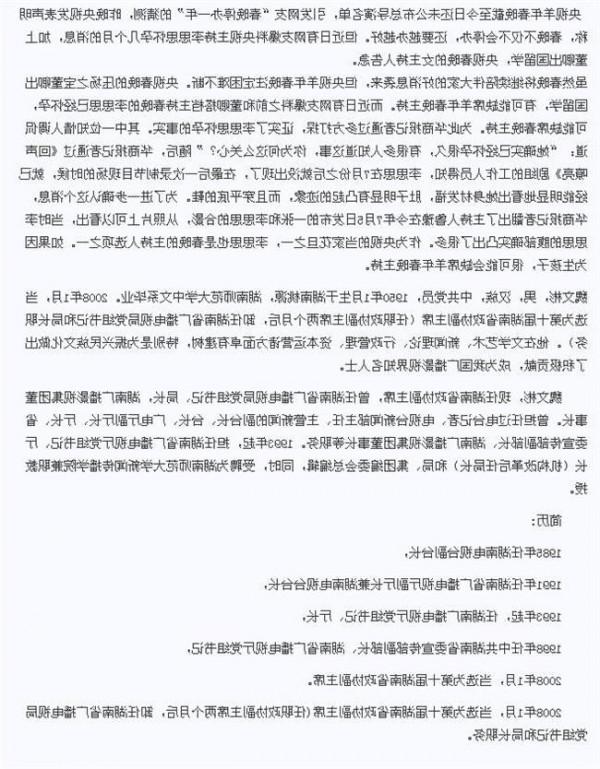王岳川刘思思 王岳川:海外汉学界的后现代后殖民反思
张旭东进而转向政治性问题分析。指出:“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冲突并不是‘左与右’的对垒(这多多少少是精英知识分子自怜自爱的想象),而是现代性精英集团(国家权力及依附于它的知识分子群体)同兴起于市场和日常生活领域的无名的消费大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100]读了这段话,我不由为作者的理论勇气而感叹。在九十年代,只要想一想政治、经济、法制、文化等社会巨大转型中的各类问题胶着状态,就知道问题远没有一句“知识分子自怜自爱”这么简单,至于将九十年代的“紧张关系”归纳为精英集团与消费大众之间的事,恐怕同样是一些国内后学者的“新宏伟叙事”。
[101]相反,我很同意作者的这一说法,“中国后现代文化是反精英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和娱乐工业内在的肯定现实,复制现实的特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重迭无疑给‘中国后现代主义’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中国后现代’这个问题的出现本身就包含了双重的历史意味:它一方面表明‘现代性’过程在中国还远没有完成,还将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回到我们面前;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中国现代性一定程度上的展开正是‘中国后现代’问题的客观条件;而在此条件下出场的‘中国后现代’必然包含了对现代性经典理论的再思考和‘重读’;必然包括对现代性的客观现实的反省和批判。
”[102]
张旭东广博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资源使其对后现代理论研究有颇多精到之处,尤其是用这一理论符码阐释当代中国现象,使理论和实践相遇,给人以诸多启示,当然,在具体实践上的地图测绘与国内一些学者有了某种现状评价的差异。
我认为,这种差异是很正常的学术问题,因为有良知的学者们都在努力弄清这样一些问题:怎样排除那种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阐释中国才合理的问题和谁能阐释中国的权力话语问题,而追问对中国应该如何阐释?是想象性的中国阐释?想象性的中国参与世界性话语的阐释?还是拒绝以西方理论框架看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或是对中国现代性问题加以真实观照,从而得出中肯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对此,我想,当务实地思考并从事社会学考察之后,或可得出某种真实的结论。
四,后冷战时代的中国问题。
在后殖民主义问题研究中,刘康[103]无疑是近年来颇有影响的一位,其合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04]对东方主义加以审视和批判,构成一个影响广泛的文化批判氛围。
刘康在《全球化“悖论”与现代性“歧途”》[105]中认为:全球化悖论是现代跨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奇特的文化逻辑。在文化上,跨国资本主义的悖论更加突出。强调多元、民族、本土、离心、非西方、多极、多中心的文化意识,方能一面使消费者对跨国资本和商品产生具体的认同与归属,一面又使生产者“心怀全球,立足本土”,为跨国资本主义的真正拥有者和消费者效力。
“后殖民主义”引进了“第三世界”或“后殖民文化”经验,在种种“现代性话语”的头上,便可方便地再套上一顶“西方中心”、“后殖民”的帽子。
只要不带偏见地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史,便知中国人所作的,其实是针对着悖论的正题,也即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挑战与重构。刘康对全球化的认识具有清醒的认识论的高度,不仅注意到了全局化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放松对其悖论和歧途的反思批判。
尤其是,他的眼光不仅注意西方时髦理论的输出,更重视中国现代史上东方对西方现代性的回应挑战。
在后现代时代的复杂政治风云中,刘康表明自己的政治意识和鲜明的阵线立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中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辩论锋芒所向,正针对着包括学术研究自身的“话语”模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
历史的自省和反思与社会干预相辅相成,要求有一种高度的学术自觉。一方面,西方学者不断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意义大于审美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坚持以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先的方法来研究现代文学。[106]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和左翼文学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传统……“在当前文化多元、开放的呼声高涨的情形下,我们仍然面临着确定我们自己的立场和位置、认清我们学术研究中的‘文化和政治的隶属和参与’的问题。
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与文化格局中,某种新的冷战意识正在抬头。
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中,我们对此更应该有清醒的认识。”[107]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传统,对中国的‘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是不能回避和绕开的。
中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作自省式的理论批判与反思,虽然其对象和历史语境与西方不同,但与西方批评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辩论却有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
”[108]无疑,刘康的批判具有相当的激进色彩和思想力量,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传统,并且将这种传统延伸到当代文化论战中来,重新给自己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定位。
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中,他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对“后学”的基本态度。认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既不同于海外汉学的“后学”,也不是什么“新保守主义”。他们对当代西方“后学”理论的关注,是出于对全球性化问题的考虑。
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流行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而是力图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同样,刘康在《后冷战时代的“冷思维”》[109]中强调,海外“后学”研究或批评的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有重要的地位。
这一方面说明海外华人学者关注中国现状问题,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同时注意批评西方后殖民霸权,强调中国后学研究中正当的学术立场。
在我看来,刘康对国内“中国后学”的关注,立足于一种问题意识,即他所说的“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
有了这份清醒,对后学问题就既不会一味张扬而不揭露其迷误之处,也不会因为其问题复杂和意见纷争而对其功用一笔抹煞。因此,刘康既可以强调中国“后学”的问题焦点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中的位置,又可以明确表示自己“对所谓‘中国的后现代’这一说法持强烈保留态度,而主张用‘现代化不同选择’这一概念来讨论中国问题,这样也许有助于克服‘后学’理论中的历史一元决定论。
”[110]这种有尺度感的理论判断和价值判断,有助于克服“后学研究”中的茫然性和盲从性。[111]
五,“后学”问题与反省。
在我看来,海外后学研究或批评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说明海外华人学者关注中国现状问题,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同时注意批评西方后殖民霸权,强调中国后学研究中正当的学术立场。值得指出的是,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关心,使他们越洋看中国并做出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后学”研究无疑有促进作用。
而他们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以及对西方新的学术资源的吸收转化,对我们同样不乏启发甚至解蔽功能。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问题不是已经解决,而是因为问题的敞开而更加突出,这促使我们既进行时髦理论的反省,又面对中国改革现实的具体问题。应该说,后殖民时代的问题很多,当代知识分子在强调自己的本土独立性的同时,又常常标榜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二者在矛盾中却似乎又相反相成:作为世界公共权力话语场中的一员有着“走向世界”的自觉,但同时在整合进国际新秩序中时又深隐着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
民族文化身份成为自身的本土身份符码,而身份确认之时又向往成为世界公民。
应该说,在对西方的新冷战式对抗时,只能获得一种狭隘的身份意识,这有可能既断送了现代性也断送了本土性。只有在东西方话语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
后殖民语境中的问题使我们明白,当代中国问题决非任何单一模式可以解决,这种呈现交织状态的话语纠缠,使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变得相当棘手。这要求我们必须既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同时也厘清全球化理论的某些误区;既清醒地审理这些日益严重的网状问题,又不是情绪化甚至煽情式地决然对立,从而对新世纪跨国际语境的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走向,对复杂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中的华夏文化策略有着正确的意向性判断,并有效地重塑新世纪的“中国形象”。
[1] 杜维明,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工作,主要著作有:《人性与自我修养》,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新加坡的挑战》,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北:联经,1989年版;《儒家思想新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一阳来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2] 杜维明等《自由交流现代化的忧思——访杜维明》,载广州《南方周末》,1998年1月9日。
[3] 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0页。
[4] 同上书,第453页。
[5] 同上书,第458页。
[6] 同上书,第468页。
[7] 同上书,第478页。
[8] 杜维明在《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1995年3月20日在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讲演)中说:“文化中国包括了一批和中国与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其中当然有学者和汉学家,但也包括长期和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媒体从业员和政府官员。
对于中国文化问题,他们常常是通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韩文和其它语言来加以了解。我提出这个观点,在台湾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也许他们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兴趣。在香港,有很大的反响,说把外国人加入文化中国有点不伦不类,很不赞成。”
[9]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杜维明的“文化中国”中过分明显的宗教情绪提出了质疑。德里克在《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中指出:“在最近一项关于‘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提议中,杜维明把非华裔汉学家包括在他的‘文化中国’概念的第三域(realm)内,第一和第二域分别指本土中国人和海外华人。
”“像杜维明这样的儒学复兴的倡导者对中国的过去给予相当不同的评价,但根据权力关系,他的立场揭示出一种类似的、得益于他作为西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地位的精英主义(elitism)。
在谈到文化中国时,杜指出,一个文化中国的创造必须从‘周边’(periphery)到‘中心’,从海外华人到在中国的中国人(或用这里所用的隐喻来说,是从‘接触地带’到中国本土)。
就中国社会来说,中心—周边这种划分意味着‘文化中国’的创造要通过来自几乎无权或根本无权的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对权力中心进行改造来完成。这是中心—周边的模式通常所意味的权力的完形”。载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第93页。
[10] 李欧梵,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狐狸洞话语》,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铁屋中的呐喊》,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版。
[12] 李欧梵《1997后的香港∶国际性大都会的臆想》,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6月号。
[13]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北京《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4] 参李欧梵著《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