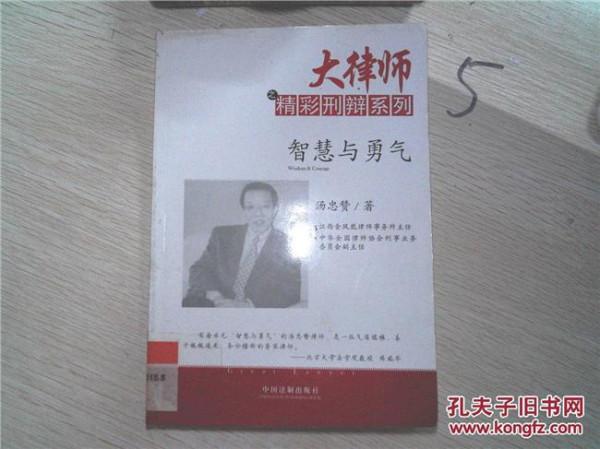吴法天律师 吴法天:刑辩律师的执业风险
尊敬的江平先生、陈光中先生、贺卫方先生、张思之律师,各位法学同仁上午好!在座各位法学前辈是我在学术上的先生,大律师们是我实务上的老师。
作为各方面的小字辈,我要向诸位学习。今天没有什么准备,即兴发言,我就以我作为刑辩律师的体验汇报一下,请方家指正。 我是兼职律师,先交代一下我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背景:我研究生专业是刑事诉讼法,博士专业是证据法,后来博士后又研究刑事证据和刑事诉讼法。
目前主要给研究生讲《证据法》和《刑事诉讼法》两门课。我想,如果我没有从事过刑事诉讼实务就给学生讲刑事诉讼,就好像自己没有游过泳的人较人家游泳,不太负责任,毕竟“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是10年前考的律师资格,但做案件是这几年的事情,主要是以刑事案件为主,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所以能够更纯粹地从事收入低、风险大的刑事辩护。
我做刑事案件有几个原则,一是从来不问报酬,如果是有意义的案件免费也做,争取把各种类型的刑事案件都做一遍;二是从来不走关系,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京外,无论是基层、中级还是高级法院,不管多大的案子,有违职业道德的事情我不介入;三是在执业过程中很注意自身的安全,原则上不主动调查证据,通常申请法院调取或者协助当事人调查但不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以免刑法第306条把自个儿整进去。
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自己的当事人嘛。
但是,即便如此,在执业的过程中,我仍然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阻力,见识到很多刑事诉讼的“潜规则”,即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却行之有效的定律。我曾经在给学生讲《刑事诉讼法》课的最后一次课里,用4个小时讲了大约30条潜规则,结果有学生居然因此打消了做律师的念头。
前几天在政法大学我还遇见我在北大、清华研究生院时带过的法律硕士生,他们作为实习律师在那里接受律协的培训,主讲老师很“善意”地提醒他们执业以后不要从事刑辩。
我们环顾左右,还有多少律师在从事刑事辩护?北京律师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已经不到1件。有多少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没有辩护人?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80%还多。以我“以身试法”、从事刑事辩护这几年的体验来看,刑辩律师面对的风险是制度性的、系统性的,下面我就以最为典型的一些无罪辩护案件为例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个方面,从刑事诉讼的“潜规则”来讲,我认为当前的刑事诉讼依然是奉行有罪推定模式,无罪辩护几乎是在“与虎谋皮”。
2007年我们曾经给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了一个《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的学者建议稿,我是北京某法院试点的负责人。在该法院我观摩了四个刑事案件并全部录了像,其中有三个案件的证据是有问题的。
如果严格按照证据规则的话,这三个案子都应该判无罪。审判长告诉我说该院已经很多年没有无罪的案件了,不敢判。最后这三个案子,两个撤诉,一个缓刑。我发现,虽然刑事诉讼法有规定,但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凤毛麟角,从事刑事辩护的成功率很低。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可能存在以下原因: 1、未决羁押制度。在我们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羁押是常态,取保是例外,尤其是外地人犯罪的,基本上都是拘留之后就逮捕。如果被告人在审判之前已经被逮捕了,那如果证据不足被判无罪,就会涉及到国家赔偿,司法机关会尽量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于是就有了“实报实销”,关多久判多久,总之是实际刑罚不会比关押的时间短。
2008年时我代理过一个很小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在元月就被羁押了,但一直以各种理由延长办案时间,原定8月份开庭后来也因为奥运会推到了10月份,虽然证据不足,但被告人已经被关得绝望了,不得不认罪,结果判了一年,判决生效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刑满释放了。
2、诉讼权力运作。刑事诉讼法其实赋予办案人员很大的权力,公安、司法机关可以合法地使用各种手段达到定罪的目的,比如公案机关自己就可以决定各种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强制措施,而律师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会见、阅卷和辩护却处处受到限制。
延长羁押期限、补充侦查、撤诉之后再起诉,这些都是合法的。我曾经办理过一个唐山的敲诈勒索案,被告人在调查中发现了一家污染企业并向上级部门举报,对方收买不成就栽赃,警察和对方称兄道弟,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就被刑讯逼供致残了。
开庭的时候除了报案人的陈述外几乎没有其他证据,声称作了记号的2万元赃款早就发还给被害人了,证物都没有,审不下去了。检察机关就撤诉,但被逮捕的被告人未被释放,过了一个月又起诉了,法院说如果做无罪辩护就再休庭,被告人60多岁了,在看守所里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还不准取保候审,他们家人怕他死在里面,就请求律师放弃无罪辩护,法院最后判了个缓刑。
3、不独立的审判。刑事诉讼法规定有独任庭、合议庭,但是无罪辩护的案子绝对不是审判长、审判员所能决定的。我们的法官个人是没有独立的审判权的,拟判无罪的案子你必须通过请示汇报,通过庭长、审委会,有时甚至要政法委来协调。
一个无罪的判决,可能涉及到公案机关、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绩效考核,一个法官是很难自己作出这样的判决的,除非像佘祥林、赵作海这样已经曝光的冤案。我曾经写过一篇《司法能见度》的文章,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法律规定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法庭必须对庭审过程全程录像并制作光盘,当事人在庭审后可以以成本价购买该光盘;凡是法律规定应当公开审理并公开判决的案件,法院必须于判决生效后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判决书全文。
这两条建议其实国外都有先例,技术上也不难达到,如果能做到,我觉得可以实现“看得见的正义”,司法要独立就不难了。 第二个方面,我认为刑事辩护的风险还来自有关部门和组织的工作人员对刑事辩护的抵触态度。
社会上一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分子,为他们辩护就是替坏人说话,其实无罪辩护中很多被告人本身是无辜的,为他们辩护本身是在维护法律的公正。但有些办案人员不能正确认识这一点,认为为他们维权就是影响“和谐”。
在我有限的经历里,比较典型的案子,就是最近的张远洋案。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轻微刑事案件,但现在已经被人为复杂化。一个叫张远洋的未成年人,他和他姥姥在2006年的时候因琐事被人打了,他姥姥被打成十级残疾。
凶手后来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他高考完就出国留学去了。2009年回国探亲时他被警方抓了,说人家告他当时也有伤害动作。但庭审的结果是,被害人与控方证人的陈述破绽百出,人体损伤的鉴定结论是没有鉴定资格的主体作出的,公诉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发生。
但在审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很匪夷所思的现象:我刚接受这个案件委托时,法官就找到我们政法大学的主管副校长,要我谨慎代理这个案件,不要给政法大学带来什么麻烦。
庭长和承办人找我谈话,说“律师也要讲政治”,要我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有一次开庭的时候,庭长(非合议庭成员)要对被告人单独问话,我说律师请求在场,庭长当庭呵斥说“把律师驱逐出去!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程序违法的地方。这么简单的案子,法院审理了7个月,开庭了7次,最后还是难以下判。审判长亲口跟我说,这个案子不是她所能决定的。 这个案件一个至今让我不能释怀的插曲:在一审的最后一次开庭前,被告人家属与检察官发生了争执,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法院把我们一行包括律师扣留了十个小时,凌晨两点才让我回家。
后来,被告人的三位家属因“扰乱法庭秩序”被司法拘留了,拘留期满后又被刑拘,随后被逮捕、起诉。
我曾经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过律师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的事情,没有答复,我也向律协、司法局反映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重视。我在博客上披露了这件事情的一些细节,有关部门就让司法局找我谈话,说我“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网民攻击我国司法制度”,要对我进行“批评教育”。
我在这儿披露这个事情,不是说我对律协和司法局有什么抱怨,实际上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维护刑辩律师权益的角度为我们多一些考虑,当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的时候,多一些关爱,我们才能更有勇气地去承担刑事辩护的责任。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以自己的一些切身体验为大家研究刑辩律师的处境提供一个标本,对于“怎么办”的问题我也很迷茫,因为这个大问题显然不是我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的。
不过,作为刑辩律师,我认为虽然道路很艰辛,但所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只要我们能有策略地战斗,是可以看到胜利的一天的。作为大学老师,我会把自己对于刑事诉讼中公平、正义的理解告诉学生们,为我们的司法输送更多的新鲜血液,等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法治的面貌会跟现在不一样。
我现在还年轻,应该能等到那一天。 最后我想用一首小诗结束我今天的汇报,这是2006年我在台湾时在民间司改会看到的,说我有一个梦想,期待有一天,守法的人不再孤单,违法的人心有畏惧,司法为我们许诺一个公平的审判,一个体现正义的社会。谢谢大家!■










![[北京]著名刑辩律师李在珂招聘律师助理](https://pic.bilezu.com/upload/b/fb/bfbcf98903c22b6559b82778056cdbeb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