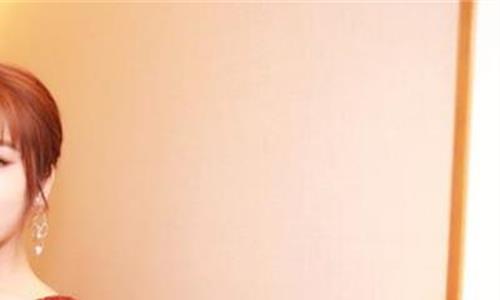陈东东北方 陈东东:诗是一种方式
1980年10月的一个下午,我坐在上海师范大学主楼第五层的期刊阅览室里,面前是一本已有些破旧的《世界文学》(1980/1)。我刚来了19岁生日,考进那所大学的中文系也才一个多月。三个月前,在预备高考的紧张夏日,我曾偷闲翻看过艾略特的《荒原》,终因不知所云而没能卒读。当时,我对诗的理解主要来自《唐诗三百首》之类的读物,我还不曾写过诗或填过词。秋天的阳光照得橘黄色的杂志封面微微泛红,这正是一个宁静安逸,适合闲览的下午。
但是,突然,仿佛被人在背后狠拍了一掌,我从漫不经心的状态中惊醒了——我看到这样的诗行出现在纸上:
姑娘们如卵石般美丽,赤裸而润滑,
一点乌黑在她们的大腿窝内呈现,
而那丰盈放纵的一大片
在肩胛两傍蔓延。
她们有的直立着在吹海螺
其余的拿着粉笔
在书写奇怪而不可理解的文字:
这是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长诗《俊杰》中的一小节,它带来震颤!它那宏伟快捷的节奏凸现给我的是一群如此亮丽的诗歌女神!于是,一次作为消遣的阅读变成了一次更新生命的充电,诗歌纯洁的能量在一瞬之间注满了我,并令我下决心去做一个诗人。
黄昏到来,我带着抄满埃利蒂斯诗篇的练习本下楼。在回宿舍的路上,诗歌已不仅是“僧推月下门”或“僧敲月下门”了,它是灵魂革命、绝对信仰、肉体音乐、精神历险和真正的生活!第二年春天,在一堂沉闷的哲学课上,我写下了我的第一首诗。
埃利蒂斯成为我和诗歌间最直接的导线,但如果要回答“为什么写诗”这个问题,却不能简单地停留在透明清澈的大师那里。埃利蒂斯第一次打开了我诗歌的视野,诱发了我身体内部语言的激情,而一个诗人的真正源泉,必定是他心灵的激情。这种心灵的激情,与诗人的童年经验、友谊和挫折、恋爱、肉体的损伤、处身众人之中的孤独、对四季的敏感、对风景尤其是海的渴望、对往事的追忆和对来世的预想都十分有关。在我这儿,这种心灵的激情更出于展开音乐的企图。似乎是因为我对音乐的暗中热爱和实际上对它的无能为力把我引向了诗歌。我愿意引用另一位诗人,美国人阿什伯利的话来说明我这种由于音乐而选择诗歌的命运:“我感到我能在音乐中最好地表达我自己。我喜爱音乐的原因,是它能使人信服,能将一个论点胜利地推进到终结,虽然这个论点的措辞仍然是未知量。保存下来的是结构,论点的建筑方式,风景或故事。我愿在诗歌里做到这点。”
或许我可以这样来回答:我写诗是因为我充满了演奏的欲望。我的乐器是语言,我的乐谱是时光、景色、女性、沉默、书籍、有待升华为精神的物质生活和几乎从未间断的回忆、梦幻和孤独寂寥。
这样,在说出“为什么写诗”的时候,我已经涉及了“什么是诗”。对我来说,诗就是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