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资料 他们将要做出些什么样的事——谈夏衍的三幕话剧《自由魂》
以秋瑾为题材和主要角色的文艺作品,我以为夏衍的《自由魂》是最好的。 在这短短的三幕话剧的篇首,夏衍引用德国剧作家莱辛在《汉堡演剧评论》中的一段话概述他此次创作的要旨: 有一种没有根底的见解,以为演剧的职能只在保留伟人的面影,但这只是历史的任务,而不是演剧分内的事情。
我们在舞台上应该学习的,不是这人或那人做了些什么,而是在具有一定性格的个别的人物,被安置在特殊的环境里面,他们将要做出些什么样的事。 在阅读整部作品后,有一种触动直击胸口。
而夏衍的文字却是平静而充满思辨的。革命者的热血并未被涂上油漆般浓烈却呆板的色彩,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真切。 关于秋瑾,自从她慷慨就义,后人都以崇敬的心与眼看待她生前的所作所为。
第一个书写她的人大概是鲁迅,只是他为她改了名字,在短篇《药》中用曲笔表达了他对革命者的敬意。那个流血的夏瑜尚未唤醒民族的魂魄,他的牺牲还需等待时代的觉醒。第一个以秋瑾为原型而创作这一段历史题材故事的,也许就是夏衍。
与几十年后的两部以《秋瑾》为名的电影作品相比,夏衍所塑造的鉴湖女侠多面而立体,而他自身的革命者身份又使他看待革命阵营的眼光有别于生长在和平年代的编剧。也许可以说,夏衍的《自由魂》是以革命者的眼光来回看前辈,从而审视革命的性质与革命者的责任和担当。
今人谈到革命,早已五味杂陈,讳莫如深。但夏衍在1936年的上海创作这部剧时,时代赋予革命的意义远别于今日。自清末始,革命的浪潮已然在中华大地上拍打无数惊涛骇浪,可谓死的死散的散,到抗战爆发前夕,处于一个短暂的低谷期。
也许早从1927年始,革命一词的含义就已出现较大的分化与差异,社会上对革命一词的普遍看法不再如从前那样较具备统一性。
夏衍早年参加国民党,后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创作《自由魂》时,他的心情和感想一定不同于一般创作者。而作为革命阵营中的老资格,他所观察到和接触到的又使他注意到这一阵营中存在的复杂性,也许是理工系出身的缘故,尽管夏衍常年从事文艺创作,但他的文字所表露的思想和情感却是理性的。
《自由魂》篇幅很短,只有三幕,分别以1900年、1903年和1907年为时间节点,讲述秋瑾生命中三个不同阶段。1900年时,正直庚子之乱,秋瑾还是一个年轻的少妇,与丈夫一同避难南下,回到绍兴老家。
通过乡民、县官和秋瑾夫妇的人物对话,1900年的中国民间百态已经活现于眼前。民众的愚昧无知,教会势力的为非作歹,官府的腐败无能,义和团的凶狠愚弱都从几方面言谈的碰撞中自然地表达出来。
此时的秋瑾单纯而充满正义感。她鄙视官府的无能,为百姓的愚昧感到痛心。然而她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满腔不平。但我们已可以感到,她所观察到的现实百态已经深深刺痛了她的心灵,她的人生也会因此而有所改变。
当剧情发展到1903年,已回到北京过着衣食无忧之生活的秋瑾不再满足于看报纸发牢骚,而是下定决心到日本去求学,甚至做好了离婚的打算。这一时期的秋瑾,有一腔热血,但夏衍通过挚友吴兰石的语言,表达了对秋瑾的担忧。
她是一个多年在富裕家庭里养尊处优的少奶奶,虽然年届三十,但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世界。而她性情上的冲动并不能看做改变中国命运的良药,尽管丈夫王廷均显得迂腐而懦弱,但夏衍却并未一味贬低或嘲弄他,他对秋瑾提出的规劝是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而得出的。
他有他的立场也有他的局限性,但并不代表他的话都是错误的。 革命者不是圣人,称号无法代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品性与人性。对于秋瑾性格上的弱点,夏衍毫不客气,借吴兰石之口加以指出 非但不知道隐藏,还好像唯恐旁人不知道她是革命党,讲话不肯让人,为了一点儿小事情是人家过不去!
鲁迅曾在东京听过秋瑾的演讲,据说他并不十分热衷于慷慨激昂的革命,并曾因此受到过秋瑾的责骂。
我们当然不应该要求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与社会做抗争,有人用身躯,有人用笔端。秋瑾去国前夕拜访过吕碧城,曾力邀吕一同赴日。但吕碧城并没有与秋瑾同行,而是留在国内以文章为女权和女子教育事业谋求良策与发展空间。
某种角度看,吕碧城与鲁迅选择了同样的战斗方式,尽管他们的斗争方向并不一致。秋瑾是革命先驱,也是少有的女性革命先行者,行为令人敬佩,但却也并非完人。咄咄逼人是她性格上的缺点,而不够谨慎的性格特征或许就是她革命失败的某一条导火索。
夏衍并不因为她是可歌可泣的革命者就粉饰她的人性,故意将她塑造成高大全式的人物。秋瑾的单纯和鲁莽是她性格中不可改变的成分,但她的热情与爽朗又恰是那些负面成分所折射出的另一重光彩。
后者使她革命者的形象更为光辉,但前者却让她是一个难得的,活生生的人。 关于革命党人的责任,夏衍在1907年的那场决定秋瑾生死的起义中做了探讨。秋瑾的同志是程毅,两人最后双双为革命而牺牲,可谓侠肝义胆。
但他们又是不同的两种人。秋瑾热烈,程毅理性。秋瑾求死,程毅惜生。在秋瑾看来,“杀身成仁,是革命党的本色。”而程毅的看法是“孤注一掷也决不是革命党的光荣。”当秋瑾希望以死来承担革命失败的责任时,程毅反问:“死,能够减轻责任吗?”我疑心夏衍将自己融入了程毅,以理性的认知穿越时光,回到他出生的时代,走近这位壮怀激烈的同乡女杰,向她提出自己对革命的一些看法和认知,做一场想象中的对话。
显然,夏衍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革命并不是一味求死,并不只有杀身成仁那么简单。因为革命不是戏剧,不是为了英雄的出场而演给别人看的。革命者有他们的目的和使命,而要完成这些,需要鲜活而强有力的生命。
革命者当然应该歌颂,但革命者首先是人,不做无谓的牺牲,也不做无谓的英雄。 当程毅在衙门受酷刑而不改初衷,坚决保护同志,不禁想到话剧完稿几十年后的夏衍,在那样一个年代,因不肯诬陷他人而被从台上踢下,摔断腿。
夏衍曾经将心灵化作程毅,在那一刻,他的身躯是另一个程毅,只可惜已没有秋瑾并肩。 回到莱辛的那句引言,夏衍写秋瑾,不是为了记录她的丰功伟绩,那是历史的事。作为戏剧创作者,夏衍想要追寻那个艰苦年代里秋瑾的选择,也许通过秋瑾在特殊的环境里将要做出些什么样的事来思考自己在另一个特殊环境里应该或即将做出什么事,也在为同行者们思考大家将要做什么事。
这也许是夏衍在1936年的初衷。至于一切的后续与影响,还是留给历史评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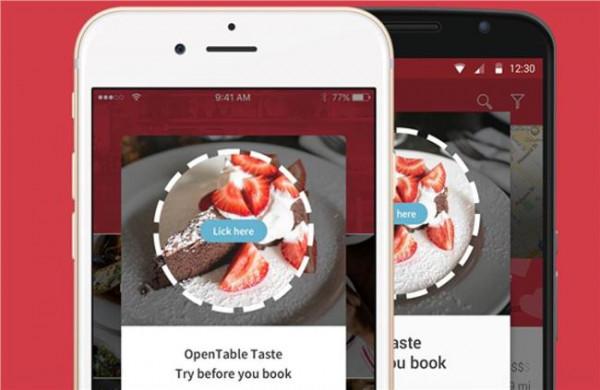












![包身工夏衍猪猡 包身工[夏衍所著的报告文学作品]](https://pic.bilezu.com/upload/d/4a/d4aaa53b392fcb5d1be3eb362a04d7e1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