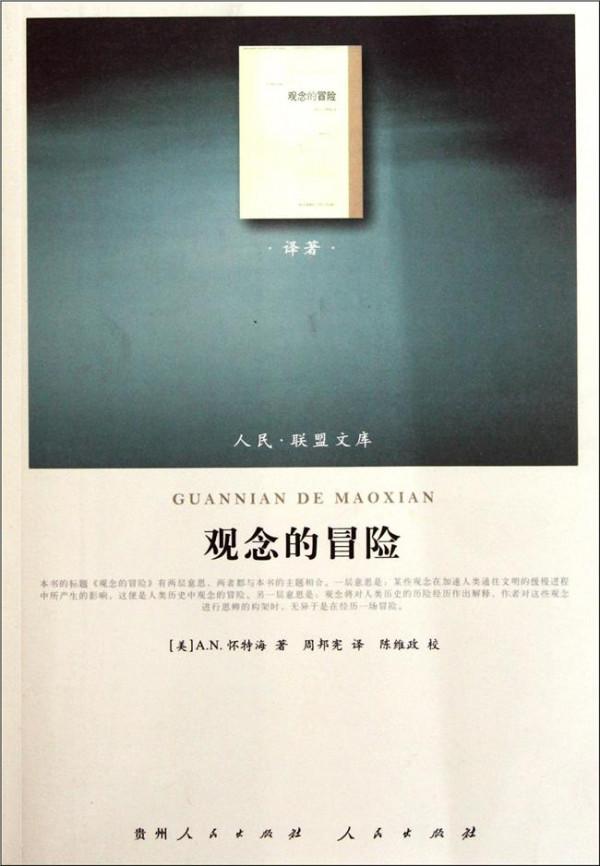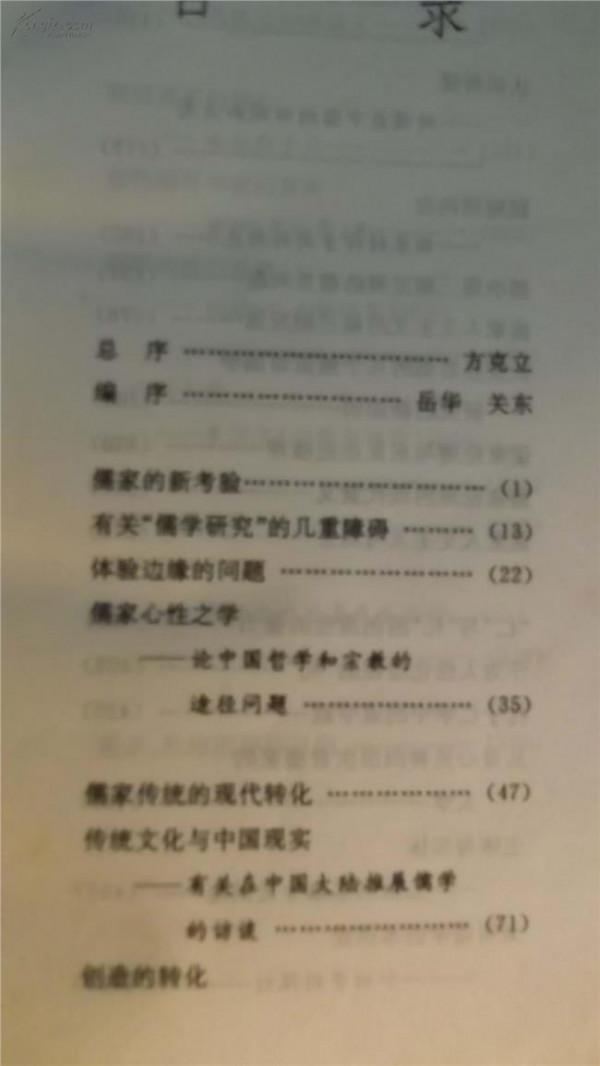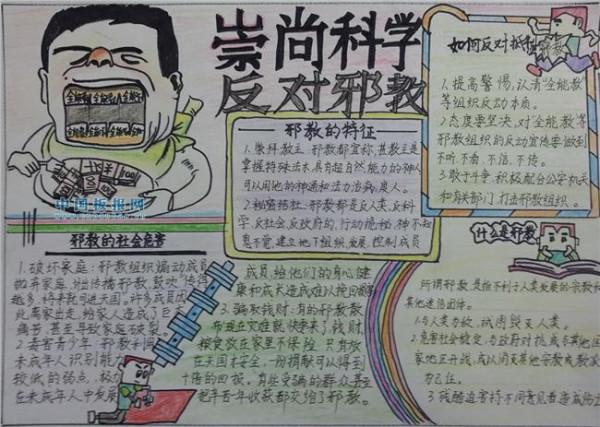杜维明演讲 杜维明武汉大学演讲: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
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在武汉大学的演讲,1997) 各位师长,各位同学,我很荣幸能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到武汉大学来进行学术交流。两年前的暑假,我曾在这里介绍有关文化中国和儒学创新的一些相当肤浅的看法。这一次应新成立的中国文化研究院和哲学学院的邀请,把一些还不成熟而且还正在发展的观点给各位介绍一下。
一方面与各位见面非常兴奋,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有些惶恐,因为我要谈的这个课题太大,能够很平实地把现在还在发展的观点说清楚就不太容易了。
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道主义或者说人文学,是近十年来在国内渐渐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关切的课题。我今天的观点非常简单,那就是:当代人类社会既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本土化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代。
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的认识(也可以说是成见),然后把它作一简单的分疏,作为讨论这一问题的背景来了解。另外,我要提出自己考虑的问题,即我是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然后从这一方面来谈谈全球伦理。
最后谈儒学的创新对全球伦理的特别意义,归结到目前美国知识界讨论得特别热烈的问题:公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问题。 我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现在面临两个相互冲突而又同时并存且影响相当大的基本潮流(我没时间来详细地解释这两大潮流):一个是全球化的现象——无论是通过市场,科技、企业、旅游,甚至是从疾病和环保等方面看,都有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另外一个是本土化现象。
最近二十年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都遇到了全球性与本土性、根源性相矛盾的问题。具体地说来,本土性就是族群意识,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乃至宗教差异性。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对全球化有特别的理解。
在美国,如果族群问题如黑人与白人的问题处理不好,美国就可能由联合各种不同社群的统一国家变成分裂的国家。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阿瑟·席来辛吉(Arthur Schlessoper,Jr)说,美国将会由united states。
成变disunited states,即变成一个分裂的国家。美国最敏感的问题就是种族问题。另外,加拿大、比利时都碰到了语言的问题。如果法文和英文不能和平共存,加拿大的魁北克就会出现分裂的问题。
如果弗莱芒语(Flemish)与法文不能共存,比利时这个国家就会出现分裂问题。如当今著名的鲁汶大学就分成讲法文的鲁汶大学和讲弗莱芒语的鲁汉大学,这两个鲁汶大学看起来就不可能重新统一。
性别的问题,也就是说女性主义的兴起,使得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权力结构、工作的时间和工作的习惯等各种其他的日常生活都要重组。地域的问题如巴勒斯坦的主权问题、印第安人的主权问题、夏威夷的主权问题、欧洲巴斯克(Basque)的主权问题,还有其他各种不同性质的主权问题。
阶级的问题在以前只讲南北的差异,讲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差异,现在南北差异不仅在全世界存在,而且在同一个具体国家,同一个社会,甚至在同一个单位都出现了。
年龄的问题以前认为三十年算一代,现在发现十年就有代沟问题。在日本就有“新人类”乃至“新新人类”的种种说法,在中国台湾地区这种说法现在也用得很多。70年代、80年代出世的人与前面两代人的价值观念、处世方式亦有相当的不同,甚至在大学四年级与大学一年级之间亦有代沟问题。
同样地,在家庭的兄弟姐妹之间也会出现代沟问题。宗教问题,以前大家担心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如回教与犹太教、锡金教与印度教、回教与基督教等之间的冲突。
现在是宗教内部的问题,保守的犹太教与自由开放的犹太教、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和保守的基督教的冲突,甚至佛教内部,如藏传佛教即达赖所代表的藏传佛教内部也有冲突。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另一方面,本土化的问题通过族群、语言、阶级、性别、地域、年龄、宗教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尖锐。
既是全球化,又是本土化,造成了当代文明内部的一种矛盾和张力。这两股潮流不只是发展中国家才碰到,而是任何发达国家都会碰到。
在这样一个复杂矛盾的情况之下,不能只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不能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更不能把全球化当作一个西化的过程。正是全球化的意识,使得根源性意识越来越强。
也正是这一原因,我们不谈从传统到现代,而是特别突出现代性中的传统。最近,我编了一本书,由哈佛大学出版,书的名字叫《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当然传统不仅有儒家的传统,也有基督教的传统,回教的传统,精英主义的传统,心灵积习的传统等各种不同的传统,这些都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而不简单的就是从传统到现代的问题。
另外一个课题是:现代化如果不是西化,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文化形式?有没有东亚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可能?如果有东亚的现代性,这就意味着将来可能有东南亚的现代性、南亚的现代性、拉美的现代性,甚至还会出现非洲的现代性。
这也意味着西化所代表的现代性是一个分歧的观点而不是一个统合的观点。
英国的现代化和美国的现代化、德国的现代化、法国的现代化、意大利的现代化都有所不同,这是一个事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民主在英国的发展和传统的渐进以及经验主义和怀疑精神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传统性在英国的民主化过程中有突出的表现。
而法国的革命性以及对宗教问题的执著,对法国的民主有非常重要的导引作用。德国的民族认同性和怀疑精神对德国的民主进程有非常重要的导引作用。美国的市民社会(亦即公民社会)对民主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的社会比它的国家远远地更有力。国家可以说是社会中的一员,和东亚社会政府的力量特别强,有的时候社会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这都只能是不同的传统对现代化的进程发挥不同的影响而已,很难就判定说不同的现代性就是如此发展出来的。
我因为讨论全球意识和本土意识之间的交互影响,提出了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和现代性的多元倾向,这是我目前关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认识。 通过上面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我今天想提出的一个课题是,“启蒙心态”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说是现代人类文明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这一启蒙精神所代表的人文精神,能不能够从不同的文化传统来对它进行反思、批评? 从西方17世纪、18世纪开始的“启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理解:启蒙是西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西方发展出的文化现象,它从18世纪产生,延续到19世纪直到欧洲中心主义出现,这是一种启蒙文化。
其次,启蒙也可以算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突出理性主义。
至今,许多学者还认为这个理念没得到充分的发展、充分的落实,我们还应该让启蒙在西方世界继续发展。启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启蒙作为一种理念是有所不同的。但我今天所提到的“启蒙心态”既非历史现象,又非哲学理念,而是一种心灵的积习,这正是我要讲的“启蒙”的第三个方面的意思。
这种心灵的积习在现代中国的转化,在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这一“启蒙心态”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即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文精神。
当然,如果溯源到更早的时期,则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这种人文精神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以及从事中国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中,这一文化心理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说服力最大。
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分开来,那么,今天在我们文化中国还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乃是西方“启蒙心态”下的“人文精神”通过中国社会的改造成为中国重要的意识形态,这种启蒙心态在我们心里所引起的影响力要远远超出传统文化。
我这里所指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家的传统文化、道家的传统文化、大乘佛教以及民间的各种宗教。这是一个我认为值得注意的特殊问题。 我现在要考虑的是:能不能从传统意义下的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对西方“启蒙”以来发展起来的“人文精神”而又在现代文化中国的知识界影响极为深刻的这一种形态(也是一种人文精神)进行反思,进行批判?有没有这种可能?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传统文化因素远远没有西方“启蒙心态”所代表的”人文精神”通过中国化这种转化而成为我们文化心理结构的力量那么大。
西方“启蒙心态”所代表的这种“人文精神”,到底有什么属性?我认为,这种“人文精神”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即以人为中心,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是从一‘启蒙心态”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强调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从工具/目的的角度来理解理性的,就是强调理性有没有实用性,有没有价值,对我们有没有用。
假如没有用,则这种理性对我们就没有价值。这是一种强烈的物质主义,是一种科学主义,是一种实用主义。而其后面所根据的重要理据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富强是价值,不能富强就是非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反对神性。这与西方启蒙以来“凡俗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有密切关系。工具理性的突出、目的理性的突出,忽视了沟通理性,而沟通理性通过谈话、辩难,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对富强没有一定的价值,但通过沟通,通过理解,通过认识,慢慢地发展我们的人文资源。
这种沟通理性比较薄弱,人文资源就比较匮乏。相比较而言,物质主义就相对地轻视精神价值,重视科学主义就相对地轻视人文学,如文学、哲学、历史和现代讲的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之类的学问。
实用主义色彩特别强的话,各种理想就会被视为没有道理的空想。 我们现在的人类社群碰到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撞击。美国的人文学者在重新对人文学进行反思时认为:面向21世纪,任何一个人类群体如果要进一步的发展,它就应该掌握各种不同的资源。
除了经济资本之外,还应该发展社会资本;除了科学和科技的能力之外,应该发展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之外还应该发展伦理;除了物质条件之外还应该发展精神价值。
即使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如果社会资本积累得不够,文化能力不强,伦理没充分地展现,精神价值荡然无存,即使在富强方面,在经济建设各方面有短期的富强,取得突出的成就,但前景是值得忧虑的。
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资本不能量化,它是要通过了解、沟通、对话,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来积累的,比如说对一个大学进行调查,对一个系进行调查,看它们有没有社会资本。如果说,院和院之间、系和系之间没有什么沟通,这个大学可能有很大的潜力,比如财务状况很好,但这所大学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却相当的薄弱。
一个系,没有横向的沟通与了解,没有相互之间的论谈,这个系也就没有积累很多社会资本。一个社会和国家亦复如此。
文化能力不能通过知识的膨胀来取得。文化能力一定要通过体验,没有别的路可走,正如学钢琴要去学要去弹一样。如果没有实践,没有在日常生活中让它展现出来,这种文化能力是不能被掌握的。在储积文化能力的过程中间,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身心性命之学慢慢地累积,一代人不能传到另一代。
每一代人都要通过身心性命之学的体验来掌握文化能力,而这种工作是很缓慢的。传统中国社会成员,其文化能力的培养常常在家庭,而在家庭里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常常是母亲,儒家的精神之所以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不是靠知识精英,不是靠大皇帝的命令,不一定靠正常的学术规范,而主要在家庭里面靠母亲的身教传下来的。
这种说法很容易理解,在今天我们还有切身体会。
中国17世纪有一个思想家,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应该向两个无父之子学习。这两个无父之子,一个是孔子,他在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一个是孟子。这两个无父之子能够在文化上有那么突出的表现,因为他们都是通过母亲的身教发展起来的。
母亲常常不识字,所以不要把识字能力与文化资源混为一谈。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没有文化,这个人不识字,但这个不识字的人,往往有很多精粹的文化价值在他的生命中体现出来,这种传播是一种文化能力的培养。
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假如这种文化传播能力被减杀了,即使有高度的科技能力,文化能力也会被冲淡了。除了智商以外,美国常常说情商,即通常所说的Emotional Intelligence,我想这不太合理,但是实践的伦理,对于伦理而言,即是讲做人的道理价值,我们叫它Ethical Intelligence,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价值也不是从正规的学院里能学到的,一定要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
一个社会如果它的伦理素质受到了很大的摧残,特别是在急速转化的社会,它的滑润剂,即社会能够运作的很多非量化的机制受到了破坏,也是值得忧虑的。一个社会的精神价值的培养不能从上到下,不能用完全政治化的方式来提倡。
如果社会资本的累积不够,文化能力不强,伦理的素质在减杀,精神的价值不能开拓,即使有雄厚的经济资本,有高超的科技能力和智商来作物质条件,这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则是一个变型,这是非常危险的。
作为一个从事人文学研究的人,在看文化中国的时候,我们觉得最忧虑的一个问题是,整个文化中国,中国的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以及散布在海外各地的华人社会,精神资源非常薄弱,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中的精神资源特别薄弱。
薄弱的原因非常复杂。如果我们仔细地来分析个中薄弱的原因,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间缺乏传统文化资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李慎之先生最近在纪念匡亚明先生逝世的文章中提了三个观点,我很同意他的这一说法。
他有三个观点对文化中国精神资源为什么那么薄弱作出的一个评断,我在这里只能很简单地提示一下。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有古有今的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考古能证明这五千年来的文化是有继承性的,有非常强的继承性。
但是,李慎之先生说,中华民族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中华民族的现代记忆,一百年来的现代记忆却非常短暂,而且断裂的情况非常的严重。一个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却又有非常短暂的现代记忆的民族,可以爆发出非常复杂的问题。
从鸦片战争以来,一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十年就有一次大的动乱。从太平天国到甲午战争,从辛亥革命到军阀割据,再到日本侵华,国共两党之争,每十年就有很大变化。而像中国社会的极重要的杂志《新青年》只存在了四年半的时间。
最近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庆祝它们创刊140周年。在这140周年里,该刊完全没有中断发行。明年,北京大学要庆祝一百周年的生日。有一百年历史的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比较悠久的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到五四时代的胡适之、陈独秀所在的北大,再到国民党控制下的北大,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大,这是完全不同的大学。
1949年以后的北大与1949年以前的北大,不仅不同,而且地方也搬了,从红楼搬到了燕京大学旧址那儿;“文革”时期的北大和50年代、60年代初的北大,教育的理念与价值观有很大的转变。
“文革”以前的北大和“文革”以后的北大也是完全的不同。如果你要去问北大资深的教授,了解或描述北大的历史,多半会是不堪回首。
这暂时不要讨论,而是要指向未来。这样一个大学在储备人才方面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其集体的现代记忆却是非常短暂的。如果从北大扩大来看各种文化组织,现代中国的各种社会组织能够有十年历史就很难得了。
许多杂志三五年出了第一期就不能再出了。许多学会成立了三五年就解散了。有些政党能够维持很多年,但是它的党纲,它的宪法,它的内部机制也有急速的改变。在美国的一个学会即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院,1798年发起的(是后来的波士顿地区做了美国总统的亚当斯要和费城地区弗兰克林组织的美国哲学学会相抗衡,在波士顿也建立了这样一个荣誉学会),我在1985年和1986年去作报告的时候,介绍我的史华慈教授说:这一次杜教授的报告是第1672次的报告。
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学会每年只有七到十个报告,但两百多年来,学会每年的学术报告累积下来没有中断过。我服务的哈佛大学是1636年建校的,从1636年开始,即从中国的晚明开始,一直发展下来,从没有断。
也就是说每一年它出了什么事情,它有什么发展都非常清楚,都有记录。所以从历史上讲,美国和中国是有相当的不同,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其现代的记忆非常短暂,而且断裂性很强;而没有悠久历史的美国文化,这近三百年的文化承继性非常强,强到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有详细的史料。
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可以列举。历史的断裂,尤其现代史的断裂,使得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没办法累积。 因此,在我们的心灵积淀里面起最大作用的人文精神,是以近代西方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影响最大。
这种人文精神以对自然的破坏为主要特征。在中国古代,儒、道、墨都有关于人与自然的合理思想,如儒家的天人合一的观点,道家的与万物为一体的观点,佛教里面的很多观点等等。
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和自然如何取得和谐的机制破坏了。文化中国对自然破坏的情况十分严重,如空气的污染、水资源的破坏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破坏,其情况均令人担忧,有些自然的恩赐甚至被当作没有用的东西给抛弃掉了,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最近几十年有所好转)。
而有着深厚的可以跟自然传神的天人合一理想的文化中国,在实际上,特别在20世纪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是最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