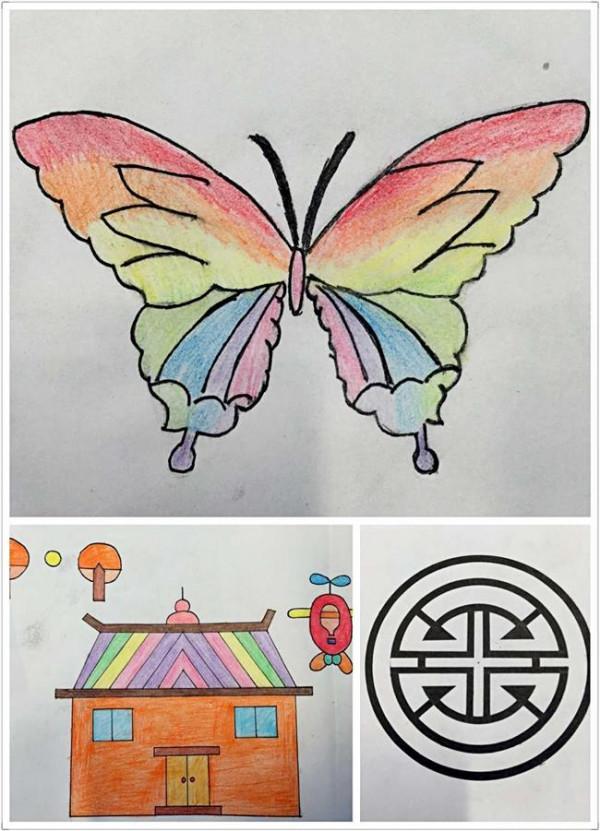王肇民水彩画图片 诗化的水彩画大师——王肇民
王肇民,这个名字在美术界是一个传奇:对于西方,他是“一百多年来写实主义绘画进入中国后达到成熟的标志之一”;对于中国,“他是当代中国水彩画最高成熟的标志”,“他是当今中国水彩画第一人”;他具“伟大的风格”。
然而,美术界知道较多的是他的绘画特别是水彩画的辉煌成就,而实际上他的绘画成就来源于他的诗痴、诗艺,来源于他的既古典又创新的中国文人诗化的情怀。他在诗词方面的成就不亚于绘画。可以说,他是诗意栖居的水彩画大师。
敢与今人争一流 艺林今古始称尤
2009年中国嘉德广州冬季拍卖会上,王肇民的一幅水彩静物画《美人蕉》以78.4万元的价格落锤,让所有在场的人惊羡不已。这一价位打破了一向不被人看好的水彩画的低沉局面,刷新了中国美术界的水彩画纪录。
他是美术界的“新星”吗?否。他是有什么特别“背景”的精英人物吗?否。
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人们不禁要打听他的来历。实际上,他的背景既简单又不简单:他是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此前的他于1908年出生于安徽省萧县这个历史上重文经武、书画之风颇盛的彭城之郊。青少年时代他是在家乡文风画韵的浸润中度过的。
1929年在徐州中学毕业时考入林风眠为校长的国立杭州艺专,参加“左联”领导的“一八”艺社,任研究干事。1932年因此而被开除学籍。旋经林风眠、王青芳等介绍转北平入以沈尹默为校长的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组织北平木刻研究会,被誉为“北平新兴木刻的播火者”。
1933年毕业到南京入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系主任为徐悲鸿)旁听。翌年复至北平,任私立北京艺专教授及艺术科职业学校训育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到家乡参加新四军,后任萧县民主政府民运科和教育科科员。1942年因父亲去世,赴重庆奔丧,即留渝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员工子弟小学教员。6年的流亡生涯,亦教亦诗亦画。1949年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市委文工团团员。
1951年至武汉先后任中原大学、中南文艺学院、中南美专讲师。1958年随校迁广州后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1979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离休后被聘为广东省美协和广东画院顾问。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第一个到巴黎举办个展的艺术家就是王肇民(1980年)。当时此展成为巴黎画坛的“盛事”。巴黎的《中国艺术丛刊》编辑部文章说他是“像徐悲鸿或林风眠那样的巨匠”,“水彩画大师和名家”。
在先生仙逝四年后的2007年8月,中国美协、中国美术馆、广东省美协、广州美院、广东省美术馆联合在京穗举办“百年王肇民”水彩画展,精选了大师上世纪70—90年代的水彩静物、风景、肖像人体画等计100幅。该展轰动了中国美术界。
众多美术评论家称他是“当今中国水彩第一人”,著名美学家迟柯教授赞其为“伟大的风格”。《北京晚报》当时载文称“王肇民的艺术,成了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重要个案”,“他在一个艰难的角度,验证了一个独立的、自足型的艺术家的个体价值,以自己的成就证实了艺术可以达到的一种近乎理想化的纯粹境界”,“可望不可即”。
林墉(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省美协主席、广东省画院院长):读王肇民教授的作品,“如狮虎之行于大漠,鹰隼之立于高岩,可以消除猥琐鄙吝之心,而向往于宽阔的胸襟、高尚的人格”,“超乎所有人画出了独有的一种庄正大度,坚实有力和厚重浑朴,在单纯明确的画面结构中,蕴蓄着一种迫人骨髓的张力”,“可以肯定地说,他和他的作品是当代中国水彩画最高成就的标志”。
他还说,王先生艺术的“光彩最突出处是诗意”,其作品“不论采取何类题材,采用何种手法,都抒发一种独特的东方诗意”。
张力克评说:“王肇民是我国当代当之无愧的水彩画大家。他对于我国水彩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画品和人品令人敬仰。他丰富的绘画实践经验和绘画理论,给了我们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和有益的启示,是我们宝贵的艺术财富。
解读王肇民的人和画,可以使我们在当下绘画界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拜金主义和急功近利的风气中,就如何做一个有操守、有追求的艺术家,如何选择适合个人的艺术发展道路,如何进行艺术上的继承与创新,如何使艺术为大众服务等问题,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并且称赞他做到了“理论与实践、自然美与艺术美、继承与创新、个人艺术追求与大众需要、人品与画品”的“五统一”。
诗情每逐画情去 笔端磅礡吐虹霓
“诗画学来自幼冲,诗情画意每相通”(《诗画》)。王肇民先生曾述因“北伐”“停学家居,习为诗”,“后就读燕杭艺院”。他是先学诗后学画,诗艺先于画艺。这为他终生“边画边诗”既奠定了基础也确立了“路线图”。正如许多大文人并未以诗歌为业却成就大诗人一样,虽然他最早和终生的职业是画事,但是他最早公开行世的作品却是诗集。
早在1943年,即他赴渝奔丧的第二年正月,那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孤身外悬、丧父别妻的孤苦生涯,点燃了曾作为新四军战士的王肇民之心中诗火,“得数百首”之“心血点滴,生命所寄”,“抄为三册”,并自己作了序言。
其后,虽然他多次举办过画展,但先于画集行世的仍是《红叶》诗集和1974年的《王肇民诗草》。
直到1980年代,他的《画语拾零》、《王肇民水彩画选辑》、《王肇民素描集》等才相继出版。2000年,在他83岁高龄时,集选平生诗作,分1926—1942,1943—1944,1945—1948,1949—1965,1966—1989,1990—1998,六个时期及“补遗”共七卷合成《王肇民诗草》一书,以初版“渝序”和1974年版的“穗序”作该书之序,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当代诗词》主编李汝伦为之作“跋”。
此书为一窥王先生一生的诗心画路,探析其诗化的人品画品提供了最可靠的资料。同时也可见证先生的诗歌成就。
诗书兼擅或诗书画兼擅曾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特色。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优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人成长、成熟、树帜当世光耀后世的必备要素。书画“同源”,诗画也可说“一脉”。王肇民先生幼有家学渊源,随父读书县中,时变而能居家习诗,继之游学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最前沿之燕抗艺术殿堂,可以说他于家学、国学、西学以至无字之“人间世学”等皆得天独厚,6年的国难重庆孤旅亦教亦诗亦画的历练,加上数十年的教坛、艺坛的执鞭,边教边画边诗的饱学饱艺之陶冶,更兼其“或言人品即画品,品高笔墨始登仙”的德艺双馨的人生操守,才造就了他的人品和艺品的“伟大的风格”,才横空出世了他这位东方一流的水彩画大师!
王肇民的诗画情怀,从人品说,既有中国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入世济世思想,又有传统文人不曲奉营营、刚直不阿的正统血脉,更有现当代眼睛向下的大众情怀和时代担当。从诗品说,他既操有传统文人熟练有素的格律诗词和古风等素养并加以改造,又善于吸取民歌营养而创新诗歌形式。前所引“五个统一”之外,还应加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想和艺术表现的统一:
“勤把之无教小娃”(《孤女》)与“笔端磅礴吐虹霓”(《题画、写于合肥》)同出一笔;“逢人忙借问,何处有灾情”(《暴雨》)与“放怀天地小,知命任沉沦”(《放怀》)同源一怀;“骚人心性美人姿”(《落花王者》)与“志在鵾鹏敢傲物”(《鹰》)同为一身;“诗酒消愁愁未少”(《小别》)与“老作新郎常自笑”(《而今》)同为一人;“巴山夜雨惊残梦”(《寄长沙夏晨中国学》)“天安门上日初红”(《到北京》)同是一人所历;“红花布褂碧油头,缎子小袄绣石榴”(《竹枝词》)与“铁臂银锄争起落,青衫红袖汗如注”(《那莫妇女》)是其笔下两个时代的妇女美;“莫向今宵狂把酒,他乡于我只增愁”(《中秋》在重庆时)“诗成神鬼惊佳句,酒晕心肝是可人”乃两个时代的酒;“梦向黄梁枕里迷与几度梦魂来笑语”(《怀友人》)是两种社会的梦;“街头物价涨犹涨,腹内愁肠煎复煎”(《小女》1948年于南京)与“吾年非少壮,吾心似婴儿”(《长相思》写于20世纪80年代)乃一人愁乐两重天;“倘把满朝文武算,御胡飞将有阿谁”(《感时》1942年)与新四军“只杀得鬼子兵,魂亡魄散,口呆目瞪”(《读陈卓坤同志狱中诗草题后》)是面对外敌两表现……
王肇民先生的诗词令李汝伦“展读之中,爱不忍释,有‘后宫佳丽三千人’,而大多个个是太真之感”,“风骚振响,使人肝胆俱热”,“先生乃真诗人,纯诗人矣”。先生以“老杜之语意,陆子心怀”(李汝伦语)看待世界,亦以诗人之心手眼从教事画,遂使其丹青世界也便诗化了:“兴来握管如握帚,对客横扫明窗前。
丹青殡纷满纸飞,粉墨狼籍四座湔”(《答客问歌》)。“惟有真作能寿世,惟有志士能独妍。他日挥洒画坛上,气撼岭南万重山”。他底气十足便“艺气”十分自信,学不让今不让古,艺林今古始称尤”(《敢与》),“八十三龄南岳顶,群山下望尽丘陵”(《柬莫非同志》)。
王肇民先生“把中国画的用笔、素描的功底、油画的色彩和诗的境界融合在作品中,形成了他鲜明的艺术风格。”这是先生的老同学、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的评赞。真先生知已也。此境界是既具东方传统风格又有西土色彩、既能悦目又可赏心的艺术化境,诚可谓“可望不可即”。
由于他一生笃持“人品即画品”观点,故特始终注重高洁而“孤独”的人品修为,“立身应似铁,处世或如梅”(《得王景唐宗惟成书有感》)坚信“品高笔墨始登仙”(《答客问歌》)。他自言“诗画幸无才子气。心肝差有古人风。
爱顽不作权门客。守拙宁如田舍翁”(《自述》)。中国传统文人讲境界离不开一个“禅”字,王先生亦然。“半参诗画半参禅”(《一生》),“媚俗夸能吾不取,曲高自有知音听”(《观历代画展》),“放怀天地无恒物”(《晨》),如此“禅”境不是一般人所愿取、更难做到的。从此境界欣赏、解读先生的诗和画,方能窥其真貌,方能懂其真谛,方能赏其真艺术、高品位。
由于他“作个羊城一士民”(《九十岁作》)“由我门前罗鸟雀,任他座上满簪缨”(《柬莫非同志》),心志一直低调、平正,以“边画边诗自在身”(同上)之洒脱意态,才能在艺术之途上心无旁骛,踏实攀登,摘得艺术王冠。
同时,在坚守人品先于和重于画品的同时,先生并未丝毫放松画品的极致追求。从其百年展的百幅佳作来看,已经不单单是气撼岭南万重山了,也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初n那“巴黎的盛事”,而已经是中国“水彩画的昆仑”,是气撼世界的当今“融化中西”的中国水彩第一人。
漫写性情漫写意 凌云健笔欲生花
王肇民先生由于“边画边诗”(以至“边论”,从其较早辑录出版的《画语拾零》即可见所论所述各条,均有真知独到之卓见),所以其诗其画相互间如影随形,诗中可见画,画中可会诗。其水彩画面上虽不像国画那样题诗其上(也有不少题画诗),可显读诗情画意,然而当你感染到了他画面上溢出的那种“迫人眉睫的张力”后,特别是当你了解了先生的人品诗品之后便可明显地领会到他水彩画中蕴涵的诗意之美;同时,当你审读了先生的壮美画卷后再吟赏其经典性的诗词时,同样会更加领略其诗词中的人
性、人情和格调、韵致之真善美。
他的笔端特别饱蘸着浓浓的人情味。亲情温馨如“愁中爱看妻儿笑,世乱家贫倍觉亲”(《山居》);父亡后,“生前琐事谁犹记,老母喃喃话旧时”(《崖边》);夫妻恋情缱绻如“入肠酒化相思泪”(《之日寄衍芬》),“人从梦里相逢好”(《寄衍芬》)“字字伤心句句佳”(《答衍芬》)。
作者从别离妻女的第一、第二天至妻亡前后直接的寄、答、忆妻之诗计达16次30余首,苦恋伤别之意读之令人心肠寸断!舐犊之情如“惟喜娇憨两小女,已知寄语问平安”(《得家书》),“听声纵使非英物,足慰萱堂地下心”(《喜得子》)。
手足之情如“细看眼角眉梢处,多少辛愁在上边”(《弟肇东来广州》)。友情绵绵之歌诗较多,如对战场相识的抗日战友黄骏“相逢患难且相亲”(《送黄骏》)“自怜拜省未同群”(《送黄骏归者》);对老同学、老道友李可染“握手忽言欢,各称相见难”(《逢李可染》),“继踵齐黄机杼新,廿年前已作知人”(《柬李可染》),“生前未尽谈欢愿,死后常来梦里游”(《屡梦李可染》)。
与其他友人的交游、怀想、忆念之作不胜枚举,且情深意笃谊长。情牵家乡不仅赋诗家乡胜迹“皇藏峪”“圣泉寺”,而且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树都入了游子的诗囊。另如“照眼穿帘动客心,故乡遥忆正缤纷”(《见梅花》)“惊闻乡国讯,遥为岁年愁”(《闻家乡水灾》)。
情暖师生如事师“放翁心事杜陵泪,合与先生作若吟”(《题花植先生抗战杂咏诗后》);如待学生“莘莘学子尽相知……我似阿爷生似儿”(《故都杂忆》)。
“多情更作护花泥”(《落花》)更是一语成谶,使他成了“终身教授”。思右之情不仅神会屈杜陆苏、高启、八大等,还倾情扬雄、荆卿、昭君、项羽、石达开等。深沉浓烈的人民情如抗战期间于重庆,“弥天草木血腥重,失国人民涕泪多”,“中原父老空流泪,西望旌旗又一年”(《威时》);抗战胜利时“闻道东南破虏兵,长江万里可扬舲”;新中国成立,“红旗漫卷河山壮,白发飘迎燕雁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后,“总是英明先进事”(《会城晒后》),“兵精食足国更强”(《民歌二首》);“满村都是李双双”(《那莫如女》),“铁肩人尽是英豪”(《松涛水库车子队》);解放军战士“精忠更有健儿在,能把西夷一气吞”。
悼怀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陶铸等诗作饱含革命先驱、领袖的钦敬之情。
先生的情感倾注中,人情、物情、时情俱有,且皆真挚、热切、感人。并多有杰构佳句。吟咏对象除“以人为本”外,所涉范围广而具,具而细,迩而远,无物不可入诗画。
真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无论大自然的风花雪月、草木禽鸟,还是人间的生离死别、喜怒哀乐、无论是时代风云还是尺幅小景,随手拈来,遣上笔端。诗人集子中涉猎的有北国松柏杨柳、石榴杏桃,南国红豆木棉,芙蓉椰荔;有老骥鸱鸟、鱼鹰惊鸿,有子规鸣蝉、喜鹊蜻蜓……约略数来,直观的计有四五十种.
先生哀落花,爱梅花,“落花”诗达16首,且皆为七律。咏梅诗达17首,诗题如见折梅、画梅、读梅、看梅、古梅、梅花松枝歌、忆梅、庭梅等。曹雪芹苦思冥想借大观园才子才女不过写了咏菊12首。兹录其咏梅词《满庭芳.罗岗观梅》下半阙:
梅之清幽淡雅的情态、馨香及与诗人之怜香惜玉的雅兴浓情,相融相会,活脱脱一幅绝妙的“梅妻图”!
尤其令人拍案者二:一乃诗中涉“酒”涉“梦”者极多,二乃梦中咏诗醒后记续有多首。据说先生一生不烟不酒不茶,不棋不赌不搞收藏,业余只以吟诗作画为乐。真乃“最孤独者是神仙”(《七夕》)。中国传统文人中尤以李白诗酒和曹雪芹的红楼之梦脍炙人口。
王肇民先生的诗酒、诗梦之才别有天地。“酒”字成了先生加浓诗意的“佐料”。“酒”句多达六、七十个,“梦”句更多达90多个。“酒”句趣者如“欲写真容嫌老丑,却吞美酒作仙丹”,“图成人尽夸风彩,一笑那知是醉颜”(《题自画像》)。
“梦”中吟诗妙者如:“信步闲庭月正高,心头不锁暗来潮。何人夜中吹横笛,幻作云间弄玉箫”(《在莺歌海梦画美人,并题诗其上,醒而记之》)。勘称梦美、人美、画美、诗美之四绝也!诗画之执着痴迷者,古今谁曾至此境界?
先生画名掩诗名,由上文可略窥其诗才之貌大概。然其画论较其诗才来可以相颉颃,“诗情每逐画情去,画论常从诗论来”(诗话)。本文不就其画论述评,只撷其诗词中涉论鲜明者。“如何笔底无音韵?万卷书曾读也不”(《学画》);“诗中有画诗方妙,画可兼诗画愈工”(《诗画》)。
尤其是《答客问歌》(古风体,48句)和《读艺术杂志》(七律)两首,不仅可见先生鲜明的艺术思想,更可见其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又疾恶如仇的凛然气概。
前诗针对为何不开画展、不投稿之“客问”,答曰:“习作只合自家看”,“囊中买米尚有钱”,“男儿立身先立志,尺幅片纸有尊严。固穷何能投其好,守道宁肯谓我顽”,“功在人民自千古,鬼神喜怒何足患”。后诗短些,不妨全录:
先生这里的“齐黄”系指齐白石黄宾虹。无须笔者多言,其思其想、其肝其胆、其操其守、其指其斥、其忧其痛以及其嘲其侃,其气其颜,真是凛然不可犯!是何等痛快淋漓、俨然耸然而又奇趣盎然!活脱脱一个不倚不邪,不为名累,不受利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文坛夫子、艺界大丈夫也!联想当今汹汹金钱大潮,“道德滑坡”之域,不更可见先生之“出淤泥而不染”、搏击风霜雪雨的高风亮节、良心傲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