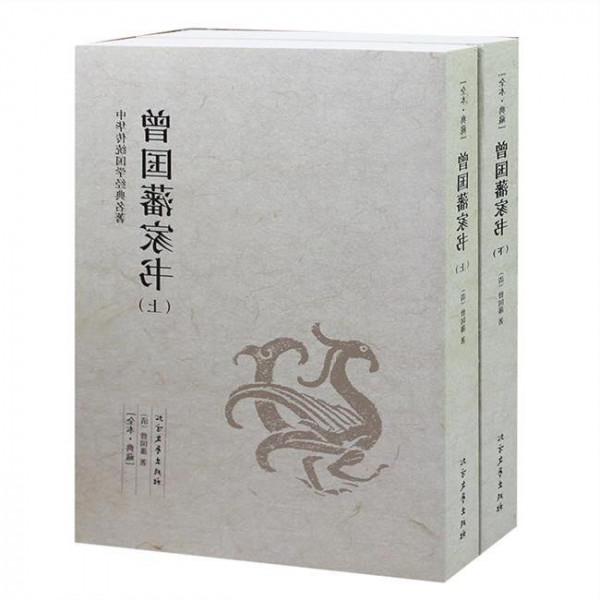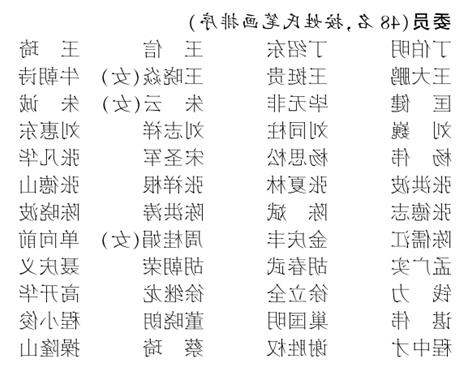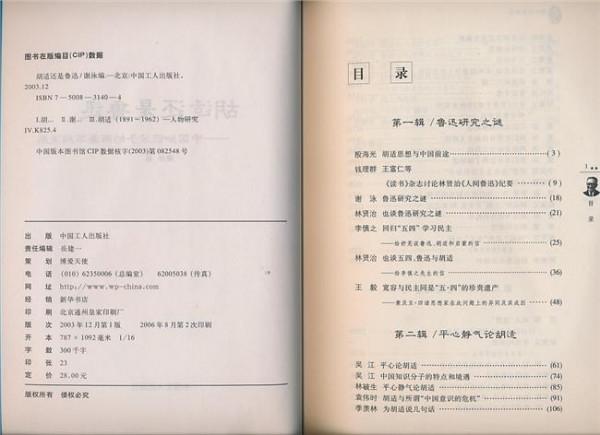出版家王匡 王匡(新闻出版界人士)
王匡(1917-2003),广东东莞人,从少年时起,就参加爱国进步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20岁的他,立即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其后又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
王匡人物经历编辑
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40年代,任中共中央研究院哲学研究员。抗战后期,他随同部队到中原解放区,历任江汉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科长、部长。
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往中共南京办事处任秘书,兼任南京新华分社采访主任。解放战争期间,他到太行山解放区任新华社临时总社国内部副主任,并参加刘邓大军前线记者团,随军挺进中原,进军江汉。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是新华社的四大著名记者之一。
1949年夏、秋间,他跟随叶剑英同志南下,随军解放广东后,担任叶剑英为首的广州军管会的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副处长(后任处长),领导对国民党报纸的接管工作,同时担任新华通讯社华南总分社第一任社长。为了创办南方日报,他在南下途中,就与曾彦修、曾艾荻、徐峰等同志一起准备南方日报创刊头三天的大量稿件,从而使得南方日报得在广州解放之初的1949年10月23日顺利出版。
1952年8月,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并兼任南方日报的第三任社长。直到1955年1月,他升任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同年7月,华南分局撤销,改设广东省委后,他仍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之后,又升任省委候补书记,分管宣传工作。在1957年,他奉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省委之命,主管筹备创办羊城晚报的工作。后来他被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委员、宣传部长后,仍一直关心羊城晚报的工作,特别是当羊城晚报转由中南局直接领导后,他经常指导羊城晚报的办报事宜。
“文革”期间,他成了广东省最早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倍受长达十年的迫害。粉碎“四人碎”后,1977年,他得到“解放”,复出到中央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之后又被调任香港,担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回京后又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离休后,他仍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和党的思想宣传、新闻出版工作,晚年长期患病,终年87岁。
1957年初,当时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提出广东应办一份晚报,作为省委机关报的兄弟报。王匡同志对此表示赞同,还把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曾任中央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同志说过的“各家报纸面孔雷同,这是新闻界的耻辱”的话转告了陶铸。
于是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决定把创办羊城晚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晚报)的任务交给省委宣传部,并由王匡同志主持领导此事。之后,在王匡同志统一领导下,由南方日报派人成立筹备工作组。
应该说,羊城晚报的得以创办,首先应归功于陶铸和王匡同志。1966年“文革”开始后,早已交由中南局直接领导的羊城晚报,被广州的“造反派”强行封闭。王匡当时之所以成为要被打倒的“走资派”,其中有两条重要“罪名”,就是他参加创办和经常“遥控”《羊城晚报》以及重用、包庇秦牧、红线女等著名的“资产阶级文化界人士”。
记得在他于1977年被“解放”,从拘留所回到广州后,他曾对我谈起,他因与《羊城晚报》有关而大受批判的经过。
在那次谈话中,他还开玩笑说:“当年看文稿,我常修改,累得我闻得臭气阵阵!”原来他指的是过去大家写字都使用毛笔,而且用的是质量很差的墨汁,写起字来晾干了,纸上仍然不免存有一股臭味。
从他这番话中,却可见他对文稿是怎样认真和严格修改的。他还回忆起,当年为了准备纪念广州起义30周年,省委决定由宣传部写一本正确反映广州起义经过、意义及其经验教训的名为《广州起义》的书的经过。“文革”后,羊城晚报复刊,我到了晚报工作。
80年代初,我和路平同志曾被当时已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的王匡的提名,经省委派遣,上京参加对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遗作的文选的编辑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前往王匡的寓所拜访,他也喜欢与我谈论他在广东工作时的往事。
他认为,编辑那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文选时,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当年这位领导同志在世时的事迹应“一分为二”地看,对他的遗作也应“一分为二”地挑选。公开、正式出版文选时,应选用那些经得起历史考验,对当前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仍然适应的讲话、文章,至于那些曾受错误路线影响,带有严重“左”的色彩的内容就不要选用了。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广大读者有利。至于要对一些人的生平、功过进行全面评价,那就要根据和参考各种材料,这另当别论。
羊城晚报复刊后,王匡虽已不在广东工作,但每当他从北京、香港回粤时,他都很关心羊城晚报的发展。1992年,他正式回到广州休养。他在羊城晚报创刊35周年纪念时,与曾任省委宣传部长的陈越平同志一起莅临羊城晚报社,畅谈晚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得报社的同志们大受启发。
1992年4月26日,王匡同志到白云山移葬与他同命运、共奋斗一生的战友、爱侣田蔚同志的骨灰于山麓,植以相思之树。并作“种树归来”一诗,充满了真情实感。田蔚同志是我党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时的最早几位广播员之一。
广东解放后,曾先后担任广东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副台长、台长,离休前还担任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省广播电视局局长,对广东广播电视事业曾经作出重要贡献。田蔚同志逝世后,王匡同志大为悲痛,后来王匡长期患病,恐怕与他对其妻子的深切怀念不无关系。
1993年,王匡同志经亲友们的多番劝告,才决定出版他的《长明斋诗文选录》一书,这实际是他多年作品的自我选集,于1994年正式出版。从书中的诗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著作中的若干精华,使读者看后得益不浅。在该书中,收集有多篇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这些都是当年他向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的工作人员所作的专门讲话,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王匡寻觅足音编辑
南方日报:白手起家创办的产业
王匡是南方日报社的第三任社长,为这份报纸的发展也是倾尽心血。带着对王匡的敬意,记者重新走访了南方日报社以往的办公地址,希望从这些旧址中,一窥这位老领导当年的工作痕迹。
《南方日报》创刊时的地址,是1949年10月20日接管的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址。这座破旧、狭窄的四层楼房,坐落在广州光复中路(后改名为光明中路)48号。1950年5月1日,军管会增拨了沙面复兴路42号前万国宝通银行旧址给报社,作办公和排字之用(印报仍在光复中路48号)。1953年,斥资100万元,在西堤新基路37号建了一幢新楼,同时在西堤二马路新建了印刷厂,这才开始有自己的产业。
印刷设备也是从无到有逐步添置的。创办时,接管了国民党《中央日报》未及撤走的3台对开活版铅印机和一台抗战胜利后便没有使用的旧低速轮转机。印刷工人发扬了当家做主精神,迅速修复好这台轮转机和另一台接收《前锋日报》的低速轮转机。这两台“老爷机”便担负了1952年前的报纸印刷任务。
据报社的老同志介绍,在这之前,经过朱德总司令批准,于1950年用党费从香港购进原天津《大公报》一台美国司高脱铅印轮转机(理论时速24万份)。这台轮转机于1951年运抵广州时,由于美帝国主义封锁,不给安装图纸,使安装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后来,在广州重型机器厂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把机器安装起来,于1952年胜利试机投产,成为当时远东地区印报能力最强、印刷机时速最高的印刷厂。
电话通信设备初期只有接管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一台20门电话总机,1954年更新了一台上海产的50门总机。这个时期的交通工具也较少。只有旧的福特、霍素小房车各一辆,美制威利士吉普车一辆,大货车只有两辆,一辆为斯蒂蓓克旧车,另一辆是由大客车改为货车的道奇T118.记者外出采访,往往要靠步行。
王匡家乡情怀编辑
两万多册藏书捐赠给东莞图书馆
身为东莞人的王匡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王匡生前最喜欢买书,在晚年,他把自己毕生最珍贵的东西留给家乡,他把在“文革”中被抄家以后又发还给他的两万多册藏书捐赠给东莞图书馆,在图书馆专设“王匡书室”,为其珍藏展览,以育后人。
王匡书室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著作、读书笔记、名人赠书,第二部分是珍藏图书,第三部分是珍藏的画册。赠书中有珍藏的图书:《上海博物馆藏画》、《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
珍藏的画册:《广东省名画家选》、《广东书院画集》、《关山月画集》、《徐悲鸿油画》、《李铁夫》、《潮汕国画家选集》、《明清广东书法》、《张大千画集》、《邓白画集》、《关山月旅美写后画集》、《美国名画原作展》、《潘天寿作品集》等。
建国后王匡多次回莞。建国初期,东莞的可园曾做过敬老院、幼儿园、小学之用。1959年,王匡提出重修可园的设想。1965年在陶铸的关怀下,由当时的东莞县委林若直接领导修复可园。
王匡钩沉辑轶编辑
曾被毛泽东单独召见
王匡毕生曾见过毛泽东两次,一次是王匡二十岁在延安抗大做红军老师的时候,毛泽东和他们几个教员谈如何教好文化课的问题。另一次就是在1958年,毛泽东在广州珠岛宾馆单独召见王匡。王匡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才二十岁,到第二次见毛泽东时,已经四十岁,估计毛泽东也忘记了在二十年前,在延安曾接见过这位红军教员。
1958年被毛泽东召见的时候,王匡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那次相当的意外,王匡没有任何的准备,他和女儿正在家里吃午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他立即到珠岛宾馆去,说北京来的客人要见他。
王匡问是谁,对方说你来了就知道。没想到这位客人竟然是毛主席。王匡的习惯是将黑布鞋后跟踩在脚下,当拖鞋穿,他一见到毛主席当即狼狈万分,第一时间蹲下去将鞋后跟提上来。谁知毛主席对他说:“王匡同志,就这样吧”。
那次毛泽东单独见他,但并没有吩咐特别的任务,也没作出工作安排,只是问他过往的经历,问他有没有读过马寅初和凯恩斯的书。王匡回来后也不太明白毛泽东的意图,但估计是毛泽东想对负责宣传工作的人才进行了解,量度他的工作能力,是否一个可用之才。
王匡冲破阻力重版35部名著编辑
“文革”后,王匡任国家出版局局长时,作出重新出版35部名著的决策,而且还用了印毛选的纸张。
这个决策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十分艰难而冒险的事情,如果当时政治形势再有变动的话,这两条都是“死罪”来的,但王匡就是这样,完全豁出去了,不会因为受到“文革”的迫害,而改变自己的追求,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始终恪守自己的信念和真理选择,这也是儿女最敬佩父亲的地方。
重印这批书籍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究竟哪些书可以重印,哪些书不能重印呢?由谁来界定?标准是什么?真叫人疑虑重重,迈不开步子。想来想去,王匡就先从马克思肯定过的书、列宁肯定过的书、毛泽东肯定过的书入手,后来确定了35部中外名著。
其次的难题就是缺乏纸张。“文革”期间因为长期不出书,仓库里根本没有储存的纸张,加上纸厂全部停工,仅存在仓库的8万吨纸全部是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第七卷的。王匡想,在当时的形势下,出版“毛选”第六卷、第七卷似乎不大可能,因为“毛选”第六卷、第七卷会涉及到“反右”斗争、三面红旗、庐山会议等问题的评价,这些问题中央都还没有做结论,为此,王匡专门为这件事去找吴冷西、胡乔木商量。
吴冷西笑笑不回答,胡乔木则说:“‘毛选’四卷编了好多年才出版,第五卷编得很不容易,第六卷真不敢说什么时候能编出来。
”虽然是这么说,可这些纸是专门为出版“毛选”第六卷、第七卷准备的,谁敢动用“毛选”的纸呢?“毛选”印不出来岂不是要你负责吗?这个罪名可不小。于是王匡连夜进中南海,请示了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吴德,得到了他的支持,才从汪东兴那里拿到了纸,书终于顺利地开印了。
这批书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新华书店发行。售书的第一天,对广大读者来说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人们通宵排队等候书店开门。书店里人头涌涌,摩肩接踵,新华书店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买到书的人满头大汗,如获至宝地捧着一尺来高的一大叠书从人群中挤出来,心满意足地走出店门,口里说要留给儿子看、留给女儿看。
对这批中外名著的出版,社会上有口皆碑,普遍赞扬。这批书出版后,很大程度缓解了书荒,初步满足了广大读者对书籍如饥似渴的需求,给出版界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