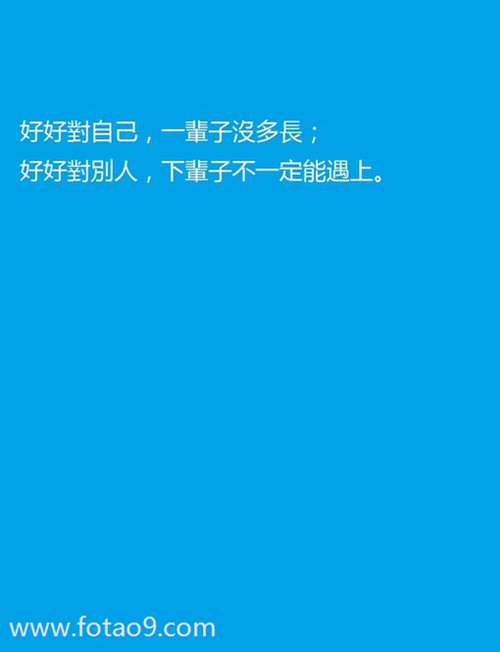余浩的书籍 蒋余浩:地方决策的终极目的应是对公众有益
近日,有报道说,成都有关方面将出资500多万元,对杜甫草堂博物馆内的4座厕所进行改造,全部按照五星级标准打造。这令人想起不久前北京市的举动,其对公厕的管理上最受热议的是“公厕保洁卫生控制指标表”中的“苍蝇(只)≤2”一项。
坦率而言,此类极为严格详尽却又颇易流于形式的制度规定,在我们生活中从来就不少见。比如说,公司的财务制度会严格规定不同行政级别单次开支的金额总数,但从来就不去防范公司高管分拆开支;公务员队伍不断严格收支两条线的管理规定,但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对待行政机构经营牟利性事业而导致小金库屡禁不止;在科研学术机构里,目前在大力借鉴和推广“先进发达”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目的很明确,是要保证科研经费用于科研,而不是落入研究人员口袋,但各种原因使然,一些科研人员想尽办法私分经费的现象根本无法杜绝,假发票、假开销、假项目横飞,严格制度规定之下满是斯文扫地的尴尬。
总之,纸面上的规定越来越详细,留给被管理者的腾挪空间却依然十分巨大,我国法学界有人批评那种一味主张“程序正义”的意见是替“繁文缛节”张目,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如何分析这种现象?费孝通先生以前在《乡土中国》里已经说过,旧的习俗规范被冲刷,新的制度安排又与乡土实际不符,于是就造成了“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严格规定通常是与被管理者没有直接交往机会的层次制定,制定时不妨尽量往科学化、标准化、细则化的方向走,一旦这种制度“表达”落到实践层面时,被管理者直面的多样性环境就立即起抗拒作用了。要使制度规定全面生效,就必须彻头彻尾改变被管理者的行为方式,然而这种改变所需的成本非常庞大。于是我们看到,许多甚至能够产生良好效果的规定同样必须依赖领导的专门批示才能落实。
需要改变的正是对制度作用的认识。2009年底,中信出版社推出经济学家理查德·H.泰勒和法学家凯斯·桑斯坦合著《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中译。两位美国学者在这本著作中推荐了一个“自由主义家长”的制度理念:制度应当激励人们从事自由选择。
在他们看来,制度不是规定人们的选择范围或者方式,而是激励人们选择好的东西,例如不用去禁止人们消费垃圾食品,而只需要把好的食品放在他们容易留意的地方,就能收到正面效果。
与此同时,“自由”也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自由必须是在容许充分观察、充分了解的前提下作出的选择。因此,制度作用不在于“制止”而在于“激励”:帮助人们克服偏见,更有效地选择好的,放弃坏的。
自由至上主义者当然会怀疑这种制度理念蕴含的治理理论。但是,只要我们承认,现代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依赖各种各样专门性知识和专家,就不能否定这种弱性治理理论的存在价值。需要抵制的是那种从“严格管理”的角度出发看待制度规定,给与基层工作者适当的激励、相对宽松的环境、足够的重视和尊重,远比为他们加置行为准则更能促进工作的改善。
在《无缝隙政府》一书中,行政管理专家林登讲授了大量的实例,例如美国凤凰城警察局,在面对一个事件时,警局官员们只需要回答如下的问题:这件事情对整个社区有没有好处?处理这个事件对警察局有没有好处?这件事在社会道德上是否会被容许?你愿意为此承担相应责任吗?
如果所有的答案都是“肯定”,则马上能够形成“去做吧”的工作指示,而不需要专门进行请示。这样的政策指南鼓励工作人员自己去思考,只要行为结果的确是对相关公众有益,就允许以富有个性、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投入公共服务工作,而无须严格得令人发笑的制度规定进行督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