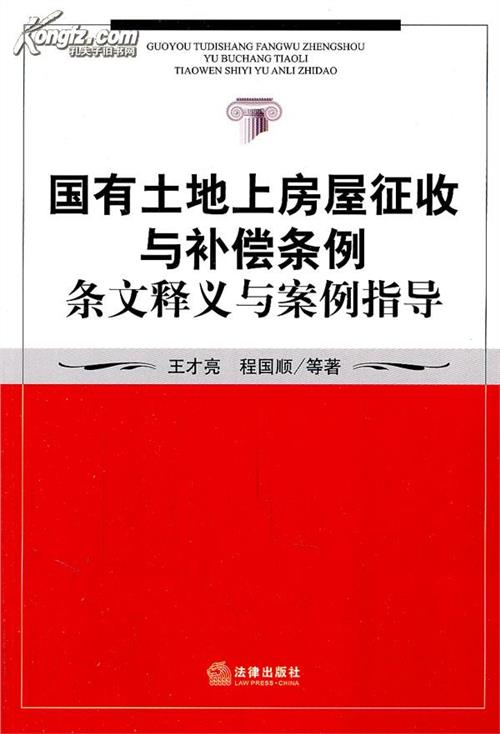海耶斯美洲 克里斯·海耶斯:美国土地上的殖民地是如何形成的
从印度到越南再到加勒比地区国家,殖民者一直在引导被殖民者进入权力部门,而与此同时殖民者们仍然对殖民地人民保持着高度的支配地位。导致巴尔的摩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死亡的警察中有半数都是黑人,当地警察局局长是黑人,甚至该市的市长也是黑人。那么弗雷迪·格雷这位黑人青年为何会死在一个权力阶层中黑人占多数的城市呢?
这就是美国当下的种族等级现实,虽然我们早已经选出了一位黑人总统。黑人可以在这个国家里生活,他们甚至可以出人头地,但他们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与白人完全平等的公民。针对黑人的下作手段从不缺乏,即使是一位在哈佛大学做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的著名黑人学者,他也可能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体面的住宅里被突然戴上手铐,原因仅仅是有人怀疑他偷了别人的东西。
在美国,种族在公民社会(Nation)与殖民地(Colony)两者之间划下了清晰的界限,但“种族”这个概念并非总是那么清晰、稳定。纯粹意义上的白种人并不存在,但一个“白人”天生可以坐享大量利益;“黑人”是一个人为制造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却实实在在可以杀人。
在一本名为《种族问题的操作技巧》(Racecraft)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从语言学或语义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美国社会中不平等现象根源的那个幽灵,为了欺压少数族裔创造出了很多以词汇为外衣的概念,似乎那些词汇所描述的东西是早已存在的,而这在明眼人看来不过是应用语言学的把戏。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被创造出来的词汇也在经历演变,但它们仍然可以反映白人当权者和被压迫黑人之间的畸形关系”。
关于美国种族范畴的词汇,其内涵一直在变动中,甚至词汇本身在大众应用领域也时而流行时而消失。与此同时,公民社会与建立在其内部的殖民地之间的界限也有些模糊不清。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分属于这两者的两个族群往往毗邻而居,似乎有一道看不见的墙把两者分开,往往只有当地人才能分清哪个区域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这就像英国著名奇幻小说家柴纳·米耶维(China Miéville)的作品《城与城》(The City&the City)中的那两座虚构城市Beszel和Ul Qoma一样。在这部小说中,虽然两座城市建立在同一片土地上,但它们各自的市民却故意无视另一座城市的存在。
以弗格森小镇为例,遇害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所居住的小区在当地白人市长詹姆斯·诺勒斯(James Knowles)口中就是一个“问题小区”,也就是所谓的“殖民地”(Colony)。而这位市长枪击案发生时正在两公里外的农贸市场购物,那里却是美国法治昌明的公民社会(Nation)。另外,巴尔的摩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死亡的地方位于市区西部,那里也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
这就是《民权法案》留给我们的遗产,种族歧视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好邻居”和“坏邻居”、“好学校”和“坏学校”、“市中心”和“睡城”……形形色色的分别之心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其实已经接受了种族隔离的现实。这一切并非偶然,是历年政策积累的结果。联邦政府的住房指导方针、地方房地产中介的销售取向以及各种中小学校董事会、市议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决议……所有这些都在将公民社会和殖民地区分开来。
在殖民地区域里,警方引发的暴力事件时常发生,如果你不愿屈服,死亡发生的概率并不低:桑德拉·布兰德,28岁,黑人女性,她最近死于德克萨斯州一所监狱,被捕原因是驾车变线时未打转向灯;沃尔特·斯科特,50岁,黑人男性,他遭到一名北查尔斯顿警察的枪击,背部中弹,当场死亡,原因是刹车时刹车灯发生故障未能正常开启;本文前面提到的巴尔的摩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的死更加离奇,他在与一名警察发生目光接触后继续前行,随即遭到拘捕并被殴打致死。
如果你住在公民社会,司法体系就像你电脑里的操作系统,它默默在那里运转,为你的工作生活提供最好的环境;如果你住在殖民地,那司法体系看起来似乎成了某种电脑病毒,它不时侵入你的系统,打扰你的正常生活,而且这病毒所做的一切都名正言顺,甚至被人们当作一种常态。
在公民社会,有法制;在殖民地,有秩序就不错了。在公民社会,老百姓因警察保护自己而安心;在殖民地,老百姓为避免发生意外躲着警察。在公民社会,国家给你权利;在殖民地,警察给你命令。在公民社会,在被证明有罪前你是无罪的;在殖民地,你生来就是有罪的。
警察群体被要求区别对待上述两个区域的居民,他们甚至可以凭本能采取相应的不同行动。一位巴尔的摩警察局长曾这样对他的下属训话:“不要对那些罪犯采取对普通公民一样的态度”。
在公民社会,你可以放心地在一条没有任何车辆的、极为安静的马路上散步。我在弗格森小镇就曾与镇长先生在这样的马路上同行,当时那条马路铺满了落叶,四周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绝大多数都是白人居民,你见不到一个警察的身影。
其实当时我们是违反了交通规则的,因为我们走在马路的正中央,并没有靠边,可谁会在乎呢?我相信,即使附近有执法的警察看见,他也不会过来打扰我们。但是,在几百米外的黑人聚居区,殖民地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直觉告诉我,如果一个黑人在那一带的马路中央散步,他很可能会触发一系列事件,甚至可能在这个国家的执法者手里丢掉性命。
殖民地里大多是黑人等有色人种,但金融海啸余波未平,随着去工业化和工资增长停滞,正有越来越多的白人劳工坠入原来只属于黑人的殖民地深渊。如果把美国监狱里的黑人和拉美裔罪犯全部被释放,美国仍将是全世界服刑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因为美国白人罪犯的人数实在过于庞大。
而且这些白人罪犯中有很大比例都学历偏低、收入不高。据2008年的调查结果,在20岁到34岁这个年龄段内,高中辍学的白人中有15%在监狱服刑。而大学毕业生这个比例还不到1%。
这意味着将殖民地与公民社会区分得太清楚会有一定风险:“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理是要不得的。那些被强塞给殖民地的专横和暴力有朝一日会反过来将公民社会也也拖下水。美国警察的确枪杀了太多黑人,但倒在他们枪口下的白人也在与日俱增。
我相信,在当今的美国,即使公民社会中最有同情心的居民也会认为那些殖民地发生的惨剧与己无关。他们会说,“的确,美国监狱已经人满为患;的确,警察滥杀无辜黑人太可恶;的确,这一切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是,这一切跟我自己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3月6日美国《名利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