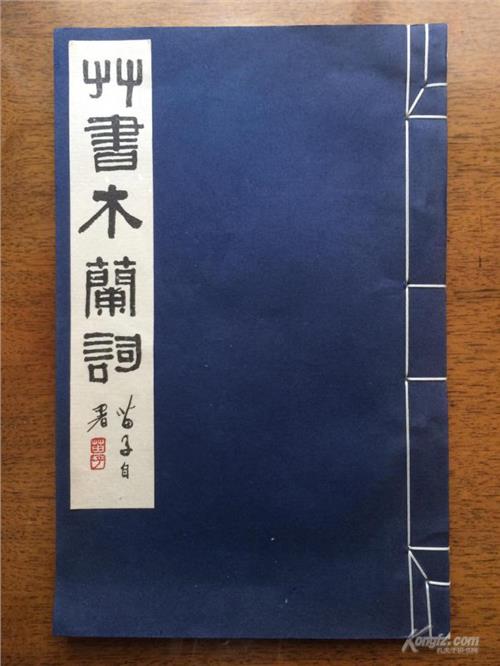章诒和的丈夫 章诒和:散发坚硬的冷气
严格来说,一个人极尽一生都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旁人试图破译其文字的密码、解锁其灵魂的门禁,以鉴别真相认知全貌,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要说每一部著述之于作者,正像支流与河床、枝条与根系,就是每一个细碎文字的组合构成,准确而极限地传达了灵魂,灵魂这东西也如空气般瞬息万变,扑朔迷离,复杂多义。因此所有的读者与作者之间,都存在误会。即使瞬间地离近,也将永久地隔远。
所谓见仁见智,只是误会的另一套说辞。
也许是误会罢,在我看来,《刘氏女》正是章诒和心口上的一道骇人的疤痕。她1960年考进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文系,1963年被下放。“文革”间因在日记中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惹下大祸,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有期徒刑20年。
1979年被无罪释放。她说,“我在监狱近十年,和女犯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26岁到36岁,比某些夫妻的婚龄长,比很多小两口还亲。那里外表平静如镜,其实终日翻江倒海!”《刘氏女》正是十年牢狱生活系列小说之一。刘氏女,就是指她的同牢女犯刘月影。
故事从中队长指派刘月影杀猪、章做助手开始。让刘月影干这件事,可谓知人善任,意味深长。这是章后来慢慢知道的。刘月影经历了一场令人绝望的婚姻。“他在,我没法活;除非他死,我才能活。”于是这个女人筹划了一场镇静的谋杀――用半年时间,存储了足量的花椒,在一个安静的冬夜,一如往常地进行了一次熟练的屠宰,只不过这一次屠宰的是她丈夫。
然后肢解,像处理猪肉一样涂抹上油料和盐,放进腌肉的坛子。人在无声中一点点疯狂。要说这小说的惊世之笔是在后来:小儿子在大姑来家吃饭时,忽然热情喊道:那腌的爸爸的肉,该吃了吧?惊煞!
现实真是比任何想象力都富于想象。《刘氏女》所做的就是将文字精简成锐利的刀片,冷、生猛、凌厉地划下来。
章是怎样与这些女犯相处10年的?她们人人美艳,个个凶残。她在人生最丰沛的年华,见证了最残酷的梦魇。一个人心里疼痛的地方是不轻易示人的,它留下的印迹会像毒素一样缓缓地释放在小说里,每一个情节都是心灵开放的瞬间。
她需要面对饥饿。“胃器官本是个柔软的袋子,一旦没了食物,它就变成两片粗粝的砂纸,互相摩擦,狠狠且无休止。人渐渐心慌无力感觉快要断气,恨不得有人过来一把掐死自己,不是为了结束生命,而是为了结束饥饿”。
她需要维护尊严。“女犯们每天收工后,赶紧到伙房排队,为的是打到半盆热水。因为洗脸、擦身、洗脚、洗屁股,全靠这半盆水。犯人端着水盆,把脱下的衣服挂在篱笆墙上,双腿蹲下,用三根手指一点点往身上撩水。就是洗澡了。”“最常见的景观,是你的口鼻正对着别人的屁股。前面的人起身,一不小心,就会把旁边人的脸盆拱翻。那人跟你拼命,即使脱光衣服,也追着打。”
她需要排解孤独。“监规里的强制性沉默与间离,使我一下子深刻认识到人的互相依存性。如果用强制手段消灭这种依存性,任何一个人都会陷入深深的痛苦……”
在最黑暗的黑暗里,她们攀比着邪恶。“人进了监狱,都没有良心”。她们相互批判相互揭发,脏话满天相互侮辱;她们瓜分死人的遗物,几个鸡蛋、一块破布,裤子和鞋之类的意外收获,成为她们快乐的来源。
那些往事对她来说确实无法如烟,她的伤口在岁月里慢慢结痂。
她必须把多年以前所吞咽的一整块痛苦化作腐水流淌出来,否则她剩下的除了仇恨还是仇恨,并且还会发酵变异。毕竟,女犯们在时间的洪流中一个个消散,而她还活着,可以倾吐,可以幽怨,可以控诉――她能一次吐干净吗?
她带着刚烈、不驯服、冷和硬,如嶙峋怪石,在新旧年代交接的不平滑处,散发着一股坚硬的冷气。
单就写作而言,以我等的理解,长篇就像婚姻,开始时是冲动,到后来靠的就是意志和信念,还有惯性;中篇是最完整最充沛的一场恋爱,该施展的施展,该放纵的放纵,该收敛的收敛,启承转合,全须全尾;短篇就是一次短暂出轨,需要悬念,猜谜式的探究与推进,还有吸引眼球的炫技。《刘氏女》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中篇。
如果说张柏芝谢霆锋两口子是用生命在演戏,那章诒和她老人家就是用生命在写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