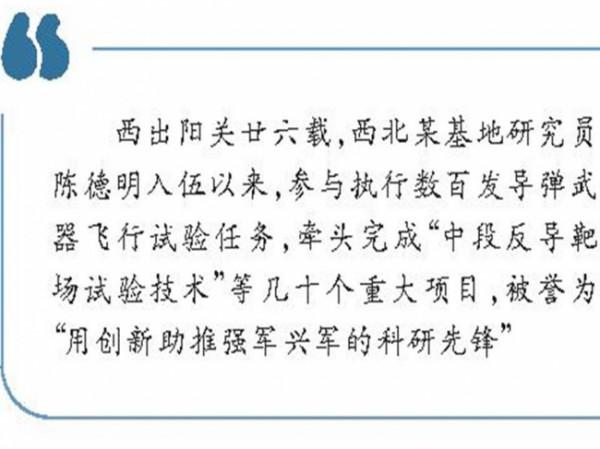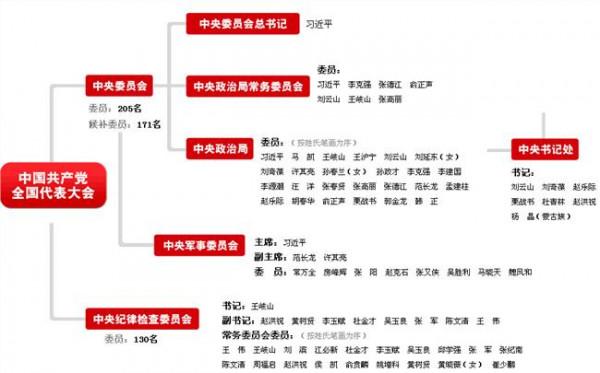章太炎齐物论释 陈少明:排遣名相之后——章太炎《齐物论释》研究
章太炎作《齐物论释》的主要思想资源,明显是道家与佛学。这种思想选择,既与个人学养的性质直接相关,又与近代以来的思想学术大势大有因缘。太炎对道家的热衷,同对整个子学的兴趣有关。子学在清代的复兴,本是由清学以汉反宋的倾向,发展出以考据为特色的学问带动出来的。
但太炎思想也不为清学所限,他对清儒只识考据不通玄理,也不以为然。其以认识论与因明的视角研究先秦名学的开创性,为学术史所公认。《齐物论释》则堪称体现太炎治子风格的学术经典。
子学是学术史的,佛学则是思想史的。梁启超认为:“晚清所谓新学家,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它可追溯到鸦片战争期间的龚自珍、魏源,“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荐,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包括康有为及其弟子,如梁本人。
(梁启超,1988年)然清代学者论佛有两类,必须区分。一是逃佛者,一是用佛者。逃佛者源于对社会、人生的失望悲观,而油然有出世倾向。而用佛者则思以佛学为思想武器,同混浊的世界抗争,是入世的。晚年才信佛的龚、魏属前者,而康党系后者:“若康南海,若谭浏阳,皆有得于佛学之人也。
两先生之哲学固未尝不戛戛独造,渊渊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撼宇宙,唤起全社会之风潮,则不恃哲学,而仍恃宗教思想之为之也。”(梁启超,1984年,第139页)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谈章太炎与佛学关系只寥寥数语:“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
”其实,在以出世精神鼓动入世事业方面,太炎也未遑多让。下面这段常被引述的演说词非常说明问题: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
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任公说太炎“好‘法相宗’”虽太简略,但也道出章氏佛学重分析重理智的思想特征。在太炎看来,法相一术,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不但与清代朴学学术风格一致,甚至也与西方近世科学精神趋同。
《齐物论释》最显著的述理方式就是名相分析:“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自非涤除名相,其孰能与于此。”(《齐物论释》,见《章太炎全集》第6卷)这也导致太炎借庄学讲经世的理想,淹没在另一种玄谈之中。
不要以为章氏古色古香的观念是思想闭塞的表现,《齐物论释》提及的西学知识,包括逻辑思想方面,均非常准确。可见其以佛释庄,不是眼界的局限,而是自觉的选择。《齐物论释》对西学引述虽然不多,但西学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即作为章氏陈述自己思想的一个潜在的参考系而起作用。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近代思想家能忽视西学的存在。
了解太炎正面运用的思想资源后,还得补充一点,他所摒弃的流行观念就是理学、今文经学,或许还有西学中的功利主义。这对深入理解《齐物论释》也很有帮助。
二、以佛释庄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说:“少虽好周秦诸子,于老庄未得统要。最后日读《齐物论》,知多与法相相涉,而郭象、成玄英诸家悉含胡虚冗之言也。既为《齐物论释》,使庄生五千言字字可解”,“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
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齐物论释》序云:“(庄子)纲维所寄,其唯《逍遥》、《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一部《齐物论释》其实就是以法相宗的手法,对这一“对子”的思想演绎。下面择要观察太炎如何从《齐物论》“丧我”、“天籁”及“成心”诸说中,解读他心目中的“平等”理想。
《齐物论》开篇是一则关于“丧我”的对话体的寓言。南郭子綦用“吾丧我”来概括他那“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精神状态后,接着就以“人籁”、“地籁”、“天籁”的不同,喻某种对世界或人生的观点。最后的对话是:“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
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注疏史上,对这则寓言的解读也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最有深度的对比,则是郭象与王夫之的理解。
郭象看到的是“物”,强调事物的自然本性;王夫之听到的是“论”,体味的是以不齐为齐。这与两人对《齐物论》题解的不同相关,郭象是“齐物”论,而船山则是齐“物论”。太炎偏向郭象,却别出心裁,引入法相宗的观点:《齐物》本以观察名相,会之一心。
名相所依,则人我法我为其大地,是故先说丧我,尔后名相可空……云何我可自丧,故说地籁天籁明之。地籁则能吹所吹有别,天籁则能吹所吹不殊,斯其喻旨,地籁中风喻不觉念动,万窍怒号,各不相似,喻相名分别各异,乃至游尘野马,各有殊形腾跃而起。
天籁中吹万者,喻藏识,万喻藏识中一切种子,晚世或名原形观念。非独笼罩名言,亦是相之本质,故曰吹万不同。使其自己者,谓依止藏识,乃有意根自执藏识而我之也。
(《齐物论释改定本》,见《章太炎全集》第6卷,第65页)名为概念,相系情状,依佛家,人对概念及事物的执着,根于对“我”的执着。没有“我”的存在,名无从起,相无从现,名相便可“空”掉。故“丧我”便是对名相釜底抽薪之举。
“我”如何“丧”?途径是改变“念”。“我”与名相的关系,是能与所,即主与客的关系。在认识中,没有能就没有所,但同时没有所也就没有能。一切能、所起于念,而念背后是“藏识”,“藏识”才是万有的总根源,叫做“种子”或“原型观念”。
故对“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的解答,郭象是没有支配者,太炎则是有,是“藏识”。法相分“八识”说明人的精神世界,第八识阿赖耶识,也即藏识,为万有的总根源。
依章太炎,《齐物论》中的“真宰”也是藏识的另一说法。虽然人(每个“我”)也是藏识的产物,但藏识得通过人的精神世界才能变现万物。因此,强调藏识,依然是着重人的主观性。
故“成心”也是藏识中的种子:成心即是种子。种子者,心之碍相,一切障碍即究竟觉,故转此成心则成智,顺此成心则解纷。成心之为物也,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未动,潜处藏识意根之中,六识既动,应时显现,不待告教,所谓随其成心而师之也。(同上,第74页)
是云非云,不由天降,非自地作,此皆生于人心。心未生时,而云是非素定,斯岂非以无有为有邪!夫人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以瓦无是非心,不可就此成心论彼未成心也。然则史书往事,昔人所印是非,亦与今人殊致,而多辩论枉直,校计功罪,犹以汉律论殷民,唐格选秦吏,何其不知类哉。
(同上,第76页)佛教批判世俗以有为真的说法叫“破执”,既破“我执”,也破“法执”。太炎释《齐物论》也循此路数:“广论则天地本无体,万物皆不生,由法执而计之,则乾坤不毁,由我执而计之,故品物流形,此皆意根遍计之妄也。
”(同上,第78页)上述以藏识释“丧我”、“成心”、“真宰”,是破我执,而以幻有解物我、有无、生死,则是破法执。对“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句,章氏这样解说:末俗横计处识世识为实,谓天长地久者先我而生,形隔器殊者与我异分。
今应问彼,即我形内为复有水火金铁不?若云无者,我身则无;若云有者,此非与天地并起邪?纵令形敝寿断,是等还与天地并尽,势不先亡,故非独与天地并生,乃亦与天地并灭也。若计真心,即无天地,亦无人我,是天地与我俱不生尔。(同上,第90页)
凡此万物与我为一之说,万物皆种以不同形相禅之说,无尽缘起之说,三者无分,虽尔,此无尽缘起说,惟依如来藏缘起说作第二位,若执是实,展转分析,势无尽量,有无穷过,是故要依藏识,说此微分,惟是幻有。(《齐物论释改定本》,见《章太炎全集》第6卷,第96页)所谓“处识”、“世识”也即空间与时间意识,它们也处藏识之中。
章氏对天地、物我关系的分析,目的是起破除世人以心识为真的作用。太炎认为以缘生说幻有存在着逻辑上无限倒退的缺点。
你说房屋是瓦木构成,故无自性。可瓦木以及瓦木的构成者是否有自性呢?解答将得无穷尽地进行下去。不如藏识之说,知人“复有意根,令其坚执,有乘刚之志,故触碍幻生;怀竞爽之心,故光采假现。而实唯是诸心构相,非有外尘”(同上)。一下子截断退路,不再拖泥带水。
由于法执我执俱破,故所谓生死便非真假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在释“庄周梦蝶”义中,太炎自问自答:“或云:轮回之义,庄生、释迦、柏剌图所同,佛法以轮回为烦恼,庄生乃以轮回遣忧,何哉?答曰:观庄生义,实无欣羡寂灭之情。
”(同上,第118页)究其原因,是庄生以百姓之心为心。“其特别志愿,本在内圣外王,哀生民之无拯,念刑政之苛残,必令世无工宰,见无文野,人各自主之谓王,智无留碍然后圣,自非顺时利见,示现白衣,何能果此愿哉。
苟专以灭度众生为念,而忘中涂恫怨之情,何翅河清之难俟,陵谷变迁之不可豫期,虽抱大悲,犹未适于民意。”(同上,第119-120页)太炎此说,实在系以佛陀之心度庄生之腹,然否不必深究,但颇感人。所以尽管太炎迷于佛,但不是逃于佛,相反,表面上是退,实际姿态是进。他要借佛法入世以至救世。
三、辨名析理
章太炎是要从子学、特别是庄学中寻哲学的。不过,他更喜欢叫做“见”:“九流皆言‘道’……白萝门书谓之‘陀尔奢那’,此则言‘见’。自宋始言‘道学’(‘理学’、‘心学’皆分别之名),今又通言‘哲学’矣。‘道学’者,局于一家;‘哲学’者,名不雅;故晋绅先生难言之……故予之名曰‘见’者,是葱岭以南之典言也。
见无符验,知一而不通类,谓之‘蔽’(释氏所谓‘正见见谛’)。”(《明见》,见章太炎,1920年,上册)简言之,哲学就是去蔽明见,即打破流俗的偏见。
佛学喜欢言“破”就是这个意思。但“破”不是简单表达相反的意见,而是要令人信服的证明。所以,在西方哲学中,太炎非常重视认识论的价值。他说:“康德以来,治玄学者以认识论为最要,非此所立,率尔而立一世界缘起,是为独断。
”(《?汉微言》,见章太炎,2000年)不论谈康德还是讲法相,其共同点就是追求说理。所谓名相分析,是佛学中的一种说理方式。章氏说《齐物论》破“名家之执,而即泯绝人法,兼空见相”,表达的正是他的《齐物论释》的主旨。
《齐物论》有一段话:“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太炎认为“‘指马’之义,乃破公孙龙说。”暂以其释“指”为例:公孙龙子《指物篇》有“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
”太炎对此解释说:“上指,谓所指者,即境;下指,谓能指者,即识。物皆有对,故莫非境;识则无对,故识非境。无对故谓之无,有对故谓之有。以物为境,即是以物为识中之境。故公孙以为未可。庄生则云以境喻识之非境,不若以非境喻识之非境。盖以境为有对者,但是俗论,方有所见,相见同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