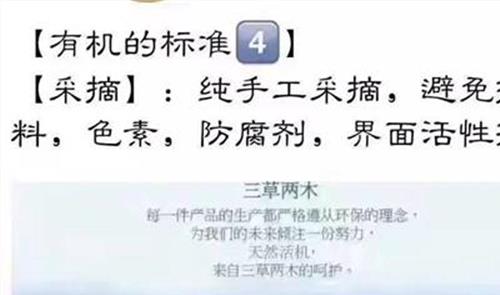木心先生和樊小纯关系 木心先生·送别与守护
神奇之事。木心先生入院前,有人适巧转来在上海意外发现的木心照片,摄于1946年,他才十九岁,斜站着,学生装,戴副白手套,身边站着两位穿长袍的男子。
初次给他看,他完全不能辨认,移开目光。翌日再试,他可怜样地抬眼看我,一脸困扰,又低头看,终于嘟囔道:“噫……是我呢!神气得很呢!”
忽然,木心扭头痛哭。
我不愿描述这片刻。他头一次当我的面,失声大恸——那么多年,我只记得先生有过两三次微妙的哽咽:说起晋的嵇康与山巨源,说起托尔斯泰的出走,说起他夭折的小姐姐——有谁近半个世纪再没见过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吗?先生的所有文稿、照片,都毁失了……转瞬,他展颜微笑,如小孩,一点不羞愧刚才的失态,又看照片,幽幽说起当年的情形:“大家都喜欢我……那是我第一次办个展呢……”之后他再看,再哭,顷刻收泪,无辜而失神地看我们,显然动着什么别的念头,然后仰面睡倒。
另一份礼物是林兵的美术馆设计稿。“一顶桥?”先生讨饶般地看我,知道自己糊涂了。“美术馆!你的美术馆!”我冲他吼。
哦。风啊,水啊,一顶桥。浙东方言便是这样地将“桥”叫做“一顶”。他疯了,我想,等着他恍然沉吟。渐渐地,先生看向天花板,语调平静:这可以使人疯狂……这样地倒在床上,死了,真好。 我不确定他是否终于确认这是他的美术馆:他最后牵记的事。
“先生!明年开馆,我轮椅推你去!”我高声骗他,毫不愧疚。我所全神贯注迹近享受的事,是他糊涂了:倘在早先,先生的独断无比挑剔,但7月与设计师面对面,他已放弃了毕生的精明:“去弄吧……弄好了,吓我一跳。”
11号病房。空寂的长廊。可有治愈的希望么?如若不然,先生还有多久?“多久”,难以启齿的词。19日,木心读者樊小纯请到上海方面三位会诊的中年医师,各事心脏、呼吸、神经科。江南午后阴冷,他们进入病房,轮番诊视,事后分文不肯收取。
事毕,与本院大夫聚在面北的大间详细陈述:关键是左肺淤塞,必须动用器械吸取积痰,期间,心脾肾肝出现任何异常,便无可救。多久?大量病例固然可以援引,一说是三个月,一说可能半年。所有词语回避死亡,同时,指向终结。
木心难以闯过今冬。看着他由壮及老,老而弱,弱而衰,我明白这是他最后的时光。只是,还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