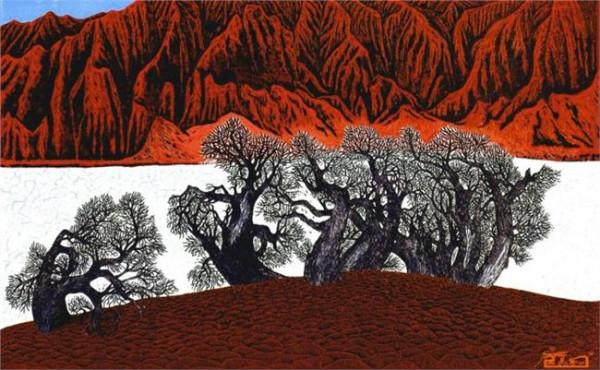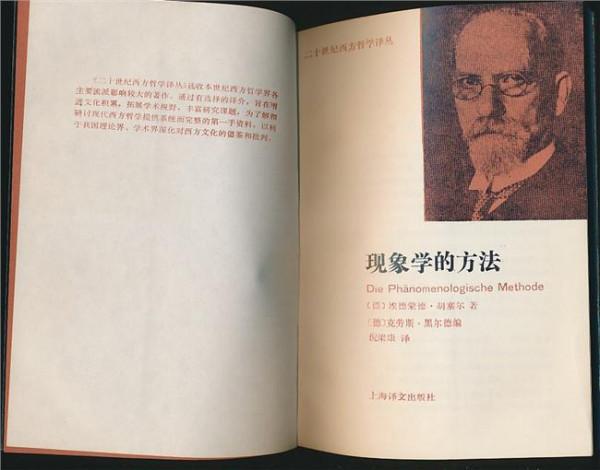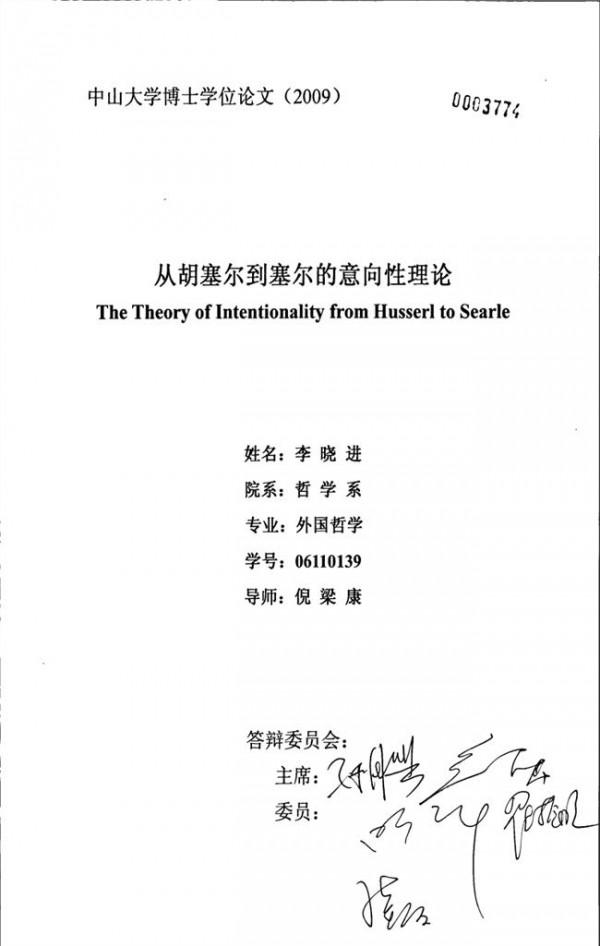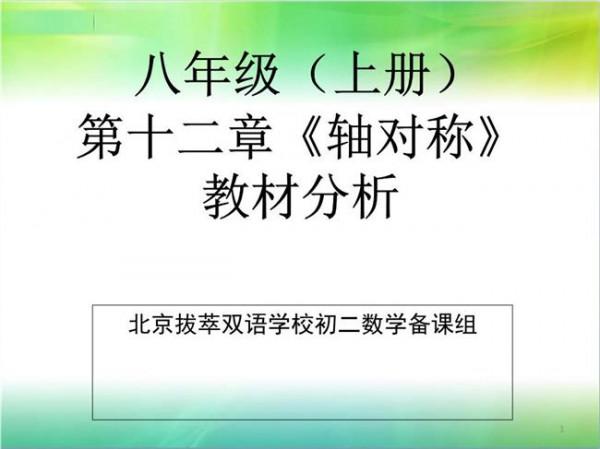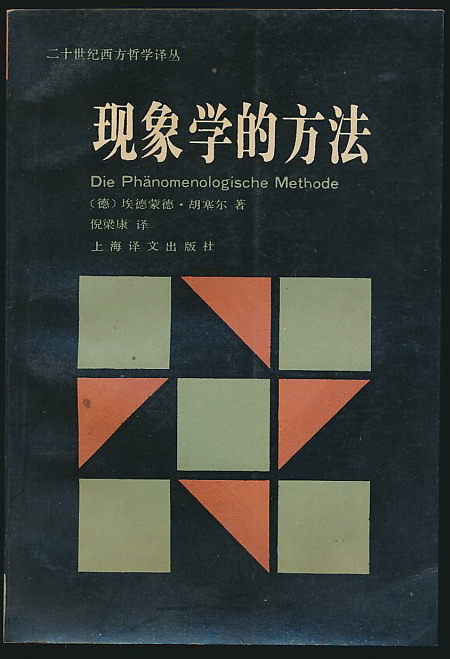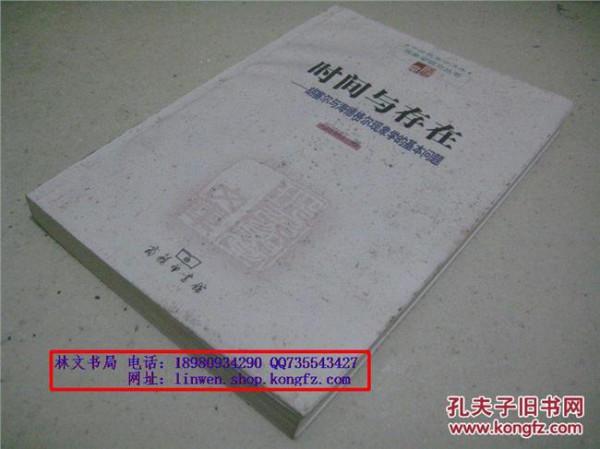胡塞尔物自体 康德的“自由”、“物自体”及其他
“然而,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固然不在它们的立法中,但却在它们关于感觉界的诸效用中不断地相互掣肘,不构成一个领域,原因是:自然概念固然在直观里表述它的对象,但不是作为物自体,而是作为单纯的现象;与此相反,自由概念固然在它的对象里表述一个物自体,却不能使它在直观里表现出来,所以两者中任何一个都不能从它的客体里(甚至于从思维着的主体里)获得一个作为物自身的理论认识,或者,如物自身那样,成为超感性的理论认识,人们固然必须安置这个观念作为一切经验对象的可能性的基础,却不能把这观念自身提高扩大成为知识。
”(中译本,第12页,译文无大误)
这段话的总体意思是康德常强调的基本思想,并不难懂,说的是自然和自由、现象和本体(质)之间的非立法性制约关系。康德先说自然作为对象固然可“直观”,但不是“物自体”,只是“现象”,这个意思也好懂,但他接着说“与此相反,自由概念固然在它的对象里表述一个物自体,却不能使它在直观里表现出来”,这句话的前半句,如何理解?“物自体”不能在“直观”里表述出来,这是康德常说的基本意思,好懂;可是那句一带而过的“自由概念固然在它的对象里表述一个物自体”却要费点思考,而康德在这里似假定读者已经很懂得的样子,未多作解释。
我在这句话上,作了一些发挥,彭冈君觉得有些意思,建议把它写出来,于是就有这篇短文。
为什么说:“自由概念固然在它的对象里表述一个物自体?”“自由”与“物自体”是什么关系?当然,我们都知道,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不是“知识”的事,——“因为”它不是知识的事,“所以”它就是“实践”的事;“知识”讲“必然”、“自然”,“所以”“实践”就讲“自由”、“道德”——过去的理解,似乎就是这样的“推论”出来的。
显然,这种“因为”、“所以”的关系,不能平息我们的问题。为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理解什么叫“自由”。
康德意义上的“自由”,首先是一个“否定”的力量,不是那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怡然自得的“境界”。“自由”是要“摆脱”些东西,从那些东西里“解脱”出来,那么,“摆脱”、“解脱”些“什么”?“自由”是“摆脱”、“解脱”那眼前的、现成的东西,“自由”就是对那眼前、现成的东西(现实)说:“不”、“不对”、“不行”。这是“自由”的基本的、哲学性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引伸出一些有意义的意思来。
首先,这个意义上的“自由”,说明了、显示了一个更高级的“理性”领域在。“自由”不仅是“随心所欲”,不仅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它只是表明:支配人(的行为)的,不仅仅是眼前的、当下的现成的“事实”。譬如说,人饿了要吃东西,如果眼下有面包,那么,拿起来就吃;如果没有,就去找,就去买,总之,我们受“饥饿”的支配。
然而,如果在一些条件下,譬如,是敌人给的面包等等,那么,我宁可饿死也“不”拿来吃,于是有伯夷、叔齐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明人受一个比“饥饿”更高级的“律令”支配。“饥饿”是“自然”的,但那更高级的“律(令)”则是“非自然的”——“理性”的。所以,我们说,恰恰是人们在说“不”字时,最为清楚地显示了人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理性”的。
其次,我们还看到,“自由”这个“否定”的力量,还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因而是“无限的”。“无限”不是1,2,3,4,5⋯⋯的“无限”,所以不是“无限膨胀”,为所欲为;“自由”(理性)的“无限”,是说“不受任何限制”,就是人们“可以”对一切现存的、眼前的事实(事物)说“不”——虽然人并不总是说“不”,但它天生就是“被”许可(可以)对一切现实、现有的东西说“不”的。
“不”(否定)是人作为人的天赋的权利,所以“自由”也是一种(理性)的力量(power)、权力(right)。人,只有人,保留了对一切现成的东西说“不”的权利,尽管他并不总是在用这种权利,或者甚至说,多数人、在多数的时候,并不使用这种权利。
那么,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和“物自体”又有什么关系?
当人们运用这个“自由”权对现存的东西说“不”字时,蕴含了这样一个意思:这个现存的东西“不对头”,“不合适”,总之“不行”。“不对”、“不行”,乃是说,它——这个现存的东西,“本不该(不应)是这个样子”,它——这个现存的东西,“本该(应)”是“另一个”样子的。
这样,我们就贴近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了:这个“现存的东西”,原来只是“现象”;那个由“自由”显示出来的“本该”、“本应”“另一个样子”,乃是“物自体”—Dingeansich。Dingeansich就是那个“本”,那个“该”,那个“应”“是”的东西。
所以,从“自由”的角度来看,那些既成的、当下的事实、事物,不过是一些“现象”,是一些表层、表面的东西,而还“应”有一些深层次的、“本来”的东西在“现象”的背后;那么,这些在既成事物(现象)的“背后”的“应是”的东西又是些“什么”东西?
康德告诉我们,这些“应是”的东西,是“不可知”的。在康德看来,我们能够知的,只是那些“现象”。这里所谓“知”,是“对象”提供感性的直观,人“接受”过来,按照必然的规则来加以综合,因而一切的“知识”,必须要有感性把材料提供出来,形成“直观”;但那“应是”的东西,源出于(理性)“自由”,它只是提供对感性、现存的东西说“不”的权力,至于具体倒底“应是”些“什么”,它并不过问。
当然,康德也承认,人们可以从对现存事物的知识中推测——预见到事物——现象变化发展的前景,或者可以有一个合乎科学知识的设计方案,以自己的劳作,将其实现出来,这时这些“方案”、“前景”可就是“知识”的产物,自然是可以“直观”的。
不过,这些在康德看来,都属于“科学知识”、“现象”的范围里,而并非“物自身”,理由是:一旦这些方案、前景“实现”了,“自由”的“理性”仍然有权对它们说“不”,仍然可以说“不对”、“不行”。
所以这些比较而言更为“完满”的现实事物,仍不是“物自体”。“物自体”仍在它们的“背后”,不能得到“直观”。“物自体”不是“比较出来的,因而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
“本应是些什么”,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理想”,但它们不是一些具体的、可以直观的观念——设计方案、前景,因为“自由”要保留它那不受限制的“否决权”,所以它并没有具体的、可以实现的“理想”,而是坚持着对现实事物说“不够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永远是“理想的”,不是“现实的”。
“自由”的“理想”,也不可“想象”(Imagine)为一个“大而无当”(或通常意义上的“至大无外”)的“全(体)”,不可“想象”为无限“膨胀”的“气球。”“自由”的“理想”(ideal),不是“意象”(image);因此,它的“无限性”,也不仅仅是“无限大”,而只是“不受任何限制性”。
按照通常“理想”的“模型”制造出来的任何东西,同样也“限制”不住“自由”的理性和理想。这样,严格意义上的“自由”的“理想”,不可能是一个经验的“概念”,因而永不能转化为经验的“对象”,不可能提供经验的“直观”。“自由”的“理想”性,不可“想象”,没有“意象”。所以,哲学上所说的“无限”,绝不是“想象”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理性”赋予“人”以“自由”,这种“理性”和“自由”,在“人”对现存事物说“不”、“不行”里,显示出来,因为在“理性”看来,现存之万物,都“本不应如此”,“原本可以不是这个样子”的;至于“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什么样子”,则是人类不断的努力劳作的过程,是人类生活、生产、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
这个过程当然是无限的,但人类劳作、人类生活、生产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是无限的,但人类生活、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的可能性,正说明人的理性的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人的自由和理性赋予自己的生活、生产、科学、技术发展无限发展的权力。
人的自由的理想不会在哪一天完全“实现”,作为“自由”的“目的”(目标),只是悬设的“目的”,而不会是现实的“结果”,因而就是那个“目的”之所以为“目的”那个东西,是为“目的性”。这个最为根本的“目的性”,因其不会成为“结果”,而永远“悬设”在那里,它是“思想体”—noumenon,不会成为“现实体”—phenomenon。
“思想体”因其“非现实性”而成为“理念”(idea),“物自体”是一个“理念”。
“理念”因为没有一个相应的“对象”而永远被“悬设”在那里,因而是“悬念”postulation。所以,“物自体”固然也是一个名字(name),也有“意义”,也有“所指”,但“指”的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事物;但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abstractconcept),不是从具体事物中“抽”(abstract)出来,或“(综)合”(con)起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物自体”这名字,就像“自由”的意思那样,原本也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物自体”意味着“现象”的“否定性”。
“理念”、“思想体”意味着“经验概念”和“现实性”之“否定”的方面。“是什么”总是意味着“本不该是什么”,而对于“该是什么”,似乎在科学知识上没有一个正面的、肯定的回答。
康德并且还指出,如果要为“本该是什么”这个问题给出正面的、肯定的回答,则一定会出现“矛盾”。“物自体”“本应是什么”以在理论知识上的矛盾性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并“防止”说“本不应是什么”这种“自由”权力被“剥夺”——使之“不受限制”,不受“侵犯。”
“矛盾”性使“物自体”这个“理念”变得“玄暗”起来,它不可能完全“透明”,在理论上它始终是一个“问题”,而它又是结结实实的“物(自己)”,而不是一个“幻影”。
不仅如此,“物自体(自己)”不仅不是“虚无缥缈”的,而且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也就是说,“物自体(自己)”的“理念”,“保证”了人类的“自由”权不受侵犯,从而促进——吸引着人类不断地努力劳作,努力奋斗,在这个意义上,竟是“物自体(自己)”“支配”着人类作为“自由者”的“族类”的历史“命运。”
这就是说,“物自体(自己)”的问题,只有“自由者”(不受限制者)才提得出来。“饥饿的人”在填饱肚子之后,不再追问“食物”,只有“自由者”才会保持住“否定”的权力,才会有“本应是什么”的“理念”(理想),才会永远“悬设”一个“目的(目标)”,而不至于放弃对现存事物的追问。
“物自体”向“自由者”“显现”出来,表明它不会成为“现象”的一个部分,不会被人的经验概念体系所“把握”,也不受运用于经济世界的法制的支配,“人”无权为“物自体”“立法”,“物自体”不是“人”的经验世界的“居民”,不服从为这个世界制定的法则。人,即使作为“自由者”,有充分权力说“本不应这个样子”,而并无充分权力说“本应”何种“样子。”
康德说,“物自体”不可“知”(erkenen),但可以“想”(denken)。因为“物自体”不能成为一个经验的对象来“提供给予”人的感官;而“想”则不需要有这个条件。当然,“知”要“知”些“什么”,“想”也要“想”些什么。但,这两个“什么”(was,what)是不同的,“物自体”作为“什么”不向人的“感官”“显现”,而只向人的“理性”“显示”(sign,mark)。
不仅如此,“物自体”似乎只有人在发现“自己”无知时,才“显示”出来。“物自体”,在康德的意义上,是“知识”的“界限”,是“知识”的“终止”,但却不是“思想”的“界限”,恰恰相反,“物自体”是“思想”的“开始”。
对“物自体”的“思”,在康德那里已经有所指示。“物自体”对“自由”显示,而“知识”、“科学”只把握“必然”的领域。由“自由”指示的“物自体”不是知识和科学的“对象”,但它却是“理性”的“对象”,而倒也不是一种朦胧、神秘的“感觉”;恰恰相反,它是纯粹理性的,即不杂存任何感觉经验的。
这样,对“物自体”的“思”,不同于经验的知识和科学,但却是最为理性的,是纯粹理性的。这种“思”,不是从感觉经验所给予的“材料”出发,而是从纯理性的“自由”出发。
哲学家康德
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发展,都在努力克服康德的“物自体”,要把“本质”与“现象”结合起来,但其出发点不是康德的知识性“必然”,而是理性的“自由”。他们都不能不正视康德所指示出来的问题。费希特在建立其主体先验知识论体系时,首先提出“A是A”同一性的优越性,因为不问“A”存在(实存)与否,“A是A”的这一命题都是有意义的、对的,以此“摆脱”一切感性材料之必然性,来建立他的“知识学”——他的“Wissenschaft”,已不是经验之科学知识,而为自由的、理性的“思”。
黑格尔努力要把握康德“物自体”的意向是非常明显的,他要使“本质”在通过矛盾、斗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己显现出来,使“自在之物”(物自体)转化为“自为之物”,从而可以以思辨的哲学体系去把握自己,但他的“哲学思辨”和(经验)“科学理论”也是完全不同的(公众号“无处不哲学”编辑首发)。
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在克服了感性的限制之后,“科学理论”才能提升为“自由理性”的“思辨”,而“自由的理性”或“理性的自由”正是“精神”(Geist)之本性。
看来,必然性之经验科学思维和自由性之理性思维之间的原则区分,在上述思路下已被认定为确定无疑。在这个思路上,我们遇到了本世纪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胡塞尔提出要“回到事物本身”,表面上看是针对康德“物自体”不可知的,但实际上他是主张把一切的经验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都要“括出去”,“悬搁”起来,“事物本身”——胡塞尔用的是Sach——才显现出来,所以他的以“事物本身”为追求目标的“现象学”——一门“严格的科学”仍是康德意义上的对“物自体”的“自由”的“思”。
在本世纪把这个问题想得最清楚的是海德格尔。正是海德格尔仔细研讨了不同于科学性理论的历史性、时间性、自由性的“思”,他有专门的论文——《什么叫思》讨论这个问题;也正是海德格尔,写了非常精练的短文《对“事物”(Ding)之追问》,在文中他用一种平易的方式指出,再没有比“物自身”(Dingansich)离我们更“近”的了;说当代的科技发展,可以把最“遥远”(包括空间和时间的距离)的事物,呈现到我们面前来,但它们对“物自体”却无能为力,高科技的进步并无助于“什么是物”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科学”不是“思想”。海德格尔同样是将经验的自然的科学“悬搁”、“括”起来,严格划分“诸存在者”与“(存)在”,使“悬”与“在”在“摆脱”“在者”(使“在”自由)的基础上,“同一”起来,乃是海德格尔的一个主要思路。
对Sein的追问,实际就是对Dingansich的追问,而追问Sein的“思”,就不是抽象概念式的(经验)科学体系,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同时也是“自由”的“思想”。
“自由”在海德格尔为“让(使)其存在”(Sein-lassen),而不是“使”“诸存在者”存在,就“诸存在者”(Seiende)言,“存在”(Sein)为“什么也不是”(Nichts)。
和“悬搁”、“括出”一样,这里仍需一种“否定”的精神,没有此种“否定”精神,“物自体”、“理念”(Idea)、“存在”(Sein)的问题出不来;(公众号“无处不哲学”编辑首发)而“否定”精神,又蕴含着追问一个“应该”和肯定答案,尽管这个答案不是任何经验科学在原则上即能给出的;而如果特别着重从这个“应该”的角度来思考,那么又会有另一个思路。
康德把“实践理性”置于“优越”的地位,他所考虑的侧重点正是那个从纯粹的(形式的)理性出发的既有否定、又有肯定意味的“应该”,但它因其“纯形式”而是空洞的;从积极的“应该”出发,把海德格尔“Sein“中的“应(如何、如此)”着重地来考虑,这似乎是法国列维纳斯的思路,他似乎认为既然Seinilya是因为自由的“应该”才显示出来的,那么研究“应该”的“伦理学”(ethics)则要早于“存在论(本体论,ontology)。
这里,我们对于康德这句话的讨论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康德此处只概括地提到这个意思,因为他估计读者都已读过他前两个“批判”。但这句话不是随意说的,它蕴含了康德的一个基本思路,而我们作为后来人现在再来读它,更觉得这个思想是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思想家所一直重视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