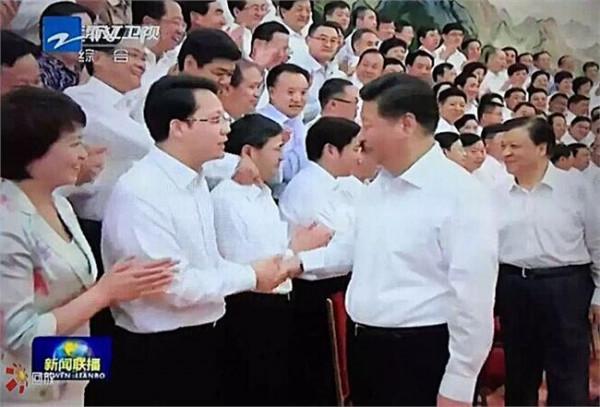李佩甫羊的门 陈行之:对生活的一种发现——李佩甫长篇小说《羊的门》阅读随想
艺术的功能在于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或者说,使没有被发现的东西被发现,小说更是如此。生活之流如滔滔江河,奔腾不息,哪一朵浪花从本真的意义上说明着这条江河之浩淼、庞杂和宏大?这需要发现。任何人都可以从这条江河掬出一捧水来说这就是我的发现,但发现和发现不同。
看到了水不一定就是看到了发现。事实上我们的很多小说只是这样的一捧水。当你从一个人的手中看到在别处没有看到的晶莹的时候,你就可以认为你看到一个人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我看到了《羊的门》。
《羊的门》不深奥,它不是那种以史为线、在历史舞台上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的长篇小说,例如《战争与和平》,例如《白鹿原》。它基本上是在生活的断面上讲述它的故事的。我觉得它更像狄更斯,像巴尔扎克。
《羊的门》很朴实,它不是那种以技巧的玩弄为得意的作品,从这里你找不到人们曾津津乐道的魔幻现实主义,找不到福克纳,找不到克洛德·西蒙,甚至也找不到昆德拉,找不到马尔克斯,它就是它,你不能把它同别的作品做简单的类比。但是人还是喜欢类比。如果你类比的不是形式,而是精髓,你会惊讶地发现,《羊的门》其实就是我们中原大地上的《百年孤独》,是《喧哗与骚动》,是《佩德罗·巴拉莫》。
小说,无论什么题材的小说,都应当隐含着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人生的阅历,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在作品中感受到力量与成熟。
可以想见,李佩甫是从《羊的门》构筑的那个艺术世界的原型生活中滚过来的。有的人滚过来也就滚过来了,仍然懵懂无知,而李佩甫看到了小说家应当看到的那种矿藏。这里面肯定会有许许多多难以言说的愤懑、苦恼和忧伤。小说是忧伤的,这一定是李佩甫内心深处的忧伤。
他明明知道结局,可是他仍然努力地往山上推他的巨石。就对人类良心负着某种责任的作家来说,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在命运都是西西弗。这是一个残忍但极为优美的神话。这个神话说明着人是可以走得很远很远的,你无法想象的远。力量,成熟,这是对一部小说进行褒扬的最好的字眼。《羊的门》受之无愧。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呼天成这个呼风唤雨之人,将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他的个性是我们这块沉重的土地的个性使然,类似于在灼热的科马拉村时隐时现的佩德罗·巴拉莫。这是一株只有这块土地才能生长的植物。你不能用美和丑的两分法来分析呼天成。
他就是美,他就是丑,而且很大。他那幽暗而强悍的灵魂深处,非黑非白,是一团混沌在翻卷。他既不是善,也不是恶,他是某种原生质的东西。如果你非要用善恶的观念来品评他,他马上会解体为一滩水,一缕烟。你只有在从整体上感知他时,他才是切切实实存在的。
所以我不赞成对这个人物进行通常意义上的如丝如缕的美学分析。这个人只有作为一个巨大的团块存在之时,才能够以其独特性告诉我们别的作品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种东西称之为巨大的思想,它一旦分解,那些絮絮叨叨实际上也就不成其为思想了,那不过是思想的排泄物,毫无意义。欣赏好的艺术需要一定的距离,需要一定的模糊性,说的也许正是这个道理。
中国当代文学上的这个位置实际早就被现实留出来了,只是没有人去把自己所能创造的人物安放在那里去。中国社会的封建宗法意识在城市、在乡村、在一切有人的地方顽强存在,这已经不是什么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我们发现封建主义仍是我们与之相伴、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东西。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切都是奇异的:进步的后面有可能是倒退,而表面上看来在倒退的,其实质却是在前进,大踏步地前进;成功者可能是失败者,失败者可能恰好体现着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到处都被悖论操持着,到处都显示出一种非常状态。
呼天成的价值就在于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十分鲜活生动地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之中,作为后来人的呼国庆陷入到政治的、人生的泥潭之中,其实是一种必然,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把自己提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一样。
这时候,《羊的门》的现实触角就伸向了历史——就像我们从所有优秀小说中看到的那样。既然《羊的门》的历史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如上所说,它是什么而不是什么。这对于当前的小说创作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昆德拉那么多关于小说的言论中,我最为欣赏的一句话是:“小说的灵魂,它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说出只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而小说说出的东西是很难用观念做出复述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对某一部小说的理论阐释相对于小说来说都显得那么蹩脚的原因之一。
《羊的门》很难复述,很难归结。读鲁迅的作品,也常常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你可以用你的观念复述或归结阿Q,但你不能说你所阐释的阿 Q是唯一的阿Q。呼天成、呼国庆身上所蕴涵的社会学意义,也会见仁见智。是植物说明着土地还是土地说明着植物,即使在我们和作家的本意之间,也会产生认识上的差距。这样就对了。这说明《羊的门》进入到了“说出只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的境界。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对小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小说家的天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阔。好比杀猪,一般来说是先杀头的,但是倘若有一个人偏从屁股开始杀,你也没有办法,你顶多说:猪是不能这样杀的。但他就这样愣是把猪也杀死了,你能说他不对么?现在有的人就愣是把小说写得谁也看不懂,也无奈。
我倒是欣赏《羊的门》的写法。小说,必须有一个好故事,让人爱看,其次才是你的人物设置、性格塑造之类的问题。这正是所谓现实主义的写法。但是现在现实主义的名声不大好,好像谁要是还固守什么现实主义就是创作上无能似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偏见。据我所知,最近几年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都是充满现实主义力度的。《羊的门》至少又一次说明现实主义是能够产生杰作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把创作方法比喻为作品产生的土壤的话,那么,现实主义这块土地恐怕更肥沃一些。
这难道不是这部作品给我们的另一种启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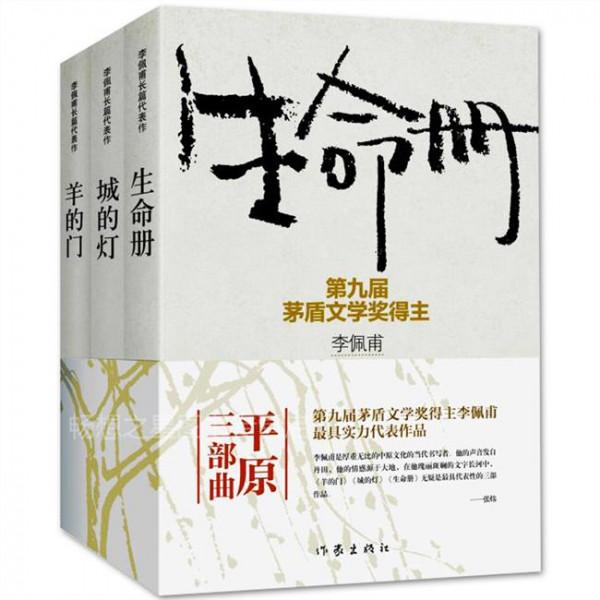





![【山坡羊叹世陈草庵】陈草庵《[中吕]山坡羊叹世》](https://pic.bilezu.com/upload/7/63/7636ffa93833097ebf62f2e998aa44c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