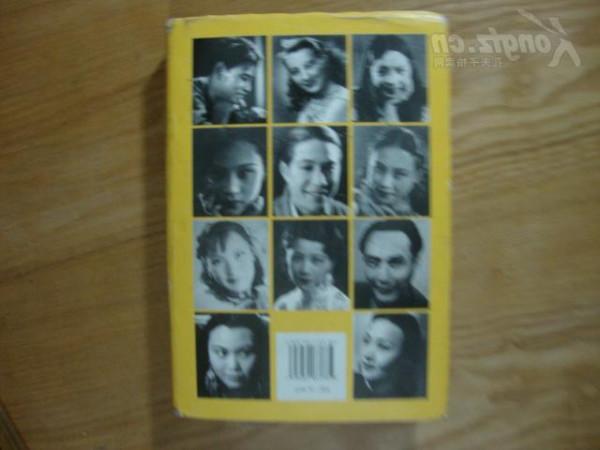金焰与秦文 金焰与秦怡的故事(中)
既然老金与我一起去香港,我们决定就不再躲躲藏藏,我们就同居吧。我因工作关系,实际上有时连和他说说话的时间也没有,他也趁此机会和朋友们聚会。一天,老友祖光忽然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结婚?”我与老金都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也许我们都未觉得结婚是那么重要,尤其是我,我认为如有真情,不结婚也能白头偕老,如无真情,结婚也约束不了,人的感情是不能靠约束来维持的。
我们虽未回答这个问题,但还是同意朋友的善意,决定结婚了。
朋友们给我们一一安排好,在香港的宇宙俱乐部,有将近五桌朋友来庆贺,特别是郭沫若先生当了我们的证婚人,并题词“银坛双翼”四个大字以示祝贺,大家都纷纷签名,可惜在“文革”时,这也说成是四旧,被红卫兵给撕了。
那天到场的几乎都是文艺界前辈,有作家、艺术家等各方知名人士,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讲了话。那天晚上,酒醉的人很多,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喝醉了,他与丁聪等许多人跟在我后面拉着我的衣服,一边跟着走一边说:“我愿意做你的尾巴……”我赶紧回过头来,让他走在我前面,我拉着他的衣角说“还是让我做你的尾巴吧。”真像是醉熏熏的一群孩子在做游戏一样。
热热闹闹的所谓婚礼结束以后,我俩暂时租借了一个英国人的高级饭店名叫“雅兰亭”住几天,也算是去度蜜月吧。虽说我本来没有觉得结婚有那么重要,但一旦举行了这样的仪式,在我心中忽然升起了一种奇异的从未有过的美好的感受,尽管我已是第二次结婚,然而由于过去从未有过爱,从未有过幸福,所以如果说真正的爱才是初恋,那么这次就是我的初恋。
也可以说,我在爱,爱一个人,那种希望真能与他白头偕老的纯洁的情感油然而生。我们回到了饭店,真奇怪,好像我们从未同居过,我等待着,珍惜着这个幸福的时刻的到来!
可是,这一切都成了泡影,老金已醉得不省人事,他回来已有点东倒西歪,然后一直呕吐不止,以后就一直连续昏睡了两天两夜。我的婚假一共只有3天,因为我在拍戏,不能等待,我赶紧退掉了“雅兰亭”的房间,因为这种地方很昂贵,回到“万邦”去住,带着遗憾的心情,又去白天黑夜地工作。这就是我们的蜜月。
我们婚后大概第5天晚上,蒋君超请我们去吃晚饭。他还请了老金的一些朋友,包括老金与人美过去的好友等人。老蒋的生活条件较好,他单独住一幢洋房,他们也是老朋友了,他是为我们结婚特地宴请的。
本来这是件高兴的事,但在席间,老金与那位太太一直在用广东话交谈,忽然间,老金越说越激动,大发雷霆,推翻椅子往外就跑,于是,在座的男同胞纷纷出去追赶,但谁也不可能有他这样的本领。香港过去的电车是不关门的,电车正在行进中,他从这部电车跳上去,然后再从另一出口跳下去,又跳上另一辆电车,这样几个跳上跳下,就再也找不着他人影了,一直弄到深夜,追赶他的人都已精疲力竭。
老蒋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场面,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又非常担心老金出祸,最后我只能一人先回旅馆。
我无法抑制这样的痛苦,我哭了,可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痛哭,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我无法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爆发的生活,这种无故的心灵的冲激。
我想我难道又走错了路?我一个人伤心地坐在阳台上,我不知道下一步究竟应怎样走下去,我还是走吧,从此不再见他?我的纷乱的思绪,难于作出任何理智的决定。正在我哭哭啼啼时,他忽然冲进房门,叫着他给我起的小名“小迪,小迪”。
我一句话未说,他奔到阳台上,两手扶着我的肩膀,深情地看着我,这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再这样看过我,跟我说他错了,错了,他痛恨自己会这样伤害我。也许就因为他这一次认错,才使我们以后共同生活了37年,我相信他从来没有向人这样认过错。
他给我写信了
解放后,老金确实改变了,虽然有时仍然会酒醉,并闹出些事来连他自己都不知,但比起解放前这种事就少多了,他也能约束自己了。我们有了儿子以后,许多护理儿子的事儿他都会做,如给儿子洗澡等等,我总是向他学。
我那时经常出去体验生活,他经常替我打铺盖,他打的铺盖,严严实实,而且许多日常的必备品他会一样不漏地给我放进铺盖。他打的铺盖背起来很省力,有时我看他忙就自己乱打一个,当他回来看到,就会立刻替我重打,对待任何这类事情,他决不偷懒,决不马虎。
我永远不会忘记,大约是1951年的秋季,我出发去拍《两家春》的外景,老金被派到北京的全国劳模大会去做接待劳模的工作。解放后工作忙,我们经常分赴两地是常有的事。老金与我从恋爱到结婚,从未写过一封情书,连一张字条也未写过,我是很喜欢能有书信来往的。
因为我觉得书信上更能表达丰富的感情,更传情。然而他不喜欢这一套,有时我出外到了目的地给他写封信也得不到回信,慢慢习惯了我也不写信了。
可是,这一次我在石家庄束鹿县拍戏时,竟接到了他一封长信,这不是那种甜言蜜语的情书,而是一封出自于他内心深处的受到深深感染的情感丰富的信,我读了他的信,知道他取得了极大的收获,为此与他同享快乐。
他告诉我,他因接待劳模的工作做得出色,大会发给他一枚劳模奖章。他本来是做大会的接待工作,但因他出于对那些劳模的崇敬与爱戴,心甘情愿地去为他们做一切,甚至倒痰盂等事;他感到招待所有些工作做得不够,因此,从生活上的一切琐事到开会的工作,全都包揽下来。
他在字里行间透露了对党的信仰及他自己的许多从未有过的感受。我看到他的信无比高兴,从心中产生一种亲切感,因为他把我看做他的真正的亲人才会把心底的肺腑之言向我倾诉,我感激他对我的信任,我想这才是夫妻。
他从来都是沉默寡言,要打开他的心扉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次他能有这样开朗的心情,能和我畅叙他由衷之感,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也立刻回了他一封长长的信,告诉他我为他的高兴而特别高兴。
我决没有想到这次通信竟是我们两人相处一生唯一的一封信。他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理解,总是过着抑郁愁闷的日子,虽然他对待工作还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他拍的仅有的5部戏也还是完成得不错的,长期的病痛和错综复杂的生活,使他又失去了开朗豁达的胸襟,他又沉闷了。
难产
1953年,我正准备参加《渡江侦察记》影片的拍摄工作时,却发现怀了孕,要第二年夏季才能分娩。临近产期,一天清晨4点钟,我还在睡梦中,忽然觉得羊水已破,于是,我一人悄悄地赶紧雇了辆三轮车去华东医院。
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医生检查后说,胎儿心脏已停止跳动,孩子已死亡,医生说这种情况生产将会有困难,可能几天,也可能一个月,但也可能明天会产出已死的婴儿。鉴于这种情况,我再不能顾及家中人的休息,当然首先给老金打电话,可他说那天上午正好是剧团进行政治测验,他感到非常为难,最后作出了抉择,他说他上午不能来,他怕别人会认为他逃避考试,如果去考了,即便不及格倒也无关,但被认为是逃避考试就很丢脸。
我尊重他的抉择。下午他打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他告诉我考试过了,他只得了59分,因为他心慌意乱,把题目都看错了,但他认为这样心里还是踏实的,“人言可畏”,在他这种硬汉子身上也这么可怕。当我现在再来回忆此事时,我真觉得这个人实在是老实有余了,不过我自己不也是如此吗?当我孩子得了精神病以后,我还要远离他去参加“四清”工作。
当时,他的这种不能令人相信的老实,倒使我十分冷静。我想我必须自力更生了。由于我的镇静,并按照医生的指示,不断做无痛分娩,把气往下压,果然在第二天上午10点钟,产下了死婴。一星期后,我自己又坐了三轮车回到家中,一切又都归于平静。
他是个死硬派
1958年老金得到了一次难遇的机会,文化部派老金去当时的民主德国拍戏,这部戏是由世界各国多位有名的演员一起合演合拍的,中国派了他去,自然他很兴奋。他作为一名汉城出生的中国人,两岁随父母回中国后,出国的机会并不多,解放前他虽然到处跑,但那也只是他爱好旅游和打猎。
解放初期他就担任一些行政工作,除了1953年赴朝慰问外,再也没有出国,不像我经常出访,因为我拍戏多。我庆幸也许能给他带来生活的转机,又会使他像参加劳模会时那样开朗。
他把一切都准备就绪,他的所有服装都是他自己精心设计,重新又复习了外语,他说他是代表中国出去的,应有自己的水平,我也相信他在表演方面、仪态方面不会丢中国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