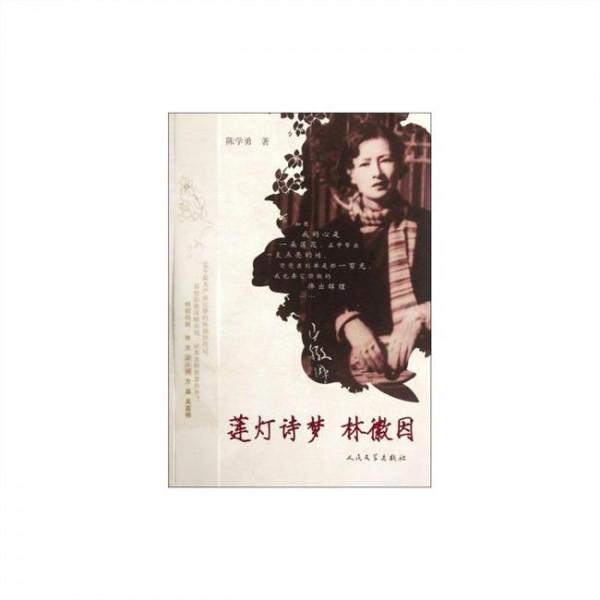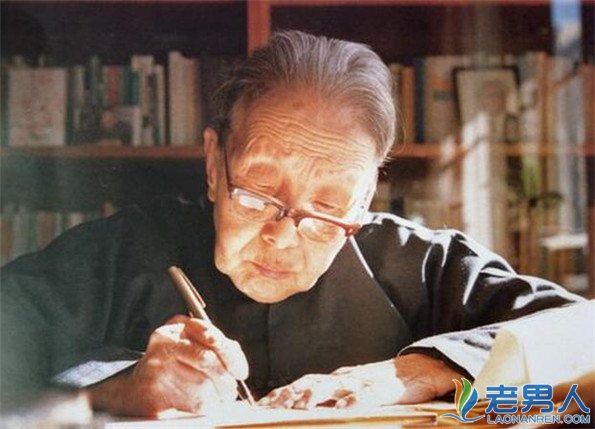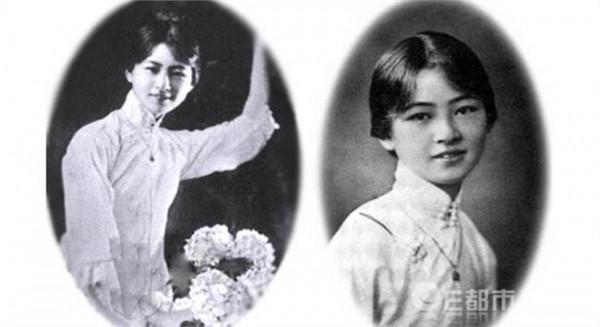李健吾林徽因 陈学勇:林徽因与李健吾
九三四年初林徽因读到《文学季刊》上李健吾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非常赏识,随即写了长信给李健吾,约李来她家里面晤。那时林徽因已经享誉文坛,她的“太太客厅”正闻名北京全城,许多人以一登“太太客厅”为幸事。
林徽因的这种方式约见,多用于未相识的文学青年,如萧乾,故似有勉励、提携的意思。然而年龄上李健吾只比林徽因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相当活跃的了,文学上算得林徽因的前辈,不知他们见面时是如何一番情景。
反正两人的订交起始于此,以后都在“京派”圈子里引为知己,尤其是李健吾,对林徽因推崇备至。林徽因借鉴意识流手法创作了小说《九十九度中》,有保守的大学教授竟然读不明白,为此李健吾写出了与小说同题的评论,热情称赞林徽因:“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
”并指出:“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
”李健吾关于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的评论,成为李健吾式文学批评的一个代表文本,并选入多种有关林徽因的书籍。
抗战八年,林徽因避居西南后方,李健吾则蛰居沦陷的上海,虽音讯阻隔,但阻隔不了李健吾对女作家的惦念。当误传林徽因已经病故,李健吾在《咀华记余·无题》中表达了对林徽因和其他三位女作家的这种情感。他说:“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令我心折。
……一位是从旧礼教冲出来的丁玲,绮丽的命运挽着她的热情永远在向前跑;一位是温文尔雅的凌叔华,像传教士一样宝爱她的女儿,像传教士一样说故事给女儿听;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最后一位最可怜,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说的是已经证实死了的萧红。
”“但是,我前面举出的四位作家,死的死(据说林徽因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活的活。都在最初就有一种力量从自我提出一种真挚的,然而广大的品德,在她们最早的作品就把特殊的新颖的喜悦带给我们。……我不想在这里仔细分析她们四位,因为她们每位全值得我奉献一篇专论。最像一个典雅的中国人的是凌叔华,然而最伟大的却是丁玲,萧红的前途应当没有穷尽,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
大概是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李健吾确切地得知林徽因尚在人世,喜出望外,立即又专为林徽因写了一篇《林徽因》,收入多人合集《作家笔会》(沪上“春秋文库”的一种)。这篇文章几乎不为世人所知,连编集关于林徽因文字相当齐全的《窗子内外忆徽因》也未编录。好在《林徽因》一文不长,此予全文抄录(原书似有字、词脱漏,但不便臆测妄加):
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
为什么我这样关切?因为我敬重她的才华,希望天假以年,能够让她为中国文艺有所效力。在中国现存的知名女作家里面,丁玲以她的热和力的深厚的生命折倒了我,凌叔华的淡远的风格给我以平静,萧红的《生死场》的文字像野花野草一样鲜丽,直到最近,杨绛以她灵慧的文静的观察为我带来更高的希望。作品没有她们丰盈,才华的显示不是任何男友所可企及,然而命运似乎一直在和她的倔强的心性为难。
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
她恰好由山西调察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现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
现在,到什么场合寻找她的音容?她和丈夫,抛弃闲适的客厅生活,最先去了昆明。这一对身体残弱的学者(中国唯一的古建筑学家,“金小玉”的范永立就借用他的职业。)艺人,有的是饱满的精神。我最初听到他们的信息,是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
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当留在祖国吃次苦。他们享受惯了荣华富贵,如今真就那样勇敢,接受上天派给祖国的掌握份苦难的命运?林徽因在她大勇若愚的忧患中,贫病中,倔强中,没有写出类似下面的美好的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