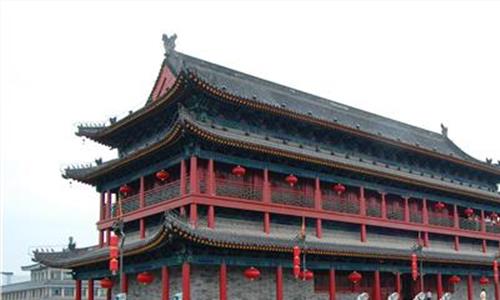余世存农耕文化 重温数千年农耕文化 余世存重解《易经》
10年前,余世存撰写出版的《非常道》另辟蹊径,以短小的碎片式文体挖掘了历史的边角料,拓展了书写近现代史所采撷的材料范围。《非常道》出版后引起社会的关注,被誉为新世纪的“世说新语”,余世存因此在学界声名渐起,本报文化周刊曾在《非常道》出版后对余世存做过专访。
10年来,余世存一直在寻找古典中国意义上的“信仰”,最近几年更是一直在艰难的转型中摸索。今年3月,余世存推出《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让他最终找到了归属感,事实上,它也是余世存找到的世界观。
被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千百年来,各种解读层出不穷,也因为其晦涩难懂产生很多误读,以致争议不断。长久以来,对于《易经》的解读呈现出两种倾向,要么被复杂化,要么被玄学化,甚至被认为是算命的书。余世存正是意识到此,而埋首于《易经》的研读的。
“要了解中国百家学问的本体,必然得回到《易经》上去。在诸子之前,在书经、诗经、礼经等等之前,我们文化只有《易经》,那样简单又包罗万象。《易经》是怎么来的?《易经》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易经》如何用?《易经》是否真的能够预言天下的命运,或者说,《易经》是否规定了人的命运……这样的问题很长时间里折磨着我。”余世存说。
余世存取伏羲先天卦序,按照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演绎体例,第一次系统地做了《易经》的现象还原,证实《易经》是三代以至先秦中国人的日用卦历,是人们生活的百科全书,他说:“《易经》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是我们先民对太阳、月亮以及大自然和生活世界的观察、思考和总结。
离开了生活的情境,一切想当然的训诂、猜谜、发挥都是自造新说。”并由此探讨了卦时与现代人的关系和命卦与个体命运的关系。在研究了北半球中外上千名人的命运之后,余世存对“时间”有了新的理解,渐渐发现易卦与现代人文之间的契合。在他看来,易经的重要,使得中国文化的每一代传人,在一生治学中都得交一份答卷:自己如何注易。
本书中,余世存试图对《易经》中的现象进行系统的还原,唤回读者的乡村生活记忆,重温中国二三千年的农耕文化。书名以《大时间》为名,意在唤醒人们的心灵,进而实现天、地、人自由和谐相处。
对话余世存
《易经》本来是普通人的学问
文化周刊:您过去的写作大多与历史、思想有关,从《非常道》到《老子》、《家世》,这一次涉足《《易经》》,转变还是有点出乎意料,为什么会对《易经》感兴趣?
余世存:对我来说,写《大时间》完全是一个意外。《非常道》以后,我的研读范围仍在历史领域。除此以外,平时看闲书,或说自己思之再攻之的领域,大概就是《易经》了。《易经》吸引我,是我读书从现代回向传统的必然结果。
从西学转向近代史、转向先秦诸子,最后发现,要了解中国百家学问的本体,必然回到《易经》上去。《易经》本身是关于变化的、不确定的学问,是一个巨大的富矿,对一切认真的人都会敞开其资源。除了老子、孔子、墨子等儒家道家的圣贤们从《易经》那里获得思想资源外,千百年来的中国人不管喜欢不喜欢,都会面对《易经》,从历朝历代解读《易经》的书籍就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当然,我的转变可能会让读者有点意外,从《非常道》到《老子传》、《家世》、《人间世》等等,再到这部解读《易经》的《大时间》,仍可以看到我的个人特征。有人称这是“余氏版本”的《易经》,你也可以看到其中有大量的知识点,有开放的态度,有现代人的问题意识和安身立命的探索,我想这些东西可算是我的书都具有的特色。
文化周刊:《易经》为群经之首,但两千多年,《易经》要么高居庙堂之上,是士
大夫们经世致用的学习教材,
要么流于世间,成江湖术士算命的依据。《易经》为什么会引起差距这么远的解读?
余世存:不管是在传统时代,还是在现代社会,不管是学院派,还是江湖派,各种各样对于《易经》的解释,其实都和普通人无关。但《易经》本来就是普通人学问,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
意思是说这些典籍里的名词,看起来艰深古奥,其实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用语,显然,这句话说的是三代以前,三代指的是夏商周,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对于天文历法都很熟悉,而天文历法,恰恰是《易经》一个很关键的立足点。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代,或者说两次著名的文化演变事件,使得《易经》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成了少数人专有的知识。一个是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在这之前,人人可以关乎天文,而绝地天通其实是把天文历法的知识收归史官和巫师所有,普通人不再能接触到它,此后有了专门研究天文的人,也就是观天象的人,这类人后来也被妖魔化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转折,是文王做八卦。八卦有先天后天,文王做八卦,是后天八卦,此后后天八卦取代了先天八卦,所有的研究者、学习者学的都是后天八卦,它对中国后来的政治、文化、乃至传统价值的建立,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直到宋代,先天八卦才被找回来,研究者也才又一次有了不同的视角。
这两个变化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文化的防火墙,以后的人们,都是在这个墙里面翻来覆去的折腾,不管是学院派,还是江湖派,不管是神秘化,还是考据化,其实都在慢慢地把原本最简单、最普通的《易经》,变成了普通人再也看不懂听不懂的学问。
《易经》不是算命书
文化周刊:在您看来,现代人对《易经》存在的最大误读是什么?
余世存:我们对《易经》的最大误读是把它当作算命书了。《易经》是我们先民对太阳、月亮以及大自然和生活世界的观察、思考和总结。举一个例子,我们很多人把《易经》的文辞看做是先人钻烤乌龟壳和用草算命时留下的辞句,但其实占卜的卜字是先民立杆测算太阳的阴线,巫字也是两个人商议天文地理的形象刻画,用现在的话,那是对话的逻各斯,但我们把卜、巫字都巫术化了,诬名化了。
易经的时间是农历。我们的农历是太阳历和太阴历的结合,二十四节气就是明证。说易经不用阳历系统,也是对易经的一大误读。
文化周刊:您说《易经》是人们生活的百科全书,简单说,有点像天文历法的书,您这样结论的理由是什么?
余世存:《易经》的起源其实非常简单,我们中国人把宇宙万物还原为阴阳,一切都是阴阳的排列组合,阴阳决定了象、数、义、理,阴阳的类聚分化记忆演化出了大千宇宙。在上古时期,最为稀缺的知识无过于天文历法,所谓时间空间的规定,正是农耕社会收成的法宝。
《易经》对应于中国农耕文化构建的宇宙模型,既是对时间空间的捕捉,又是对有限生物的必然规定。我们今天所谓的挂历,在先人那里,其实就是易卦的卦历。某种意义上说,《易经》是三代以致先秦中国人的日用卦历,是人们生活的百科全书。
“小时代”里需要“大时间”的概念
文化周刊:解读《易经》,书名取为《大时间》有什么含义吗?
余世存:《易经》是个大时间的概念,它是中国文化在它的童年时代,偶然发现的一个宇宙模型,一个最初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因此它的所用非常广泛,小的方面来说,让人趋利避害,大的层面来说,让人学会如何看待人生,更高的形而上的层面,让人学会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小时代”里,缺乏的正是对于大时间的概念,在这个小时代中,每个人关注的其实都很有限,以时间而言,一个人会考虑的可能仅仅是三五年,很少有人去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比如说一百年,在一百年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一生,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易经》它源起于对天文地理的观察,落实为生命世界如何与天文地理达成有机的和谐。这是寻找生命个体跟时间、空间即这个世界最深刻的联系。这一功德,至今仍对现代人有启示。这是我把书命名为《大时间》的原因,不论过去现在,真正通《易》的人,都过得很自在、坦然,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人生坐标,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究竟要怎么才能活得好。
文化周刊:您的这本《大时间》和其他解读《易经》的书有何不同?
余世存:这本《大时间》,跟以往解读易经的书不太一样。以往的解易著作,基本上遵守文王后天卦序,我的直接取法伏羲先天卦序。一般的解易著作,重在卦辞爻辞的考据、训诂、猜测,我的解释直接把卦辞爻辞跟农耕文化的日常生活挂钩,很多在专家学者和前贤看来是片断的占卜辞句,在我这里多是一个个的故事。比如夬卦是夏至前抢收决战的故事,大过卦是农村房屋大梁的故事,涣卦是秋天洪水的故事,晋卦是立冬后供暖的故事……
过去的解易书,不曾把卦当作卦历、当作时空来理解,我这本书不仅把卦跟一年365天相联系,而且每一卦时空的特征、每一卦时空出生的人的特点都有涉及,并用北半球上千名人来参证。易经六十四卦,就像六十四片树林,一切枝节花实,都与人心相通。比如说鲁迅是遁卦,一生都在弃绝;胡适的人生跟坤卦相关;塞林格是颐卦人,隐居一生且教化众人;物理学家霍金,其人身存在方式即是“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