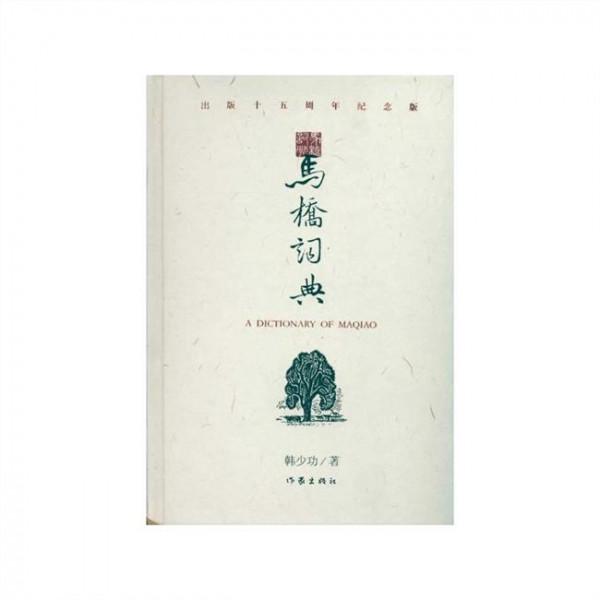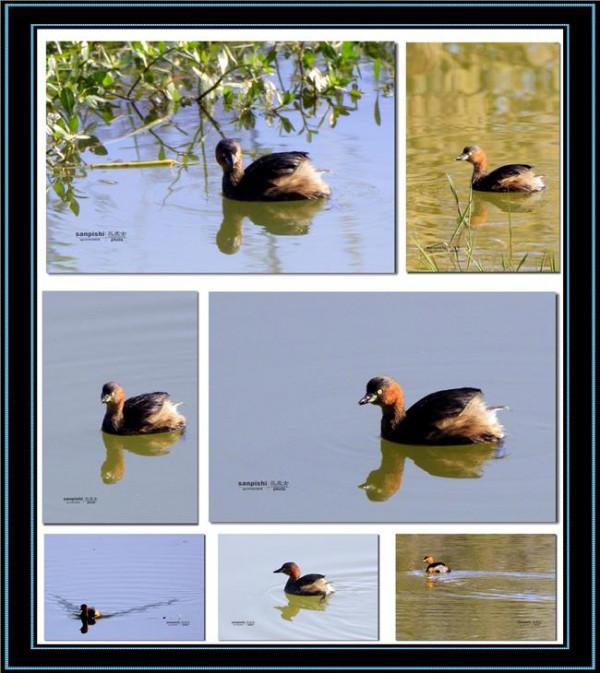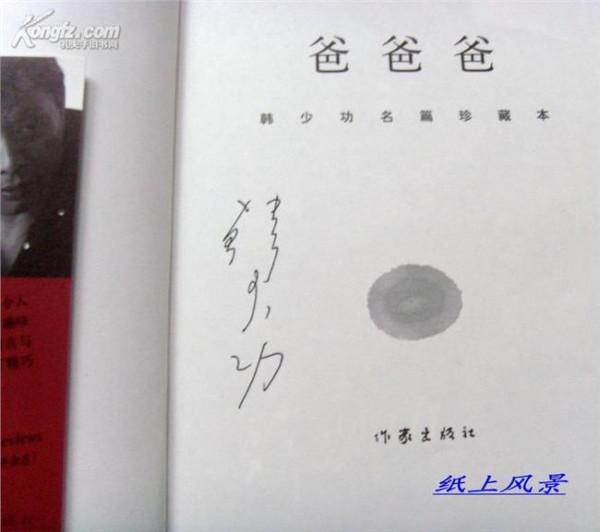韩少功夜晚读后感 韩少功《马桥词典》读后感
用两天时间,仔细读完了这本书,强化了个人对小说的偏见:小说要么读好的,要么干脆不读。好的小说读完,合上书的几天后,你都会记忆犹新,并在想为什么作者会写成那个样子,之后又不由自主地说原来或许就应该这样。
《马桥词典》是一本不露相的、反讽的、打着词典旗号的、有民族志学者眼光的、形散神不散的杂文式小说。入迷的时候,你甚至都忘了自己到底是在读虚构的还是纪实的作品。
作者在自序中所说的“一个人其实是隐秘的群体”,给读者留下了其“谦谦君子”的印象。因为写书那时的感受、成稿付梓的感受以及在时间和市场中接受检验后的感受,就作者本人而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当他冠之以自己名字时,同样对自身、对读者、对作品都赋予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他的惶恐就是有道理的,这样平视的姿态,让读者愿意甚至主动参与到他所讲的故事当中。
对于时间的感知,我想韩先生与唐诺先生,是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的,说不定会碰出什么好玩的想法。马桥人特有的说话方式、思考方式、生活方式无不与他们对于时间是循环往复的感知有关。
线性时间观的人即外地人(马桥人言之“夷边人”),到他们那里,或许会有种对未知民俗“蒙昧地”嘲笑,因为他们说的话是不着调的,不客气地讲,是没有逻辑的、低俗的。但是,文中的“我”,作为知青之一,带领身后的隐形读者们“真切地”在马桥借宿了一段时间后,以一个有血有肉的、全息摄影的记录者身份,让“我们”和“他们”能够对视、交流、然后理解。
仅仅是一部小说,就能让你在形色各异的中国乡村窥见一斑,更不用说专门的纪实作品的浩瀚与深邃了。真实的中国在话语中流淌,多面且多义,只有穿梭于不同的文本之间,你才能发现自己置身何处。
关于中国的乡村,从许多国内外书写者的视角出发,你能感受到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内部极其复杂的差异性和如获至宝的融通性。比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再比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何伟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德国人雷克的徒步西游记《最长的路》等,前者让作为个体的你“身在异乡为异客”,后者让作为群体的你身在本乡为异客。
你眼中的世界、你听说的世界、你身外的世界,都是一块虽留有前人脚印但仍待你自己开垦的荒原。因为相比时空的无限性,人不过转瞬即逝;如何让自己平衡于“地球没你了照样转”与“六十几亿分之一的特殊存在”的认知协调中,恐怕答案就在你自己的词典里。
《马桥词典》从名字上就首先吸引了我,会让人忍不住地翻翻看到底写的是什么。这本书于我这个不爱看小说的人来讲,读起来是挺十分方便的,因为有关键字索引。这也是其特色所在:一个词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背后是一种乡愁,一种乡愁揭橥的是不同人的生存状态。
先不论韩式写法是原创还是抄袭(有人说是模仿《哈扎尔词典》,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我的书架上还有一本《米什沃词典》,那么请问,他那二十世纪的西方回忆录到底谁仿写谁呢?),就内容的原创性而言,他绝对是第一作者。马桥的活文化在他的笔下跃然纸上,这一趟接地气的南方乡村游是非常值得诸位看客赏心悦目的。
人化的世界即符号的世界,它不同于客观存在的世界,这一点从方言和普通话中就可以体会。马桥方言中比较有意思的几个词儿,举几个例子。比如“散发”是一种诗意而尊敬死者的“死亡”。
这个词让我马上联系到离散函数求极限时不能直接用洛必达法则,由于其是不连续的、无序的,是你无法限定范围的不可控状态。人的死亡就是这个实体已经停止了呼吸,而代表这个人的名字却能够一直存在于话语中,这种死也没死但却已死的状态也是你无法限定范围的不可控因素。
散发一词就很好地说明了作为有机体被分解、灵魂已熄灭、甚至偶尔还能在空气中感受到人在消失时化为尘埃的那种飘逸,让生者在谈论死者的时候不用沉重的心情也可以表达哀思。
还比如“流逝”是一种顺畅的、仿佛听见水声的、有动态感的“马上”。谁都知道逝者如斯,但直接来形容时间飞快这种转瞬即逝可感知的用法,恐怕可奉马桥人为嚆矢。就算马桥只是南方一个普通的村庄,但它的许多字眼都是有文献可查的,也即有历史文化底蕴的。那这是不是变相地说明了社会是在此时此刻、无时无刻不被构建的?
一说到文化构建,你可能会想到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这样的概念。马桥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语言海洋已经露出了其无意识偏见冰山的一角,因为从书中可以看出,马桥传统是重男轻女的、反智恶美的。
马桥人把结婚形容为“放锅”,一阵见血地说明了婚姻的本质,即外姓人在男方家搭伙吃饭就表明是这个家的一份子。这个放锅的动作,既说明了女性嫁人后的首要任务是料理家务,也说明了已婚女性只能吃夫家姓的饭。
在马桥人的结婚礼仪中,见证放锅奇迹的后生们有对新娘“摩拳擦掌”的特权,这难道是列维.斯特劳斯所形容的已婚女性在氏族间流通作用的体现?这同大众传媒一般,先营造好了刻板的、温柔忠贞的家庭主妇形象,然后给人们提供对号入座的标准,不想被排挤的就按照常规来,如果稍微有点“反常”,那么请你自备救生圈准备淹死在口水里。
许多辱骂女性的词不一而足,一般人用脚趾头都能立刻想到,因为该类词汇是如此有爆发力、让女性一听即毙。各国国骂的词汇大多与“下面”有关,但是咱们的国骂中,除此之外一定还要加上个女性对象,更甚者,还有女性站在男性角度用“婊”攻击其他女性,这实在是让人费解的事情。
再看“小哥”这词指的是姐姐,其中的问题在于“小”和"哥”俩字都没有女性特征却用来形容女性,表面上看是对女性的尊称,其实从作者的叙述中可以得知,“马桥女人的无名化,实际是男名化”。
至尊者无名是由于忌讳,至贱者无名是由于多余。马桥语言中,女性词全面取消。“这种语言的篡改是否影响到马桥女人们的性心理甚至性生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变更了现实”,作者很难深究,但是他看出了这里女人的男性化。
“从表面上看,她们大多数习惯于粗门大嗓,甚至学会了打架骂娘。一旦在男人面前占了上风,就有点沾沾自喜。她们很少有干净的脸和手,很少有鲜艳的色彩,一旦梳妆打扮被人发现,就觉得羞愧万分。
她们总是藏在男性化的着装里,用肥大的统裤或僵硬的棉袄,掩盖自己女性的线条。她们也耻于谈到月经,总是说‘那号事’。‘那号事’同样没有名谓。我在水田里劳动,极少看见女人请例假离开水田。她们可以为赶场、送猪、帮工等等事情请假,但不会把假期留给自己的身体。
我猜想她们为了确证自己‘小哥’一类的男性角色,必须消灭自己的例假。”女性在马桥一般是没有话份的,连耳朵都不配当,只配在旁默不做声纳鞋垫。马桥有个字叫“格”,权且理解为人格,女人的格是依附于男性的(父亲、兄长、丈夫),做了不体面的事情被他们叫做失格;还有字叫“煞”,即表达某种敬畏之感,通常只形容男性,而作者认为一个同任何人都熟不起来的叫万山红的女书记最适合这个词。
她有独立于并高于普通男性的格,并且在马桥一直守身未嫁,所以说在马桥,“格是一种消灭性别的祸害,太高的格对传宗接代大都可能大有威胁。”作为类似的物种,高质量的剩女剩下的原因有没有可能和万书记一样是因为自身逼格太高而独善其身的?这值得商榷,但以上都是用男性的符号秩序来定义女性地位的语言事件,直观且深刻。
还有形容女性长得漂亮的词叫“不和气”,也即红颜祸水那个意思。长得漂亮就会遭女人嫉妒、引男人垂涎,为了不锋芒毕露,“世人只有随波逐流,和光同尘,不当出头的木椽,往自己脸上抹泥水,才有天下的太平。
”这个故意装丑的逻辑,在马桥那里大受欢迎。铁香作为本义送上门的妻子,最后却和当地又穷又混的小子私奔后死掉的经历,让马桥说三道四的女人们“几个月来分担着一种团体的羞辱”,因为她失格了,而且失掉的是大家同为女人这个群体的格。
她们把她的遭遇称作一种叫做宿命的“根”,就如曹雪芹自嘲为“溷藩之花”。之后,作者分析了铁香在我看来具有激进女权色彩的行为,她其实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她相信,一个男人只有爱得发狂,才会在绝望之余产生仇恨和暴力。
”是不是这样,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还有一个孩子意外被日军炸死然后自己疯掉的女人叫水水,她凭借自己“梦婆”(神经病)的身份在乡里还小有名气,根据人们将其奉若神明的态度可知“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如小孩、女人、精神病人等,在很多人心中虽是可怜的弱者,但在一些命运关头,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
”这或许是《到灯塔去》里在理智探索途中迷失的拉姆齐先生在被其需要时呼唤、不需要时呵斥的拉姆齐夫人那里总能找到慰藉的原因吧。
马桥人用“神”来形容一切违法常规、常理的行为,“在这里,人们最要紧的是确认人的庸常性质”,像铁香、水水一类的“奇”女子,当然不会辜负当地人给她们的赐字。
那些太守妇道的女性,也只配个“嗯”字。这些词儿都表明了马桥人对伍尔芙式的神经质与歇斯底里的厌恶,也表明了他们对于超出自身经验范围外的事物的不可言状的恐惧。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笔下的非人类:两棵被马桥人深恶痛绝的、有奇幻色彩的、名叫“枫鬼”的树;一只和知青关系很好、不被马桥人待见的、吃里扒外的、最后被“我”抛弃的、名叫“黄皮”的狗;一头只有当地岩匠志煌才能驯服的、见到红色就不失野性的、迫于舆论压力死在主人刀下的、名叫“三毛”的公牛。
这些生物,都不难让人想起电影里《走着瞧》那头给知青生活带来笑与泪的倔驴。
作者之所以这样拟人化或者说感性的写作,我认为有以下两个目的:一来强调符号与事物的区隔。二来说明话语即权力。作为客观存在的树、狗、牛可能遍地都是,无非是四腿健壮的动物和枝叶繁茂的植物。但作为被人赋予意义而存在的符号指称物——那棵树、那只狗、那头牛,人对其的态度可根据自身预设而有所不同。
马桥人迷信,狭隘,自大,便把各种他们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无法接受的意义赋予没有符号能力的非人类(其实也包括一些接受语言狂轰乱炸的本地受害人);知青眼中的这些非人类没有神力,没有鬼气,只有灵气,有和人类同作为地球居民的权利。
最后树被砍了、狗被唾了、牛被杀了都是村民无意识的集体狂欢,这些非人类在村民的话语事件中饱受摧残,而一些被流放到符号边界的人类如地主的大儿子盐早、遗世独立的人马鸣、外来人口希大杆子、被人怂恿的知青黑相公、“不守妇道”看上“离经叛道”三耳朵的铁香、犯了嘴煞后来精神恍惚的复查等,无一幸免于难。
就连话份很足的村长罗伯在死后也落下个“红花爹爹”的暗示其有同性恋倾向的称号,在任时底气很足的书记本义退休后那种人微言轻到连儿子上街讨饭都招人嫌的境地,真的不难想象现实中那些恃强凌弱、陌生到惊惧的嘴脸。
人言可畏,是人们惧怕话语编织的符号中伤了自己最真实的写照,而不是对失势失语者故作施舍模样的怜悯。
当然,作者在一阵能够引发读者思考的深沉过后转而用文笔来卖萌,使有些句子读起来十分形象动人。(1)描写天气:“伏天,街上比乡下要燥热得多,热得好没良心。”
(2)描写有人背对着你睡:“他给我一条背脊,没有任何动静,不知是睡了,还是没有睡着。...”
(3)描写拜访陌生人:“他不在家,我在大门口咳了几声未见回音,只好怯怯地被几级残破的石阶诱入这一洞尘封的黑暗,在一团漆黑中有灭顶者的恐惧。”
(4)描写庞麦郎似的那种皮屑:“我的鼻尖碰到了一团硬硬的酸臭,偏过去一点,又没有了。偏过来一点,又有了。我不能不觉得,臭味在这里已经不是气体,而是无形的固体,久久地堆积,已凝结定型,甚至有了沉沉的重量。这里的主人肯定蹑手蹑脚,是从来不去搅动这一堆堆酸臭的。”
(5)描写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当时有几个后生用看到割下了城里的灯泡,准备带回去挂在自家的屋梁上,说那家伙到了晚上就亮,风都吹不黑。”(有学者讲自己在台湾出租车上听到的”笑话“: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军人接受台湾时,他们在一处墙壁上看到一个叫做”水龙头“的东西,轻轻一拧就可冒出水来,觉得神奇就把龙头弄下来,直到换岗到另一个地方就往墙上塞,却奇怪为何没有水流出来。
于是台湾人对大陆人就形成了”保守落后“的刻板印象,以至于去年”茶叶蛋事件“火到不行。同理可证,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愚昧无知“的刻板印象也是源于传播内容的妖魔化。)
凡此种种,都说明作者超然的态度:“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价值缺位的。”...“如果说语言曾推动过文明演进,那么语言也可以在神圣光环之下失重和蜕变,成为对人的伤害。
”...“一旦某些词语进入不可冒犯的神位,就无一不在刹那间丧失了各自与事实原有的联系,无一不在最为势不两立的时候浮现出彼此的同质性:它们只是权势,或者是权势的包装。”那么我想,关于文革的故事,特别是1948这一年,对于书中不同的人来说,“也许还有另一部历史?”
伍尔芙说“读书,只为自己高兴。”嗯,也只有自己能为自己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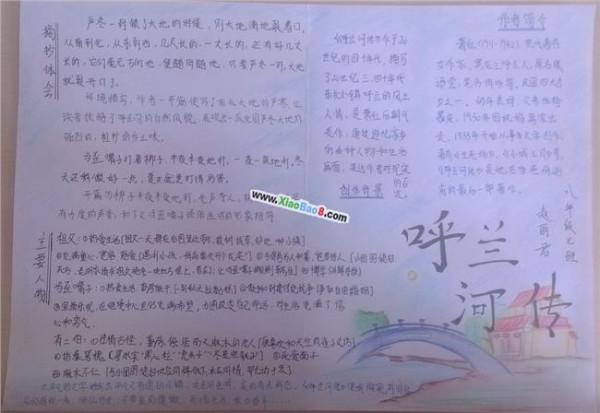












![韩少功日夜书 [2013上海书展新书推荐]韩少功:《日夜书》](https://pic.bilezu.com/upload/b/60/b609466569629a51e0fffcc4ae83b7a7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