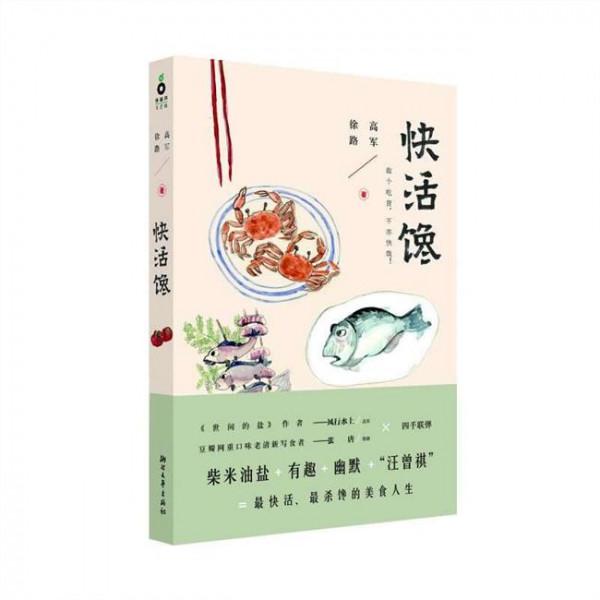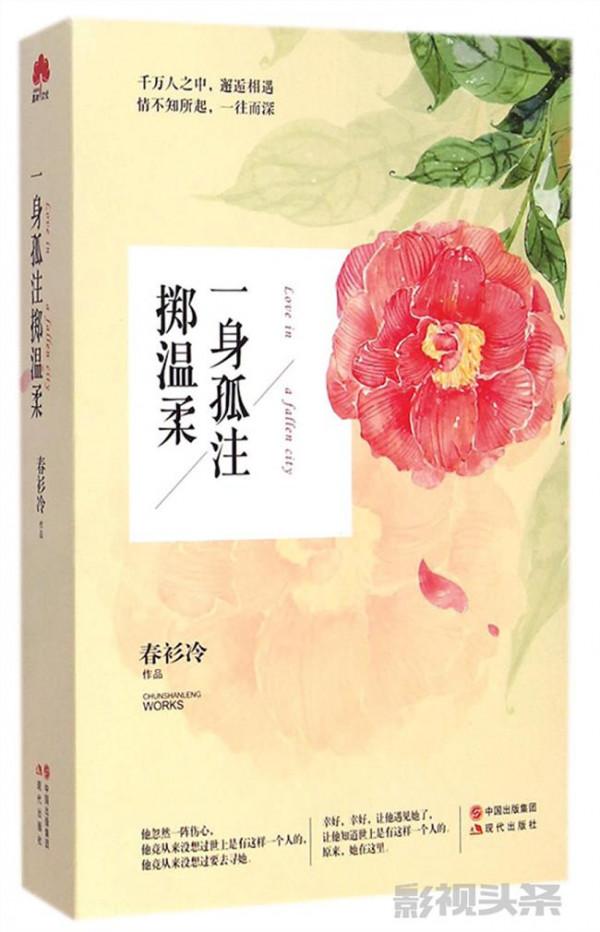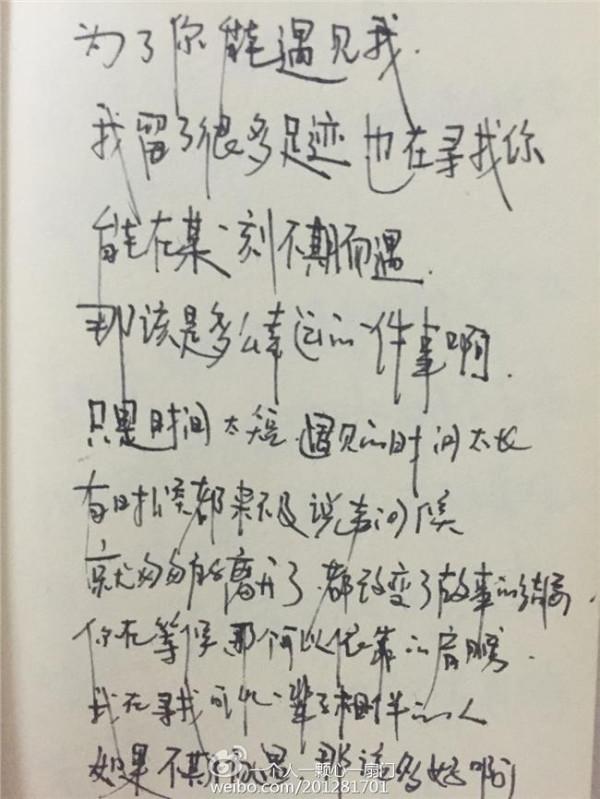高军风行水上 序:《书枝的文字》/高军(风行水上)
书枝让我给她的新书《八九十枝花》写篇序,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我很喜欢书枝的文字,她写的东西我是篇篇看的,文章中写的那些乡村生活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书枝的老家跟我的老家离得不远,书枝是安徽南陵人。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南陵住过一年多时间,对南陵这个地方很熟。
南陵县夹在芜湖与泾县之间,一半是圩区,一半是山陵地带。山区多松、竹、油茶之属。圩区地势较低,主产水稻也养鱼,那里多湖坝水塘。夏秋季节好发大水,一发大水的时候一季庄稼就没有了。
站在高处一望,白浪滔滔的。等水退的时候,就把家里的渔网修补好,坐在鸭蛋壳样的鱼盆里,到水里放卡子打鱼。我在南陵上班的时候也经常到附近水塘去钓鱼,连竹竿也不用,就这样把鱼线揣在口袋里,顺着塘埂到处走。
初夏的时候菱角从水里长出来,铁锈色里透出点绿意,我在水塘边的丰草里坐下来,把线甩到水里。线在水面稍稍迟疑一下,然后沉到水里。四周是植物的清香,有一种水鸟叫“格登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叫起来,“格—登”“格—登”,越发显得天地之间很静。
这时候有下学的小姑娘从塘埂上走过来,穿着红衣服,扎一支“朝天一炷香”的辫子。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棍子上系了根绳子,绳子另一头缚住一只蜻蜓,边走边玩。
看到有人在钓鱼,就绕了几条田埂走过去。这是沈书枝吗?所以我在看书枝在《春鸟》中写帮爸爸送酒,把酒壶盖子掉到水塘里去,自己趴在水塘边捞,立刻想卷起裤脚帮她捞上来,不然回家她爸爸会打她一顿的。 我问书枝为什么想写点东西?书枝很老实。
她没有反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东西?”这就是书枝乖的地方。她老老实实地说,原来也是尽看别人写书,忽然有一天心念一动,这有点像《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
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这样就动起手来。这一写不要紧,就写出这样一本好书来。 至于怎么好,书枝不自信。我就激她,她却以为老风在说大话。这就像我自己看一张画,画的意思满满的都明白,可是一时赞不得一个字,只好打机锋:过去我们老家水还干净的时候,初秋的时候,在水沟旁边拔了野菊扔在水里看它怎么随着水流旋转,拔完了就忘了。
一边玩一边沿着山路往家走,走着走着发现野菊花也跟到脚边走。有时它在前头,有时它在后头。
书枝的文字就有这样的好法。所以我跟书枝说,我写不到你这样绵密,也写不到你这样静。好在我可以随时放下,要不写就不写了,就像林教头跟洪教头比棒。现在我是被扫在臁儿骨上,撇了棒,一拐一拐自投庄外去了。
其实书枝书中写的乡村已经没有了,这样说可能有点武断,换一个说法:书枝写的乡村社会正在消失,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比如她写的《打猪草》,现在乡下猪圈都是空的。传统的养猪方式是要蚀本的,百把斤的猪要长一年还多,“饲料猪”几个月就出栏了,然后拉到城里给人吃,最后把人吃得跟猪一样。
现在乡下过了正月青壮年人都走光了,以前到了农忙的时候还要回来把秧栽了再走,到收割的时候再回来。现在不行了,农忙也不回来了。
我们那边每家田亩少,种地划不来。农药、化肥、种子成本一除,种地累不说,还要赔本,哪有进工厂打工好。到月发工资,风不透雨不漏的。在城里混好了,就扎下根了。也就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成功”了!“混好”了!
乡下成功的标准可以量化的:在城里买了屋,过年时候开车子带了一家大小回祖宅看看,穿着光鲜,见到本村的长辈记得撒烟,抽不了夹耳朵上。然后记得用打火机给人家点上,闻一闻,喷香,哎呀!三狗逼,你现在混好啦!
都抽上中华烟了。其实三狗逼也就买了几包充充门面,没人的时候还是抽抽“红黄山”,偶尔充充面子,家里也没有金山银山。 村里年轻人见面说不上几句话,都掏出iPhone 5上网的上网,发短信的发短信。小孩子说要看牛看猪,缠得烦了就问娘老子:“村里还有养牛的吗?”父亲照例坐在向阳的地方抽烟,弹弹烟灰说:“现在谁家还养牛?养牛也没有人拉出去放草。
”书枝书中说到放牛,放到没路的地方把路让给牛走,人下到沟里把绳头甩过牛背,这是行家的话。
没放过牛,哪里懂得这些?看到她写这一节,我还问她会不会骑牛,书枝说不会,只有牛在沟里吃草的时候,才敢在背上坐一坐。过去乡土社会人口流动性是很差的,村里就几大姓,都是亲戚。逢年过节村子里每家都要跑,不跑就是失礼。
这种人际关系说好也好,春天青黄不接,捧着碗东家借一头,西家借一合,全没问题。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然后扩大到城镇也是一样。进而县,进而省,再进而家天下。所以黄仁宇有一次在哥大上课开玩笑说,如果要他推荐一个中国海关的关长,他指了一指下面洋同学说:“我还是愿意你们去做!
”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回去就必然要掉到这个熟人网络里面去。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来找你办点事,你还不给面子?再不给,回家把你老爹绑了一道来说情。
现在乡村人口流动起来了。村里人要往镇上去,镇上人要往县里去。到了县里怎么办,往省里去。再想好,只有往北、上、广或者国外去了。到了国外一看,原来他们过的是村里的日子,无非一家一幢楼,楼前面种花,楼后面种菜。
我们这代人对土地不亲,其实亲了也没有用,地也不是咱们的。现在给我一块地,我也是干瞪眼着急。过去要求一个男性庄户人,有这样八个字,“抛粮撒种,犁田耙地”,这是最基本的,还要会看节气,会理水路。
到什么节气要泡稻种,要下秧,差一天也不行,到秋天就要差好几成收获。所以我们只能在城里混着,城里也有城里的好。城里人家一门一户,住三五年不知道对门姓什么情况常有,不像在乡下仗着都是你的长辈,问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呀?”“你看瘌头都从外面带媳妇来家过年了,你什么时候带个人来家呀?”“徐四贵听说当副县长了。
上次回来好大排场哦!”你可能心里暗暗地骂,徐四贵当副县长关我鸟事!但你脸上还不能带出来。
尽管有那么多烦心的事情,有的人从乡下出来也许就很少回去。 但说来也奇怪,睡上睡觉做梦,还尽是乡下的事情。一个人走夜路,四周萤火虫飞来飞去。或者拉着牛到山上去,风把植物银白色的背面都吹翻了过来。
云一忽儿在山的东边,一忽儿又到西边。好的写家在乡村里生活过就有福了!多识鸟兽草木姓名。渐长渐大以后,她或者他要到一个大地方去。文学家可以在纸上构建一个镇,一个县,一个不存在的都市,像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镇,再大一点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
但一个具体的村子不好写,形容落形迹。文学上太具体会令人失望。书枝创造的是村子之外的元素,花花草草,人、水、风和鸟鸣。其实我对书枝具体是南陵什么地方人并不感兴趣,我不会呆到去这个具体的地方去看,我生怕看了会失望。
假如水不如书枝说得那么清,风不像她说得那么芳香怎么办?田里的菜蔬也没有她说得那么好吃,怎么办?把她打一顿吗?那样书枝该多委屈,书枝会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属于自己的村庄呀!
《八九十枝花》是书枝创造出来一个完美的乡村,包括夏天咬人的蚊子都算。《露露》在这本书当中算是最沉重的了,但控制得要算恰好。快要掉眼泪的时候,忽然又收上去了。雅克•桑贝 (Jean-Jacques Sempé)画过一张小画。
一个小孩子在海边堆沙堡。堆好了,等浪来。打翻,再筑。再打翻,再筑。后来浪不来了,自己一巴掌把沙堡打得粉粉碎。其实写作就像孩子筑沙堡,勇于筑,也要勇于打破。
书枝写句子都干脆,比如:“这几天南京都有雨,起初落一整天”。《清明》中:“我们若去给爷爷上坟,跪拜之后——”句子光秃秃的,有时绵密起来就绵密得要死。我跟书枝说:“书枝我看得出你拳法的师承!”书枝等着我说。
“你读过废名吧?”书枝说:“哎,废名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我说:“我也很喜欢,以前到处向人推荐。好像喜欢的人不多,废名有时留的空白太大。这脚踩实了,那边还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这句话说完,我和书枝都笑起来。
这本书出来了,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书枝前几天说现在有点不敢看。这种情绪相当于“近乡情怯”,她不像我老脸皮厚的,我现在翻自己的书常常像绿妖说的那样拍拍自己肩膀说:“老头子,干得不错!”现在我们都来拍拍书枝肩膀说:“小姑娘,写得不错。我们都看好你哦!” 高军(风行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