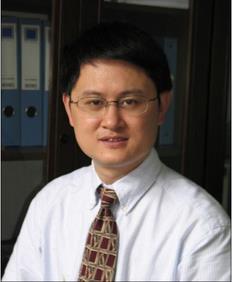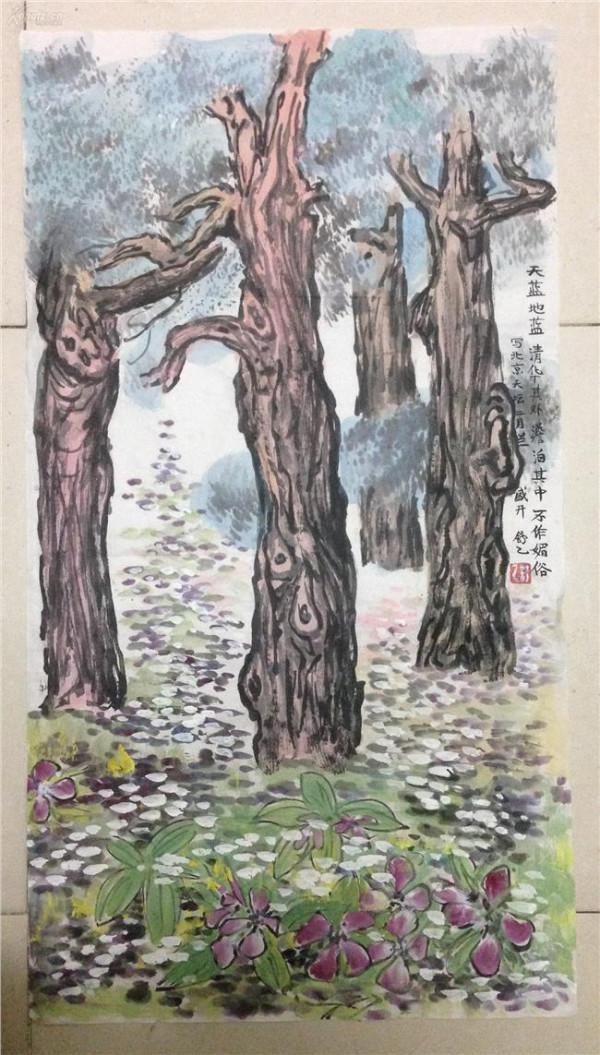舒乙死了吗 还历史的真实 舒乙谈老舍之死
编者按:“《浩然访谈录》用大量篇幅谈到发生于1966年的老舍之死。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老舍先生的家属认为浩然在这篇访谈录中出现了三个大错,把攻击矛头对准了老舍及其亲人,并要求浩然对此事负责。下面是《天津日报》对老舍长子舒乙的访谈。”
记者:最近,有《浩然访谈录》见诸报端,其中用大量篇幅谈到发生于1966年的老舍之死。浩然当时是北京文联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据他讲,老舍夫人胡青在得到老舍去世的消息后,反应冷淡,说“死了就死了呗”。您那时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人,您是否记得当时的情况?
舒乙:浩然在说谎。我的父亲老舍先生在“文革”中投太平湖自杀,对我来说刻骨铭心,我怎么会忘记呢?老舍先生投湖的前一天,受到某中学红卫兵的摧残与侮辱,当晚是我母亲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家,并且帮他脱下血迹斑斑的上衣。他投湖之后,我赶到现场,后事也是我和母亲办的。我最了解真相。
老舍先生去世那天,家里人一直找不到他,急得要命。因为前一天,老舍先生不能忍受红卫兵的摧残与侮辱,与他们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家里人担心事态向更坏的方面发展。没有办法,只好由我出面代表老舍的家属去找周恩来总理。
那时已是晚上,国务院接待站一位极负责的军官接待了我,很客气,说我们也很焦急,请放心,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你们。我刚到家,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就到了,说总理已知道此事,他非常着急,说会尽全力去找。而此时,我们还都不知道老舍先生已经去世了。
去国务院的时候,我把老舍先生的血衣穿在里面,外面又套上了外套,尽管天气炎热。到了军官面前,我打开外套让他看,衣服上血迹累累。这足以证明,家属对此事的焦急程度,情形绝不像浩然所讲的那样。
当时在太平湖,文联一个造反派头头在,他以前与老舍先生和我们家很熟,见到我竟然问“你叫什么名字”、“出示你的证件”,之后就走了,只说了句“赶快处理后事”。他的司机以前给老舍先生开车,平时也很熟,临走时司机悄悄跟我咬了一句耳朵说:“这个地方有野狗”。
他是嘱咐我要守好父亲的遗体啊。我十分感动。那时很惨,天完全黑了,并且下起大雨,我不能离开,也没办法同家里人联系,只好一个人守着父亲的遗体,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下起雨来,我在雨中落泪。那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后来在一篇散文里我写过,“不知是雨在落,还是泪在落”。这才是历史事实。
记者:《浩然访谈录》中还提到草明。据浩然讲,那天,红卫兵让老舍站在高台阶上。红卫兵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要美金。大伙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摘牌子时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是草明的“揭发”导致了红卫兵对老舍更大的迫害。对这件事,您是否了解?
舒乙:这一点确如浩然所说。草明为了保护自己,挑动红卫兵斗老舍,理由是“他拿美金”。老舍说我在美国是自由作家,“拿美金”是必然的,很正常,为了生活。但那时的红卫兵很幼稚,认为拿美金,就是拿敌人的钱。草明明白这一点,可她故意这样说。
许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很含蓄地指出过草明的事。她立即找到作协,她不仅没有自谴,却还要组织出面保护她。那时鲍昌是全国作协的领导,他跟我谈,希望我不要再说,维护草明的面子。我说:“既然你来找我,我以后不再提。”后来又有人访问草明,她很害怕谈此事。现在一谈就推脱自己,虽也说她是有责任的,但轻描淡写。
记者:许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看待那时候的当事人呢?
舒乙:对于老舍之死,草明和浩然都是有责任的。当时的事情是历史的事件,作为有责任的个人,我认为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忏悔与反思。而不应该有这样的发言。浩然的访谈在北京有很大的反响,许多作者都表示抗议。
当时浩然是革委会主任,他怎么能一点自己的责任都不谈相反说家属反应麻木,我们要控诉他,甚至要起诉他。实际上应是他心里有鬼,以这篇访谈掩饰他个人的责任。他应当自谴。作为老舍的家属,我们很宽容。我现在原谅草明,她已经老了。
去年老舍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很大。老舍先生的地位明显上升,除了人们发现了他文学作品中新的内涵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人品好,有非常浓的人情味。还有一个就是他死得太惨,死得有气节。他离家出走准备走上死路,出家门之前突然问我妈妈“家里还有多少钱”。
他是从不管钱的,对钱财心中完全无数。又问“够孩子们养家糊口吗”。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动但多余的问题,因为那时除了小妹妹还在北大念技术物理之外,3个大孩子都已经工作多年了,经济上很独立,我们从来不找他要钱。他是一个极关心孩子的父亲,有老式男人的责任感,是一种亲情促动他想到这样的问题。
总之,浩然这篇访谈录有三个大错:一、用造谣的方式直接攻击了老舍夫人,这和当时造反派为掩人耳目而推脱责任制造各种老舍之死的谎言如出一辙;二、浩然甚至攻击了老舍先生本人,那个时候,老舍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本人的文章有时都发不出来,他只有沉默,甚至搁笔,这是历史悲剧,怎么还可以指责他对年轻人不热情;三、对某些人来说,对“文革”深入批判不够,于是浩然和浩然们至今没有任何自谴和自我批评的能力,他们对“文革”这场民族大劫难往往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地向上一推了事,成了一个极可悲的通病。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并不想针对某个人算历史账,但我们要还历史以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