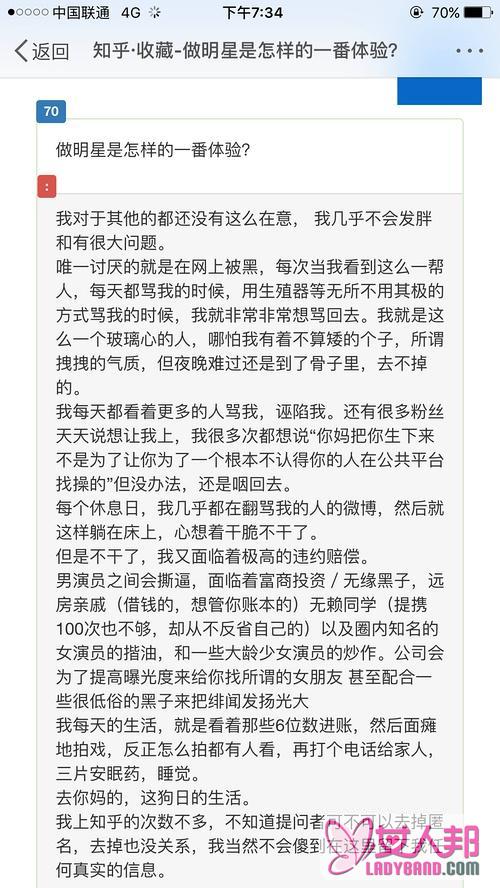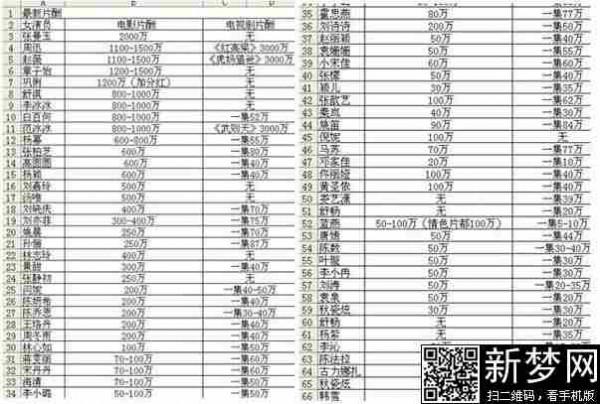痛哭抑郁发飙自杀……做明星这一行究竟有多焦虑
前几天朴树在录音棚现场演唱,节目已经临近结束了,他说他还想唱一首歌,最后选了这首《送别》。
“情千缕,酒一杯,声声离笛催……”
谁知歌未毕,曲未尽,朴树泪却先流了。
埋在心里他始终忘不掉的是2011年,他的吉他手程鑫患上了胰腺癌。朴树本来就不志在赚钱,几年来不多的积蓄都花给友人治病了,助理提醒他说:你卡里的钱根本就不够了。他说那就去签公司,卖身嘛,跟救人比起来真不算什么。
几天后友人还是走了,最终留不住,只能送别。
这也不是朴树第一次泪洒舞台了,上次是在郑州演唱会现场,朴树唱《我爱你 再见》,这是一首情感浓郁的早期情歌,曲调舒缓却又令人心碎。
听起来像是在送别自己的爱情。
曾经大家都觉得周迅和朴树是最般配的一对,他们很有默契,能够读懂对方的脑回路。可以一起在凌晨三点打电话给高晓松,探讨一个在我们普通人眼里很无聊的问题。
难怪高晓松会说:“他俩都是燃烧自己的艺术家,凑在一起,太灿烂了”
如今是“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不灿烂,很现实。
朴树住在北京郊区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他指着身后的房子说,买下这个房子,是“唯一的幻想”。
平时如果不宅在屋子里,那就一条大裤衩,一双人字拖,骑上电马儿,晃晃悠悠的,有那么股仙气儿。
用的手机还是诺基亚,通讯方式一般靠邮件,唯独有辆奥迪TT,都开了十几年了,修理费都快赶上车价了。
这些他觉得都没什么,什么事是无法忍受的呢?比如要上春晚的舞台假唱,他当时想立马拍屁股走人。最后经纪人苦口婆心的劝他,他身后还有一大批人的努力,不能就这么走了,让别人的努力付诸东流,他才在那年春晚上唱了《白桦林》。
他就是会为这些事焦虑得要死,一张专辑做了3年,录了一半觉得不对了,不录了。专辑不是他要呈现的,不录了。
音乐和情感就是他最看中的,音乐他倒是擅长,但除了写词唱歌,他表达情感的方式很匮乏。
朴树唱歌,第一个打动的人总会是自己,全情投入的歌唱就是他情感的出口。
但如果离开了旋律的依傍,朴树真的是一个不会表达情感的人,他能做的就是像这样,带着少年的泪水,一直唱下去。
明星们身在娱乐圈,焦虑当然是无法避免的组成部分,逃避也好,流泪也罢,到底也还是要解决的。
周迅会在明年出演赖声川的话剧《雕空》,搭档则是陈建斌。
陈建斌是个剧场人,站在舞台上的魅力确实没话说。但周迅是第一次演话剧,赖声川倒也不担心:“她不会有问题的,对。”说这话的时候,站在身旁的丁乃竺面带微笑,频频点头。
周迅的演技自是不必多提,饱受大家的认可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毕竟像《画皮》里的狐妖小唯、《风声》里的顾晓梦、《如果爱》里的孙纳、《李米的猜想》中的李米……每一个都是拿得出手的角色,我们对周迅演技的信任,就像不纯净的氢气遇见火会爆炸那样理所当然。
然而对于周迅自己来说,焦虑还是有的。
比如周迅知道自己不是演员科班出身,她觉得自己对“演戏”的认知是不够宽广的。
周迅最早入读的是浙艺的舞蹈班,这个舞蹈班的主要目的还不是培养专业的舞蹈演员,而是为文化馆培养老师,所以招生的各项要求都不是很高的。
她会去兼职拍挂历,一些当时拍过周迅的摄影师后来提起,周迅的那双眼睛就像是黄鹂鸟的嘴,是会唱歌的。
这些有着周迅纯真眼神的挂历发往全国,才让知名导演发现了她,充满了幸运与偶然。
正是这样的出道经历,让她在内心里埋藏着一份不自信,一份谨慎的缄默。于是周迅发起了《表演者言》这个节目,用最严肃的方式讨论表演,在与老戏骨的交谈中去重新学习与反思,借此拓宽自己的认知。
可以说,《表演者言》既是开给现今影坛的一味药,也是周迅打破自己对于演戏固有认知的努力。
第一期黄渤做客,黄渤谈到表演时语言的重要性,说自己学配音的时候会用两三个月,就只练习大哭大笑,每天练晨功就是“哈哈哈”“呜呜呜”。
听到这儿,周迅惊讶却克制的小声“啊?”了出来。她对科班演员经历的系统训练有多陌生,可见一斑。
再到冯远征,说周迅给他印象是“笨方法”,不否认同样能找到撞击观众心灵的瞬间,但这就是学院派对于野路子的看法。
段奕宏的观点亦然。
周迅问他为什么理性至上,段奕宏沉下身子告诉她,感性的灵感迸发,不是你这个段位的演员该满足的了。
周迅看着他没有接话,但段奕宏的这句话,应该足以帮周迅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了。
《表演者言》之于周迅的意义其实很像“行走的力量”之于陈坤。
据说陈坤还在上学的时候,有次失恋了,心情十分烦躁。他打算立刻找到女朋友问话,哪怕吵一架也行,毕竟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嘛。结果一路走到女友家,发现自己的心情已经平复了。
这次经历给了他灵感,拍完《画皮2》之后,当他觉得自己与演员这个职业很难相处的时候,他发起了“行走的力量”。
陈坤组建了一支10人的大学生队伍,电影刚一杀青他就飞到拉萨和他们会和。高海拔行走,最重要的规定是,行走途中要“禁语”,就是不能说话。因为对于陈坤而言,他要的就是一场苦行僧式的修行,要在克制中才能找到他想要的平静。
然而这个过程并不平静,特别是在刚开始。
行走的第二天一行人顺利翻越了色拉乌孜山,大家的心情都不错,下山途中开始有学生嘻嘻哈哈的聊天。陈坤气得说不出话,走到没人看见的地方,把手中的登山杖对着石头砸的稀巴烂,对着摄影机大吼“不许录!他们以为我是请他们来旅游的吗?”
他甚至会当着全队的人,对负责饮食却出了差错的小弟大发雷霆“能不能干?不能干就滚!”
我们从没见过这么暴躁的陈坤,像是一只被压着变形的气球,最终还是炸了。炸了之后,他又开始了长长的反省,承认那些事做的都不对。
行走中会经历各种事,会经历意外,可以洞察自己,这些也都是修行的一部分。
他晚上敲了敲门,走进学生们的房间,坐下来先道歉,然后掏心掏肺的讲述自己成长中的苦难,得意,迷失。这些让学生们感动得泪流满面的话,其实也是陈坤在反省给自己听。
陈坤小时候家里穷,小朋友来找他,可以从纸糊的窗户外伸手拍拍他,因为那层纸永远都是烂的。最落魄时,晚饭的青菜都可能是菜市场捡回来的。以至于冬天里一碗刚煮好的泡面能让他幸福得冒泡。
于是他有感而发:“幸福就是憋了两个小时尿后才去上厕所的那一瞬间。”
但是这一切,都在他演了《金粉世家》并且越来越红之后改变了。
他最初也兴奋,也膨胀,但同时,童年的经历又让他自卑,拧巴。他的职业像是暴发户,突然的物质实现所带来的冲击他感到恐慌不定,他做不到欺骗自己说:这就是我应得的。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
他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做一件能让自己平静的事。于是从禅定到公益活动,最后他发起了“行走的力量”。
这会让人想起村上的《当我谈跑步时,谈些什么》,试着做一件机械的,枯燥的,重复的事时,其实是在跟自己对话。
胡歌在2017年初也接受过一次《人物》的采访,那时他刚被《人物》评为了年度演员。问起他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胡歌回答了两个字:“改变”。
这转眼一年又末,回头看来,胡歌的这个愿望既可以说实现了,也可以说落空了。
前两天他再次接受了专访,谈及贯穿了整整一年的话题——留学,倒也确实去留学了,但这更像是一个赶鸭子上架的乌龙。
年初的胡歌说他就像是他在澳大利亚俯瞰的那块艾尔斯巨石,因为他觉得他和巨石一样,都很孤独。
《琅琊榜》和《伪装者》的双黄成功,让胡歌瞬间回到了2005年《仙剑》播出时的热度,但也就仅此而已。
他喜欢用2005年攀登启孜峰的经历打比方,原以为登上峰顶心情会非常激动,但他发现其实并没有,这些所谓的收获、成就感给他带来的快乐只在认真攀爬的那一小步里面存在过。
这样的心态会让胡歌在外人眼里看上去始终是谦卑的姿态,但于他自己而言,他觉得自己走到位置和设想中的老是有差距。
所以他一直对读书这件事有一个情结,上学的时候因为拍戏经常耽搁课程,虽然老师们都报以谅解并以胡歌为荣,但胡歌觉得或许继续读书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出国留学应该是计划了很久的,但具体的时间可能并没有定好。番茄台的这一出送别礼更是让他意想不到,还真就差搞个儿童合唱团深情地为他唱一首“长亭外,古道边……”了。
他的种种表情都在表达诧异,只不过最后也还是接受了。
他试图把留学作为一个出口,但当他剃了头发留起胡须走出去一看,依然全是注视着他的人。
于是等到回了国,他独自骑上摩托去色达,五明佛学院,去青海湖骑了一圈,并以此度过生日。也算是完成了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对比起来留学只能算是一次失败的逃离。
改变和留学,是胡歌为了更宽广的视野所做的努力。戴上头盔在夜晚骑行,则是为了排解焦虑。
当然,你有焦虑,我有焦虑,谁没有焦虑?
梁朝伟可以临时中午去机场,随便搭上一架有缘分的航班,如果飞到伦敦,就一言不发的喂一下午鸽子,晚上再飞回香港,当没事发生过。
那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