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专栏清洁的美味 马金莲专栏:清洁的美味
我们这些生长在山里的孩子,小时候都很淘气,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上树摘杏子捣鸟儿爬上屋檐掏麻雀。把鸟蛋或者刚出蛋壳光溜溜的小麻雀抓在手里看稀罕。每当这样的时刻母亲准会拿着推耙子追着打我们。她们的说辞很严重,说女子娃从小玩了没毛的雏鸟儿,长大后卧的浆水容易发臭。一个做了女人的人,一辈子在我们西海固生活,你手底下总是卧出一缸接一缸的臭浆水,那你的处境估计就不会怎么受人待见,至少你和你的丈夫和孩子们要一辈子都没有好浆水吃了。
那时候浆水是我们日常生活里不可缺少的吃食。浆水算不上粮食,也不是蔬菜,但是在我们清贫的山居日子里却是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吃面的时候,不管是秋粮面还是小麦面,不管是擀面条还是削片儿、撕拨糊、馓饭,因为缺乏蔬菜,只能是清水锅里煮洋芋条儿,然后把面下进去。然后滴进去眼泪一样的几滴清油,放一撮子盐沫子。白汤寡水的饭,往往很难下咽。拿什么调剂味道和颜色呢?浆水。
浆水装在瓦缸或者瓦罐里。平时用一个麦草杆子缝制的圆盖子遮盖着,做饭的时候用勺子舀出半盆儿来,切一根葱,锅烧热了,放一点油,油冒烟了,把葱花扔进去,立时爆出刺啦啦的脆响,放一点盐,一股很清脆的香味顿时扑鼻。这时候把浆水倒进去,烧滚了。等饭熟之后调进去,酸酸的,饭的味道立马不一样了。浆水里漂浮着萝卜叶、芹菜叶、白萝卜条儿等,有绿有白,那洋芋饭顿时就不会单调乏味了。
我们日常吃的更多的是洋芋碎饭儿。洋芋细条和细长三角形的或者菱形的面叶子滚在一起,调上白汤绿叶的浆水,那一种香啊,干了一天活儿的人端起碗来,埋着头噗噜噜就往嘴里刨,一口气刨下个三两碗不成问题。
做浆水是一门技术活,不仅仅需要心灵手巧,还需要勤劳节俭。秋天,收藏萝卜的时候,把碧绿的叶子从萝卜头上切下来,用连根拔起的冰草拧绳子,用草绳子把干净、整洁、品相好的萝卜叶子串起来,一大串一大串,挂在树上,挂在向阳的墙根下,木橛子上。在风吹日晒中很快干透了,变得轻飘飘的,成了干菜。这时候就可以收藏进仓库里。等到卧浆水的时候,解一串干菜下来,开水锅里煮熟了,换凉水泡。把白萝卜切条儿,煮熟了。然后白萝卜条和干菜叶子,一起放进一口缸或者一个瓦罐里,烧开的水晾温了,投进缸里,再撒几把白面或者荞麦面进去,用擀杖搅散了,盖上盖子。第二天,把下过面的面汤用温开水掺一掺,倒一些进去,搅一搅。第三天再做一次。三五天后,揭开盖子,一股新鲜的酸味扑面而来,浆水卧好了。
浆水做饭吃,既当做调味食物,其实在过去贫寒的日子里,我们是把它们当做主事来糊弄肚子的。尤其泡在浆水缸里的那些菜叶子萝卜条,我们叫做酸菜。酸菜是桌子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下饭菜。尤其吃煮洋芋,或者荞麦面搅团和玉米面、莜麦面馓饭的时候,用辣椒面和清油拌出来的酸菜,简直就是绝佳的好菜。
小时候冬天日子短,口粮紧张,爷爷规定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晨煮洋芋,每人一个蒸馒头。我母亲就结结实实调半盆子酸菜,每个人半碟子,酸酸的菜里,虽然只放了一点盐巴少量的清油和一把干辣子面,但是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实在最养人的食品。
真正养人而让我们一日三餐都不离开的,还有洋芋。洋芋,又叫土豆,马铃薯,山药蛋。我们乡下人的土话就是洋芋。我们这里十年九旱的山地,别的庄稼生长困难,洋芋倒是长得出奇好,稍微有点雨水,就会有个不错的丰收。每一年晚秋,把洋芋挖回来,女人们总是很细心地进行分拣,大个匀称外表干净的,装进窖里,留着家里吃。中等个儿的留一些明年春天做种子。挖烂的太小的被太阳晒得发绿的,堆起来等着冬闲了磨粉。洋芋里含着丰富的淀粉,尤其这秋收时候的洋芋,刚从软乎乎的泥土里刨出来,捡一些表皮粗糙沾满泥土的,洗净了,放进大锅里煮,上面盖着麦草杆子做的草锅盖子,下面用猛火烧,水烧开了,再慢慢用文火。过上一个钟头,揭了锅,一大锅白花花的洋芋全部笑开了花,裂开了饱满的肚子。那淀粉过饱的洋芋,面沙沙,绵软软的,咬一口,满口馨香。如果再就点酸菜,那个香,是我们西海固乡里人最实在的享受。
积存在窖里的洋芋,就成为我们一年四季不能缺少的吃食,日常生活里几乎每一顿饭都离不开洋芋,做饭,炒菜,滚汤,热锅里贴洋芋片儿,摊洋芋丝儿……冬天的时候,大家开始磨粉了。那时候我们村庄里还没有通电。马存仁买回来一台人工磨粉机。
大家兴冲冲行动起来了,家家户户从水沟里担水,洗洋芋,备大缸,开始磨粉。那时候村庄里的人都很热心,一家的事情就是大家的。谁家磨粉大家都会赶去帮忙。几个年轻小伙子轮流摇动着磨粉机的把手,把手带动齿轮,齿轮带着胶皮带子,磨粉机哗啦啦转动起来,有人用大铁锨头把洗净的洋芋铲起来倒进去,随着搅动,洋芋慢慢变成了白乎乎的糊糊,从一个出口冒出来。
这样磨上一整天,糊糊积攒在大盆和大缸里。接着是过滤,沉淀,折腾了不知道多少工序,最后终于迎来了让我们这些馋嘴的娃娃最兴奋的一道工序,下粉。
操作现场由院子挪到了厨房内。一个很大的木头杠子支在了大锅上,烧开的滚水,调进兑放了适量白矾的洁白淀粉里,然后女人们快速地搅拌揉搓着,一会儿功夫揉成了一个个拳头大的粉团。
粉团的粘性很差,稍微一碰就破了,需要一个个丢进开水锅里煮一下,刚煮湿了表皮,又捞出来,在案板上快速地揉起来。揉好的面团一样软和的淀粉,一疙瘩一疙瘩塞进木杠子上的那个圆眼里,一个大男人站在锅台上双手往下压,一束细细的粉条的雏形从木杠子圆眼下的那个筛子状的细孔里吐出来,很长很长,慢慢地落进锅里的开水中,洁白的身子变得柔软无比,鱼儿一样随水摆动。
煮一会儿,熟了,热腾腾捞出来,搭在了早就洗净备好的细长木棍子上,一棍子搭满了,提出去搭在支好的木架子上。一会儿工夫,一院子白花花都是刚出锅的粉条。一股淀粉煮熟后的味道香扑扑的,在冬天干燥寒冷的空气里流动。
我们洗净了小手,趴在木架子下铺的大片塑料布上,总是有搭不牢的粉条滑下来,湿漉漉软乎乎的,放进嘴里大口吃。等忙完了,母亲麻利地将新鲜粉条炒半锅出来,帮忙的每人端起一碗,呼噜呼噜就吃,谁也不用客气,都吃得满头冒汗,都在议论着今年这洋芋淀粉好,这粉条香。
粉条晒干了,却再也舍不得让我们这样奢侈地大吃了,母亲把它们装进袋子,锁进木柜里,只有来了亲戚或者家里念苏热的时候才舍得泡一些吃。
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最盼望的日子莫过于念苏热了。四月初八祖爷爷的忌日,七月十八太爷的忌日,十一月初八大地震的纪念日,十一月十六继太太病故的时间,腊月十六太太去世的日子……不管是宰牛(这样的时候很少),宰羊,还是宰一两只鸡,这样的日子对于我们都是隆重而一直期待的。因为我们一直被日常的简陋饮食维持的肠胃实在是很寡淡,对好吃的东西充满了等待和渴望。不管是宰什么,都需要提前买回来,精心饲养起来。牛羊等拴起来喂,鸡鸭鹅的话需要困起来,用一个大竹篾罩子扣起来,不让它们到处乱跑吃到脏东西喝到不干净的水。喂养的食物,哪怕是一背篼草,半盆子开水搅拌的麦麸皮,也需要洗净了家具,用净水搅拌。饮水也是最干净的。这样喂养上一半个月,牲灵的肠胃里就很干净。
快到某位亡人忌日的提前三四天,母亲换一个大水,担一担水回来,洗一把水瓢一个瓦盆一双筷子,然后把口袋里新磨的一次都没有吃的面粉挖一些出来,搅半盆酵子。第二天,又换了水,开始用酵子起面,淘洗萝卜切菜,吩咐父亲去集市上买一些干果和水果,藏进木柜的暗仓里备用。这几天母亲几乎天天在换大水。我们还在热被窝里流连,母亲已经冒着清晨的凉气,大锅里烧了水,把大盆搬进来,一壶清水洗完了小净,那个圆肚子的瓦罐里已经灌满了一瓦罐热水,扒开塞子,她站在大盆里哗啦啦洗着。洗过大小净的母亲,对念苏热准备的一切食材都管理得很严格,决不允许我们这些脏手的娃娃随便去动。
要炸油香了,母亲一个人完不成,需要叫个帮忙的,早年是奶奶或者某一个婶子,后来姐姐稍微长大一点,母亲就急不可耐地让她参与了,一边帮忙一边及早学习掌握这些女孩子家迟早得学会的茶饭技巧。母亲取一些干面粉在案板上,放适量的小苏打进去,再放一些白糖,倒一些清油,然后把起好的软面从盆子里挖出来揉进去。
这就是兑碱的环节了,是油香能不能做好的最重要的环节,合适的话,炸出来油香金灿灿的又蓬松又好吃;兑不合适的话,油香不光面色不好看,吃起来更是差劲。
难得炸一次油香,又是要念苏热,母亲面色严肃得没有一丝笑意,紧咬着牙弯腰在案板前揉面,然后在柔和的面里掐一小块儿,团好了,放进灶膛里烧熟,掰开了看一看面色,如果又白又蓬松,说明正好,这时候母亲的脸上还是没有笑。
催姐姐快揉面屉子,擀油香。一口小锅里早就开始烧火了,母亲拿一根卫生香,念一句清真言,点燃了,别在锅台后的小香炉里,提起一壶新磨的胡麻清油,嘴里缓缓念一句清真言,然后把油很慎重地倒进去。
开始烧火,热油上泛起泡沫,继续烧,泡沫很多,但是很快就全部消散了,油面归于平静,只有一些细小的波纹暗浪一样在翻涌。油熟了。姐姐擀出的油香一个个摆在那里。母亲对着一个用自己的手掌压一压,手指拢一拢,就是这简单的动作,却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那个姐姐手底下出来的样子有点丑陋的面饼,已经成为一个圆圆的薄厚均匀的面饼,母亲提起切刀,轻轻念一句清真言,在面饼上切出并排的两个刀口来,我们叫做水眼。
母亲把面饼贴着锅帮轻轻下进去,热油顿时啪啪作响,单薄的面饼慢慢地涨起来,一直到长成一个圆圆的厚厚的富态又好看的油香。整个炸油香的过程母亲都紧紧闭着嘴。捞出来的油香放凉了,一页一页摆在一个早就备好的大簸篮里。
油香金灿灿的,看着让人口水暗流,闻着一股清油的香味飘出老远。念苏热所做的一切包括菜、肉和油香,都不能提前吃。我们只能忍着,把馋涎一次次咽进肚子里。其实集市上也有卖的油香,但是和家里做的念苏热的比,那种油香已经远远不地道了,但是附近的汉民朋友还是喜欢买了吃,他们常说你们回民,为啥能把油饼子炸那么香呢?的确,炸油香好像成了回民的一项特别擅长的本事。
念苏热做的萝卜烩菜更是一种让人吃了难忘的佳肴。白萝卜,黄萝卜,粉条子,葱,条件好的话再放点木耳和芹菜或者青椒进去,颜色就更好看了。最重要的还有一样,是凉粉。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流行用豆粉做凉粉,做工很简单,开水锅里搅进去,边烧边搅,一会儿出锅就是了。
那时候是用荞麦榛子糍凉粉。磨荞麦面粉的时候,磨面机里第一道工序下来的粗榛子,赶忙筛一些出来,就是荞榛子了。用水泡软了,放在案板上用一双手掌心慢慢地揉搓。
这个过程真是很漫长,母亲往往需要付出一个下午的时间。直到把所有的榛子都揉搓成一团软乎乎的稀泥,再一次用大量凉水浸泡,就泡出了一盆子白乎乎的面水。这时候用一个面箩,把面水从箩上倒下去,过一遍,再过一遍。
然后烧开适量的水,灶膛里一面烧水,一面把过好的含着荞麦面粉的白水缓缓倒入锅里。这时候搅动是最重要的。母亲用一把特制的长柄木勺子不停地搅动着,在一团缭绕的森森白汽中费力地盯着锅里,并不断地往里面点着热水。
据说这时候要是大意的话,凉粉就会哑了,做出来不是筋斗斗的凉粉,而是一团黏糊糊,不能吃,只能喂狗。可见做凉粉真的是一门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直到看见那半锅清凉凉的白水慢慢地变成了亮白色的粉状物,母亲才敢舒一口气,直起腰来盖上锅盖稍微烧一会儿。
凉粉熟了,舀进碗里碟子里,过上几个钟头,倒出来,碗里的是碗的形状,碟子中倒出的是碟子的模样。用手去摸,青白透亮,看着粉颤颤的,滑滑爽爽的,筋斗,软嫩。烩菜的时候到了,烧热的锅里放点清油,接着把少量辣椒面炒进去,接着是葱花。
炒出了一股扑鼻的香味。把煮肉的腥汤倒进去,烧滚了,接着是备好的萝卜菜等。食材一样一样下进去,等到滚得差不多了,才把切成菱形块的凉粉汆进去。顿时,一口锅里,白色红色黄色绿色,交相辉映,油汪汪,热腾腾,那个香,那个诱人,念完苏热的阿訇满拉们,前来吃油香的亲戚朋友们,大人娃娃,都甩开了腮帮子吃,吃的满头冒汗。
如果谁家娶媳妇嫁女子,宰了牛过大事的话,那就不止这简单的吃法了,这时候上的是浩大昂贵的席面。席面分九碗席,十三花,十五月儿圆。九碗,就是一桌子上九个碗。十三花自然是十三个碗了,而十五月儿圆,从字面意思去理解,那就是一桌子整整地端上去十五碗。后者其实很少有谁家有财力那么去做,一般做的更多的是九碗席,十三花只有娶媳妇时给送亲的贵客和新郎的娘舅家才吃。席面上的碗里都装的是什么呢?也是有讲究的。
准备一个宴席是需要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的。而娶媳妇嫁女儿大操大办的人家也都是蓄积了很久才做出了大决定,所以需要的食材都是舍了血本买来的。还需要厨子。村庄里有一个大厨子,我很小的时候是马福有,等我能混在小伙伴们群里到处撵着看新媳妇的时候,这个马福有已经退出不干了,把本事传给了他大儿子哲布。
哲布圆圆脸,大胡子,见人笑眯眯,天生的好脾气。他很快掌握了父亲的厨艺,并且,据乡亲们评价,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乃父的本事发扬光大并做了一些创新,所以他做出的席面更有味道,更受欢迎。
每当谁家过宴席,牛宰了,肉煮出来全部剔骨,削成薄片,下水全部切碎做进烩菜里。泡好的粉条子、木耳、银耳、切好的凉粉……盆里缸里锅里到处都是。
正式来人之后,一个大火烧滚的锅上架一座蒸笼,里面一层层装着碗,碗里装得满满的。上房里高朋满座,大家按来的时间先后入座,一桌子坐八个人,然后开始端吃喝。一碟子熟好的蜂蜜,一盘子油香和馒头。大家蘸着蜂蜜吃。
吃完了上干果,九个小碟子,里面装着花生、瓜子、葵花等。接着就轮到了重头戏席面。厨房里的蒸笼揭开了,白汽笼罩中,哲布指挥人开始往一个大木盘子里摆席面。四个边角四碗肉,碗里全部是烩肉片,偶尔有个木耳和粉条子,上面是泛着红辣子油的肉汤。
四碗肉的中间分明插进去四个碗,两个碗里是萝卜烩菜,一个上面苫一层肉丸子,数量有限,八个。另一碗上面是酥肉冻蛋。这个酥肉冻蛋很好吃,尤其牙口不好的老人和娃娃最喜欢吃,是剁碎的肉上面打一个鸡蛋,蒸熟后翻过来切成了八瓣儿。
另外两个碗里内容一样,是牛杂碎和木耳凉粉等烩成的汤菜,清亮,爽口。最中间的一碗,叫甜饭。甜饭更是肠胃不好之人的最爱。蒸熟的白米饭,用清油红糖拌了,然后里面压上掰开的红枣、核桃仁儿、花生仁等。
倒扣着端上来,白色底子上镶嵌着红红的枣子和白白的坚果仁,看着就让人顿生口水。尤其那些年大家日子困难,大米是稀罕东西,很多人家平时吃不上一顿白米饭,更不要说做成了这样糯软香甜的食品。席面端上来,盘子不用取,吃完了连同盘子一起端下去。一桌子的席面都冒着热气,只等端菜的人双手一拱,高声说艾色俩目一坤———各位贵客请吃———大家就欢快地抓起筷子大吃起来。
十三花,其实是在九碗席的基础上增加了四碗凉拌肉,一个盘子装不下,用另一个盘子紧随着端上来,分别摆在了盘子之外四面桌角上。中间的那一碗甜饭也被一只囫囵的熟鸡替代了。这只鸡除了头和爪子内脏,别的一件都不能少,完整地端上来,摆在中间一个大碗上的一个大碟子里。随手还会端上来一把刀子,谁需要吃哪里,只需动手卸下来就是。而那个十五月儿圆,这些年我只是听说过,实际却没有机会亲眼见到,所以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娶媳妇的时候,面食除了蒸馒头花卷,炸油香,还要特别增加一种油食,叫油屉子。用的是一种发得半醒的面,把面屉子切成长方形,刀子在上面画出交叉的菱形花样,然后四个角儿稍微捏出一点圆润的尖角,油锅里炸出来,胖墩墩的,样子憨厚,其实不好吃,有点瓷实,嚼不动。油屉子是新媳妇取来后娘家人离开的时候,婆家要装一些干果肉食和油炸品送给娘家人,这时候油屉子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问老人们,他们也说不清楚,反正很多年来大家都这么做,这习俗就流传了下来。
我们做得最好的油炸食品自然是馓子了。平时很少有人炸馓子,一般到开斋节时候才炸。斋月还剩下最后几天的时候,满庄子浮动着胡麻油的清香。炸馓子需要很多人一起合作。我母亲老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首先,油和面必须是最好的,最新的。
认真簸了胡麻和麦子,去磨了。然后买一些调味品,茴香、橘皮、大香、花椒……忽然有一天她和要好的女人们商议好今天给我们炸馓子,一大早我们就洒扫了屋子和院子,家里一排洁净,母亲在锅里熬调面的水。
那些调料在水里熬出来一股很香的炖肉才有的味道。熬好了舀出来晾一晾。白面已经倒在了案板上,给里面打进去一些鸡蛋,倒进去一些清油,开始调制。软硬程度都是有讲究的。调好的面需要不断地压一压,放在一个大桌子上,把竹竿扁担洗净了,两个人在两边不断地按压,直到把一团面压出了韧劲儿,才重新揉光堂,盘进一口大瓦盆里,边盘边用清油抹。
最后用软塑料布苫住大盆,让面醒一会儿。帮忙的女人们三三五五来了,大家都是封着斋的,自然是身上带着大净的。
洗净了手,一个个忙碌起来。烧火的烧火,倒油的倒油,更多的人搓馓子。揭开塑料布,取一团面出来,在案板上揉一揉,很快团出一个圆团,从中间挖一个孔,一双手快速地搓起来,很快那面团变成了一个大圆圈。
很快,大圆圈越来越大,只到搓成很长很长的一圈儿。女人们都有着一双巧手,一边搓,一边还能说话,议论着这面的成色和韧劲,议论着今年的斋月,议论着谁家的撒子炸得最好,真是不亦乐乎。那些面在女人们的手里很快搓成了筷子细的圆棒儿,在案板上一摆,轻轻地折起来,盘出了一个圆满的圆盘。
站在油锅边的人用一双竹棍筷子挑起来,对着翻滚的油锅轻轻摆进去。摆撒子需要很高的技巧,不熟练的人只会捣鼓出一团缠绕的乱麻。
所以站油锅的女人肯定是最有本事的。软乎乎的一盘细面在她手里翻动着,不知怎么就已经在热油里变硬了,变得很听话,先摆开了炸一下,接着两边对折,两个筷子合到一起。一会儿翻个身,一把撒子炸好了。捞出来摆在大盘子里。
撒子的颜色是棕红还是浅黄,还是大黄,一来由油锅的温度决定,二来受调制时候熬的水温影响。大多时候都是介于金黄和大黄之间。一把一把的撒子,最后摞在一起,看着脆生生的,直叫人心里垂涎三尺。我们这些娃娃那一天是不封斋的,因为大人知道我们压根就抵挡不住热撒子的诱惑,多半会连咽舌也给诱惑得掉下来。
所以我们一等馓子出锅,就纠缠着大人要尝尝。母亲也总是很开心,不来指责我们不懂事,用盘子给我们盛一些,让端到另一个房间去吃。
厨房里的空气都是油烘烘热腾腾的,女人们都封着斋,大家的嘴唇干巴巴的,但是一个个很快乐,满屋子洋溢着那种乡邻间的亲密和朴素的情感。终于炸完了,母亲找几张报纸,给每一个前来帮忙的女人包一把撒子,让带回去开了斋尝尝。这样的赠送很有人情味。母亲也总是出去帮忙,也能带回来别人家的撒子。等到斋月结束,其实每一户人家里的撒子中都混上了别人家的,哪是哪家的,估计大家都分不清了。
吃油炸食品、吃席面、念苏热,在一年当中毕竟是很少数的时候。三百六十五天里,更多的是普通的平淡日子,这样的日子需要用最普通的饭菜去度过,尤其那些年,村庄里大家日子都很困难。所以奢侈的日子很快会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在面对着一日三餐的清贫饮食。
日常饭菜,自然是洋芋和浆水酸菜相伴的。那时候甚至白面都是缺乏的。更多的是靠秋粮面来糊口。秋粮面做好了,也是很好吃的。我奶奶就是一个做秋粮面食品的高手。玉米面,被她用开水烫过,捂在热炕上发甜了,蒸在大碗里,熟了之后蓬松酥软,一口能咬掉一大口,甜兮兮的,怪好吃。
糜子面,用开水烫熟,捏成一个个圆粑粑,熟了一口咬下去一个白茬口,不好吃,但是揉碎了,热锅里放点油,倒进去炒一炒,顿时化腐朽为神奇了,如果有白糖放一点进去的话,那种好吃没法形容。
莜麦性寒。磨面之前就要炒熟了,磨出面粉后,用开水烫过,烙出来的薄饼子,快吃是尝不出滋味的,我和姐姐在山上放羊的时候手巾里包一些,坐在山头上的西北风里,慢慢地嚼着干饼子,觉得越嚼越香,一股五谷的阳光的泥土的香味混杂在一起,咽下去了,嗓子后面还残留着一点油筋筋的香味。
莜麦面撕拨糊,是女人们懒惰的时候常做的一种饭。开水锅里煮熟了洋芋条,然后把调好的软乎乎的莜麦面用筷子头一块一块撕扯着拨进开水里。
滚熟了,滚出了一股莜麦的黏性,大人们吃得津津有味,当然还需要配上一大碟子拌酸菜。但我总是觉得撕拨糊不好吃,尤其往下咽的时候,嗓子眼里很痒很扎,有刺卡住了一样。
莜麦面做的炒面倒是很好吃。磨面粉的炒油麦,和做炒面的油麦比,那种炒就潦草多了。做炒面的油麦,需要热锅好火,还需要翻炒的技术,我们家总是奶奶在炒。她用一把很短的木头勺子在锅里不紧不慢地翻动着,一锅油麦噼噼啪啪吵闹着跳荡着,直到全身都冒出褐色的花纹,一个个肚子饱满地胀起来。
抓一把丢嘴里,松脆好吃,满口柔香。这样的油麦拿去磨出的面,就是炒面了。也有人在炒面里添加了作料,晒干的甜根子丁儿啊,炒麻子啊,这样炒面吃起来更香。
炒面可以干吃。我爷爷就喜欢干吃,早晨起来,厨房里儿媳妇的饭还没有做熟,他已经饿了,就挖半碗炒面,用一个小勺子,挖一勺子炒面丢进嘴里,喝一口滚烫的盖碗茶水。然后闭上眼慢慢地嚼慢慢地咽,神情享受而陶醉。
炒面还可以拌了吃。红糖拌了很好吃,没红糖凉开水也可以。用勺子搅拌出半碗半干半柔的小疙瘩,然后慢慢吃,也是后味无穷。荞麦面是秋粮面里最好做的面粉吧,擀面条,搀和一点白面,擀出的面条配合上葱花炝浆水,满院子都是香味;当然有肉的话,不用浆水,炒一点肉臊子,会更香。
荞麦面削片很常见,也是懒人的一种做饭,开水锅里洋芋滚熟了,把一疙瘩面端在手里,用快刃子一下一下削,面片儿飞进开水,滚熟了,荞麦面和水之间具备着天然的亲和性,让面汤糊糊的,吃起来舒服,喝一口回味悠长。
荞麦面蒸的碗坨子,烙的倒锅子,都是很好吃的。荞麦面还能做油坨坨。发好的面里放一点小苏打和白糖(其实我们那时候大家日子困难,白糖属于奢侈品,更多时候化一点糖精水兑进去),搅好了,用手抓一点很快搓出一个小圆圈,在油锅里一炸,一个圆圆的圈儿出来了,颜色多半是深红色,咬一口特别松软,很甜,一股荞麦的余味在舌尖流淌。
荞麦摊馍馍也很好吃,清水刷开的荞麦面,热锅里放一点油,倒适量面汤进去,很快熟了,一张薄薄的摊饼子。凉一凉,切成小菱形,切一碟子腌制的酸黄老白菜,两样相伴着炒一下,这时候才能真正吃出摊馍馍的味道来。
如今,随着日子好转,我们大家也都一日三餐吃上了白面,白米也已经不是奢侈品,那些秋粮面紧紧相伴的日子也都过去了,当我知道如今的城里人把吃秋粮当做时尚和奢侈,我就不由得想起成长岁月里那些清贫又馨香的日子。
随着来到城市里生活,我也渐渐地知道了回族更多的清真美食,比如手抓羊肉,酿皮子,羊杂碎,葱油饼……还有很多。
我们回民做食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讲究个清真。清真不仅仅指我们不吃忌讳的肉,自死的肉,不吃尖嘴獠牙类动物的肉,只吃念经人带着水(至少是大净)宰的牛羊鸡鸭和鱼类,我们还把做饭,哪怕是日常一天三餐,也都看作很重要的事情,做饭的人处处讲究洁净。身上带着水,做饭的过程里,往锅里倒油的时候,下面的时候,舀饭的时候,开口吃饭的时候,都要轻轻地念一句清真言。我们最讲究卫生了,就算那时候在我们山村里,极其缺水,我们的日常饮食却依旧是绝对要做到清洁。今天,当很多人和一个回民同桌吃饭的时候,觉得好奇,你们不吃猪肉啊?大家的理解也仅限于此。其实,我们的清洁意识是从骨子里散发的,是和内心的坚守与信仰紧密相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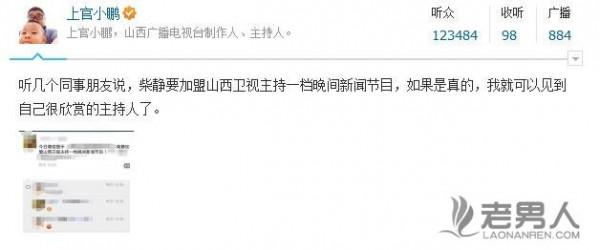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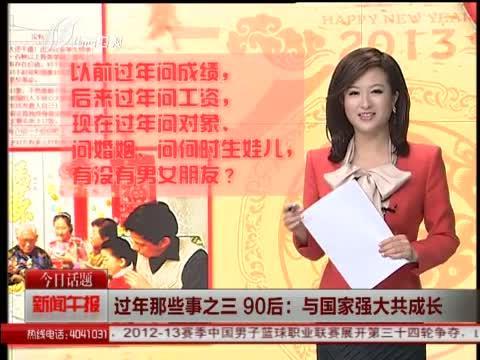





![>马金莲专栏 [山西卫视]《好人就在你身边》专栏“马金莲:当家的女人”](https://pic.bilezu.com/upload/3/26/326ce89c504579ac5992336038d5dd83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