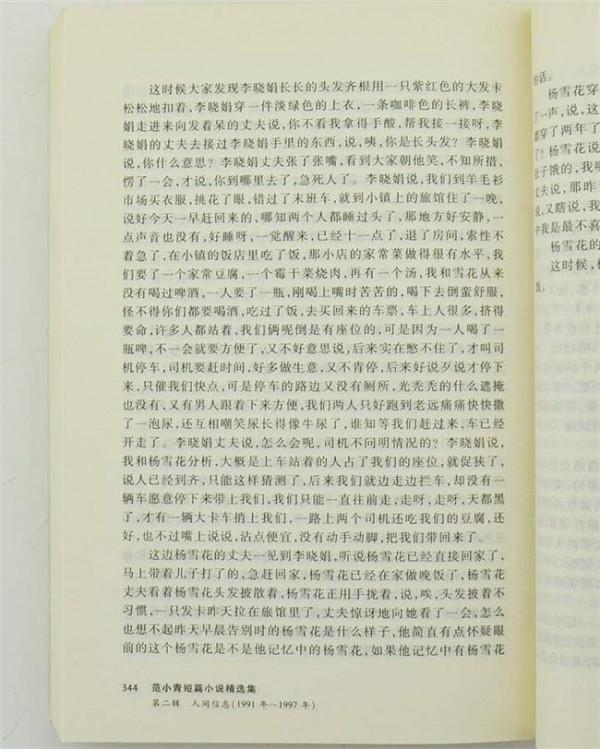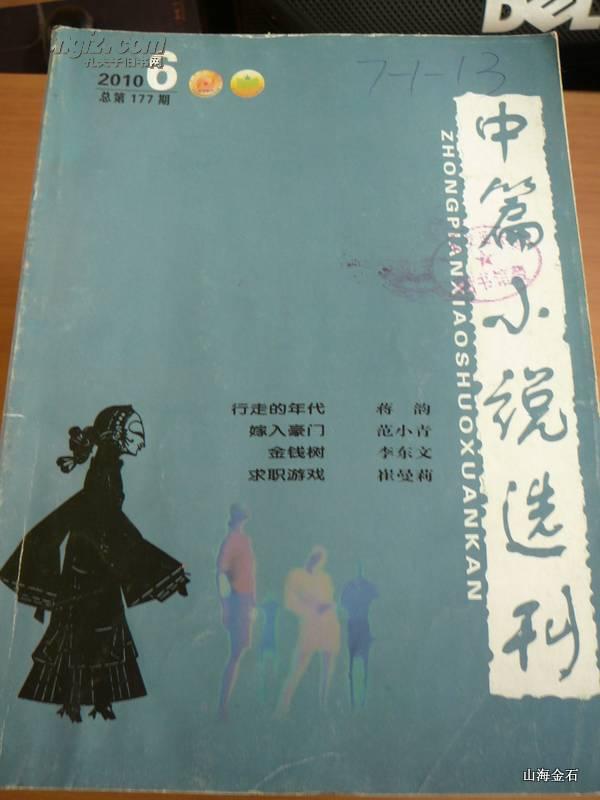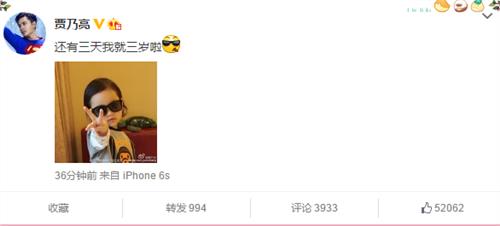范小青佛教 范小青佛理小说主题诠释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与佛教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现当代有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创作,都涉及到佛教观念,或以佛教(禅宗)义理来阐释社会人生问题。如有论者认为,鲁迅的《祝福》、《孤独者》和《野草》,是“依照佛学义理来体验与证悟死亡的意义”;许地山在《命命鸟》、《缀网劳蛛》中的“生本不乐的观念”;废名在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以“传统唯识学和轮回观破进化论”;丰子恺《缘缘堂随笔》数种的缘起性空思想;施蛰存在《宏智法师》、《塔的灵应》中以心理透视的手法表现佛家的忏悔意识与起信观念,都与佛教有关。
当代作家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则以宗教人文为背景,“去氤氲一种历史感,一种心理的和哲理的确定”;央珍的《无性别的神》表现了佛教文化对藏民生活无所不在的影响。
此外,从汪曾祺的《受戒》、熊尚志的《人与佛》,可以触摸人性与佛性之冲突或融汇的主题;从贾平凹的《白夜》以佛教轮回观念为依托的“再生人”形象,和采自搬演佛教故事的“目连戏”中的诸多文化意象,可以窥见作家以佛事对人生的象喻,如此等等,说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确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本文所论范小青的创作所涉及的佛教主题,在上述受佛教影响的作家中,别具一格,显出了风神独具的鲜明特色。
范小青长期生活在苏州,是在吴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吴地的文化环境赋予了她一个作家的佛教情怀和亲近佛学的宗教心态。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有一枝神采独异的奇葩,那就是悠久的佛教文化。它以超凡脱俗的韵味和庄严古雅的丰姿为世人所属目。
自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吴地,历朝历代兴建了许多寺观,梵宇道宫相与古城内外,成为苏州一大特色。唐诗人杜牧对吴地的佛教文化景观描绘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吴郡图经续记》说:“郡之内外,胜刹相望,故其流风余俗,久而不衰。
”。明卢熊《苏州府志》说:“东南寺观之胜,莫盛于吴郡,栋宇森严,绘画藻丽,足以壮观城邑。”故旧时称苏州为东南佛国。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姑苏城内仍留有大小寺庵二百余所,可见其佛事之盛。1997年初春,作为全国首创的佛教博物馆在姑苏城中的报国寺面世。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陈列以及庄严肃穆的佛教氛围,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
佛教在苏州扎下根后就对苏州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缭绕香烟、悠扬钟声是苏州社会最显着的文化标志之一。佛教文化对苏州文化个性的形成,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它熏陶了苏州人、培育了苏州人的心态、型塑了苏州人的性格。
当然,苏州人也并未像寺庙的和尚那样天天诵经,也不像宗教学者那样日日研究佛典。如同大多数求神拜佛的人们那样,他们的信佛,也有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和现实诉求:或祈求福寿两全,或祈求身心康健,或祈求家庭和睦,或祈求升官发财,总之都是表达对现实生活的理想和向往。
其目的是世俗的,是为了现实的幸福,而不是为了遁入空门。如同佛教流行的大多数地区一样,念佛、敬佛在苏州,也不再是佛门里面的事,而是苏州地区社会世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有这样浓厚的宗教气氛,苏州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无不受其影响。佛教义理润物无声地渗入了苏州人的生活,成为苏州人一种深邃的精神力量,乃至心灵的家园。
苏州的佛教文化既有如此深厚的传统,如此浓烈的氛围,苏州作家的创作,自然要受其浸润和影响。一般来说,当代苏州作家的创作,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比较注重作品的文化内涵的。陆文夫曾经说过:“有文化的苏州人不会让她的文化传统在她的土地上消失的”。
他以《小贩世家》、《美食家》、《井》、《围墙》等“小巷人物志”系列作品,通过琐碎的日常生活画面,勾勒出一个个生动的市井人物,在人情风俗、饮食起居的叙写中展现了苏州人的精神心理及独特的小巷文化;年轻一代作家朱文颖不管是在古典题材的《浮生》、《禁欲时代》,还是在现代题材的《水姻缘》等作品中,都写出了一种带有自省和剖析意味的“苏州寓言”;叶弥的作品也是以苏州城市为背景的,《大笑上天堂》里潮湿阴暗的弄堂,《小女人》中的小巷子、秀园旁的杂货店、大公园的评弹、《天鹅绒》里的五窨花茶、鹅绒布料等,都散发出浓浓的苏州气息。
同是苏州作家,同样写苏州,同具苏州文化意蕴,范小青却写出了自己心中独特的“这一个”苏州。樊星在《“苏味小说”之韵》一文中论述了范小青“苏味小说”的特色:“她不仅多产,更以写实中透着空灵韵味的笔触描绘了苏州文化的丰富多彩,表达了对苏州文化的独到理解,在以苏州方言表现苏州民风方面,也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
除此而外,由于佛教文化对苏州乡风民俗的浸染,范小青写苏州,常常聚焦于苏州人的“佛性”。在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中,范小青描绘了苏州市井小民的喜怒哀乐、庸常人生,但在小说“后记”中,却画龙点睛地说:
苏州人没有梁山好汉的气魄,可苏州人有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
自三国时期佛教传入苏州,对苏州民风影响颇大,有人认为苏州人佛性甚笃……我以为,佛性与“韧”,似乎是有联系的。苏州人是很韧的。
这种“韧性”是苏州人骨子里的文化品格。他们气度从容平和、为人处世淡泊随顺、善于自我化解苦痛,无论社会怎么变化,他们都能保持自己平和冲淡的心境,自得其乐地过着自己的日子。这就是范小青所说的苏州人的“韧”。
从心理学上说,“韧”本来是人的意志力的一种优良表现,但范小青却与佛教的观念或日佛性联系起来,表明在她的意识深处,确有一种亲佛的倾向。她的作品不但写出了这种她认为与“佛性”有关的“韧”性,而且涉及到诸多佛教的核心观念。
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身是常,佛性是我”,以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等,在范小青的作品里都有所表现。但她又不虚发议论,空谈佛理,而是将这些抽象的佛理落实到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描写上,落实到解决人的心灵问题、精神问题的旨归上,使人们在喧嚣噪杂的现代社会中,能够保持身心的安定和人格的圆融。佛性在民间本具有普遍的“心性”意义。
生活中有许多烦恼,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然而,人在不断重复出现的麻烦中有没有佛心净土的出现?有的话,那是什么?在短篇小说《瑞云》中范小青将苏州人的“佛性”做了诗意化的点染:吃素好婆因诵读佛经而充实、无畏、淡泊、慈善,她的养女瑞云因为深受好婆的影响而赋有了“佛性”的品格——平静地生活、笑对苦难,虽身残而心境淡泊,又因淡泊而散发出难言的魅力,小说写到后面瑞云石成为了文物,瑞云也渐渐被人们发现了人格之美,更进一步写出了命运的神奇——人与石的命运如此相似。
这里,作家不仅表示了对骨子里“韧”的认同,更体现出作品对心性修持的强调。这一主题,后来在《还俗》、《牵手》等作品中得到了 进一步的弘扬。
世间有很多种苦可以说是始终存在的,苦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世间人生的失望,而佛性的终极意义是对这种失望的一种纠正和补偿。同时在失望与理想之间,以内在的“韧”性直接参与和改良现状令得其乐。《临时的工作》讲周先生一辈子在县文化站当临时工,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有门路的同事都陆续找关系转成了正式工,而他依然如故。
面对生活中的困境,面对物质上的匾乏,他对工作依旧认真负责,对生活仍旧充满了热情。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不在乎临时工身份,在不公正待遇面前也能心平气和,工资低而没有生活保障,他仍刚强笑对。
这正是因他骨子里的“韧性”而达到的淡然达观的精神境界。由此可以看出,佛性的修为其实并不仅仅在“救苦”而在于“施乐”,所谓“乐”,是相对于“苦”而言,是从积极的方面着眼,告诉人们,人生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一个美好善良、丰盛欢乐的世界,完全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于人世间。
“施乐”归根到底就是随顺佛性,乐善好施,不杀不恼,忍心如大地,令众“和合”,消解人的精神苦闷,调解人际矛盾,利益他人,实现佛性。
佛家讲“众生本有佛知见分,但为垢障不现耳。”凹“佛知见”便是佛性,是众生“本有”的,由于被烦恼尘垢所障而不得显现。所以,成佛也就是去除烦恼尘垢而后发现本有佛性。
范小青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以瑞云、慧文、刘主任、周先生等表达“心”的本性是自然佛性,显然来自对人生问题的深切而广泛的关怀,试图从实践上解决人生苦难和烦恼,从理论上探索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本源和人生的归宿。这种创作姿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社会的认同,那是另一回事,仅就其涉及的问题本身,已足以触动人们的心弦,尤其在饱经沧桑的人群中,引发共鸣。
他们坚忍淡泊,他们以苦为乐,在平凡之中演绎生活的伟大,他们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对于浮躁的今天是一种劝善。
这也正是范小青对她作品中人物进行展示和剖析之后要向我们传达的苏州人的“韧”性品格。值得注意的是,范小青的佛理小说所倡扬的佛教理念与佛门僧侣的佛教信仰有着明显不同,它主要是一种与平凡生活水乳交融的人生哲学,是人生经验和佛学智慧的有机统一。
苏州人因深厚的“佛性”而显得淡泊、玄远。但佛家讲“玄远则不测”,不测即“无常”。“无常”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意思。正因无常的客观存在,所以有情生命就处在一种逼迫、束缚之中。“色即无常,此即是苦”。范小青在她的很多作品里都表现了这种人生无常的理念。
短篇小说《城乡简史》,通过一个城市居民不小心遗失的一本家庭生活流水帐在阴差阳错间被一乡村孩子得到,“帐本上的内容,对他来说,实在太离奇,实在太神奇”。于是,一本看似无用的流水账竟然打开了乡村孩子和他父亲的好奇心,使他们为了了解城市生活而毅然离开了故土。作家就这样揭示了“偶然改变命运”和“无用”变“有用”的玄妙佛理。
出版于2005年的长篇小说《女同志》描写了女干部万丽在政治上凭借着自己的“韧”性步步高升的成长历程,聚焦于她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几个上级的微妙关系和与几个女同事的激烈竞争的矛盾上,从而揭示了官场中人如履薄冰的谨慎心态,又游刃有余地写出了作家对于女性与政治的独到思考。
看得出来,范小青是有意与女权主义立场保持了距离的。作为一个“聪明的老实人”(这个说法就很有哲理感),从政显然不易;“作为一个女同志,过于追求进步,总是让人有点接受不了,在大家眼里,一个女人,这么想当官,一定不是件好事情。
”可另一方面,“权力欲不强的女人,别人就会认为她太软弱,没有能力”,真是左右为难(在左右为难之间,就有人生的悖论)。她的不断进步与老领导向问的大力提携分不开,也与老同学康季平的指点密切相关。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来,她的进步实际上更多取决于男人的帮助。而作家有意在最后才点明向问与康季平的舅甥关系,也最终使万丽如梦方醒、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什么才女,什么工作能力强,什么大气大度有魄力,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康季平?因为向问是康季平的舅舅?”这样的恍然大悟耐人寻味,令人感慨:原来追求进步也绝非易事!
原来“进步”不仅需要政治热情,还需要“关系”的照拂!这表达了世事无常,即使身居其中,也未必明了庐山的真面目。
进而作家又在命运无常的主题中揭示了生死无常的佛理。中篇小说《杨湾故事》中写几个中学生在“文革”中挖空心思、争取当兵的故事,但作家的立意却相当玄远。当作家写下“在陈小马这个年纪,常常偏重于‘谋事在人’的唯物论,所以她有信心。
这时候的陈小马还不可能明白‘成事在天’的宿命论中的合理成分,所以很明显陈小马是自信的,同时又是盲目的”这些话时,她也就相当含蓄地写出了“文革”中相当普遍的一种心态:因为偏信“唯物论”(其实应该是“庸俗唯物论”)而过于自信。
在这样的立意中,寄寓了作家对于“文革”的独到反思:“文革”的悲剧,不仅仅是政治的悲剧,也是思维方式简单化的悲剧。于是,作家意味深长地写出了一连串的悲剧:过于自信的陈小马在与舒波的竞争中暂时胜出,舒波竟然因此自杀。
舒波的男友陈小龙虽然是陈小马的哥哥,可还是为此打了妹妹,并使陈小马突然癔瘫,从而也没能入伍。最后当上了兵的是谢红芳,可她终于还是在入伍以后牺牲了。在这样阴差阳错的日常悲剧中,作家揭示了命运无常、生死无常的主题。
范小青有一双发现平凡生活中的玄机的慧眼。既然命运难测、生死无常、人事不可预知,这种人间真相在人们面前展现之后。范小青又是如何寻求解脱的呢?在《赤脚医生万泉和》中,范小青似乎给出了一个答案。作品写了在后窑大队替人医病时并不起什么作用的万泉和,却以他对工作的认真、对生命的尊重几次将病人从那些所谓正经大夫手里挽救回来;在爱情生活中,他对刘玉的背叛、白善花的欺骗,也没有任何仇视和怨恨。
生活对他来说,仅仅是生活本身,所谓的爱情事业都虚无缥缈,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使有些神经质的万泉和如万泉河水一样清澈明晰。与之相对的是,让万泉和倾家荡产的裘奋斗最后却跪在万泉和跟前说“万医生,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意味着幸福”。很显然,范小青是试图以万泉和这种本真和坦然来超脱诸行无常的人间物事。
苏州包山寺有一副大和尚贯澈题写的对联:“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教人“知足”和“无求”。“知足”或“无求”对个人来说,是生活得“心惬”,从而达到“淡泊”、“品高”的境界。但值得注意的是,范小青一方面写苏州民风淡泊、玄远的心境,另一方面又并不愿意苏州人止于此境。
在《栀子花开六瓣头》中,文化馆干部金志豪为人随和,淡泊无求。金志豪的采风之旅为什么收获不大?因为他对一切都无所谓,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大的兴趣”。
结果在工作 中因为缺乏应有的热情和韧性而与发掘民间文化遗产——长篇吴歌《九姑娘》失之交臂。他为此感到了后悔,“不过他的后悔也不深,因为他对吴歌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兴趣”。当范小青点明“金志豪就是吴文化”时,作家对金志豪的那种“永远也提不起精神来,他对自己的温吞水似的生活厌恶吗,好像不”的态度显然是意存针砭的。
本来淡泊无求的个性常常受到文人和世人的赞美,但作品中范小青就触发了对于“淡泊无求”另一面的反思:对什么情感都不深、不持久,这样的人生是不是也太平庸了一点?过于散淡对应的便是无所作为。
淡泊的同时还要有进取之心。一切都是微妙的,一切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世间之事不能完全看空,有时在看空的同时又有所为,《栀子花开六瓣头》就表明,作家没有完全成为佛经的注释,而是有所超越。
如此看来,作家的心态是矛盾的。这矛盾的心态显示了作家面对佛教文化的复杂态度:有时是欣赏的,有时又是质疑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作家对佛教文化的微妙立场——既有弘扬佛理的庄严,也有不完全认同的深思。作家在《裤裆巷风流记》中写到苏州人“有种小家气,总龟缩在一块地方,对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天地一点不了解……没有大出息”,“苏州是有干事情的人才,没有干事情的气氛”。
其症结所在,就像她说过的一样:“一方面是精雕细刻,另一方面是淡泊无求,这大概算是吴文化的矛盾统一吧。
”这样辩证看问题的态度和淡淡的口吻,既表示了作家对民风弱点的理解,也富有苏州文化的韵味。范培松曾经将范小青的创作特色归纳为“温柔思维”,是颇有见地的。
佛家的终极理念,是要建立一个人间的“理想国土”,即“人间净土”。“心净则国土净”,“理想国土”的建设,虽然离不开心性的修持,但仅有这种精神的东西是不够的,是不能让“理想国土”成为现实的,还需要一个理想的物质条件,即有论者所说的:“需要建筑华贵,交通方便,光明洁净,处处有树草花果掩映,清池流水分布的都市,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如此等等。而这些物质条件的获得,在今天则有赖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文明条件的极大改善。
这就使得范小青有可能将佛家的“理想国土”建设的理念,与现实变革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转化这一佛教思想,在肯定佛家“理想国土”建设目标的同时,也肯定今人世俗的物质生活诉求。实际上,从《裤裆巷风流记》开始,范小青就在有意识地从日常生活的层面,肯定人的物质生活诉求的合理性。
到了《百日阳光》,则把这种合理的物质生活诉求,转变为为创造理想的物质条件而奋斗的强大动力。再到《城市表情》,更进一步写出了这种追求和创造,在今天必然是以现代化为旨归。
尽管作品中写到的城市建设。在具体实践中要面对许多问题,甚至诸如“住房缺乏,环境污染,交通阻塞,建筑杂乱,犯罪增加……”等等乱象,但同时也为提出“变”的要求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凡此种种,都表明范小青笔下的“理想国土”建设,不全是基于纯粹的佛家理念,而是同时也认同现实变革的历史实践。
综上所述,尽管范小青的小说创作题材广泛,但其基本的主题却常常是围绕着“佛性禅心”展开的。她善于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深藏的佛理玄机,善于通过对生活的哲理点化启迪读者去发现人生的辩证法,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中感悟智慧。
她也就在这个普遍追求成功的年代里指出了命运的无常。她不仅在小说中写出了“苏州人佛性甚笃”的精神,而且也在常常在自己平淡、玄远的文风中,流露出了随处感悟智慧、点染命运玄机的“佛性”。这种“佛理小说”与一般的“哲理小说”有所不同。
在揭示人生与社会的复杂性方面,二者虽然没有太大区别。但比起“哲理小说”的形上思考,“佛理小说”更多一层对于人的命运的现实关注。这也许就是范小青的小说在当代女性文学乃至当代小说界的独特意义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