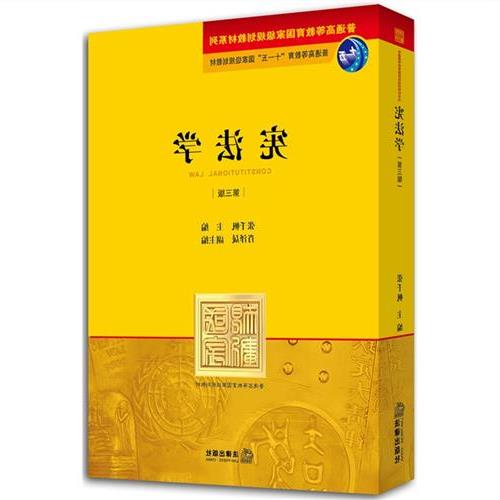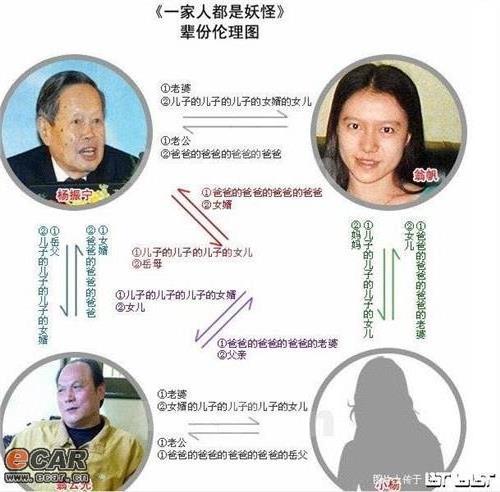宪法学导论张千帆 张千帆:中国宪法学的挑战和机遇
自1982年颁布以来,中国宪法实在不容易,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有点像三十岁没嫁出去的“剩女”,或没娶媳妇的“剩男”。这个比喻也许不恰当,但是我们不必否认这个事实,尤其是宪法学者不能否认,否则,法学同行会对我们这个职业有看法。假如要说我们的宪法还实施不错的话,那我一定可以论证,埃塞俄比亚的宪法也实施得很好,说不定比我们更好。有人说我们的宪法实施了,因为三十年来依据宪法制定了大量法律,但如果这就是衡量宪法“实施”标准的话,那么埃塞俄比亚的宪法必然也实施得很好,因为它肯定也有大量法律是依据宪法制定的。
那些没有宪法审查的国家“实施”得尤其好,因为所有法律都被认为依据宪法合宪制定的,法律的数量很可能比我们还多得多。
所以,按照这种标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会“实施”得不好,但是这样的“实施”有意义吗?即便从“马工程”宪法学教材的编写经历来看,“宪政”这两个字还是不让提。宪政是什么?不就是宪法的实施吗?如果连宪政都不让提,这样的宪法能实施好吗?
如果说中国宪法不容易,那么中国宪法学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宪法不实施,尤其是没有司法适用,宪法学研究就失去了现实素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宪法学就是一场“无米之炊”。许多人认为美国宪法学家了不起,却伯、阿克曼、孙斯坦等大名耳熟能详,他们的著述既优美又厚重,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成果是建立在丰富的行宪实践基础上的,哪一篇论文、哪一本专著不引证大量宪法判例?如果放在中国环境下,他们也施展不开、奈何不得。
在宪法适用完全不存在、宪法判例一个没有的情况下,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还算做得不错,基本脱离了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学者都不容易,不妨先自我庆贺一下。但是,宪法研究的现状是否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要求?我认为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
宪法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不论十八大之后如何,中国改革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落实宪法、改革体制。宪法实施得如何,也是衡量中国未来改革成败的首要标准。如果说最近三十年的基调是经济改革,那么今后三十年的改革首先是政治和法治改革,执政党必须完成从革命到宪政、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研究中国社会出现的大量现实宪政问题,并借鉴其它国家的宪政经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走向宪政过程中的转型经验和教训,因而,宪法学者是有大量工作要做的。但是对比这个要求,我们在研究方向上存在很大的偏差。以下,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理论研究所占的比重仍然过大。除了法理学之外,宪法学是法学各门派中最注重理论的,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个学科像宪法学对理论和方法如此情有独钟。当然,我不是说不能做理论研究,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解释方法的研究显然是必要的,但是研究了那么多年,这些问题今天已经是常识,没有必要那么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研究”这个领域。
特别要注意的是,理论研究不能成为回避现实问题的借口——反正宪法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不如研究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是不行的。我经常把宪法学比喻为炒菜,中国宪法学的基本困境就是无菜可炒,所以就有那么多人去研究“菜谱”。但是你想,一群人围着一口空锅,能发明出什么菜谱呢?这和不下水游泳,而去研究游泳的“方法”有什么两样?这样的“方法”再漂亮也是花架子,下不了水的。
学者一旦闭门造车,炮制出来的“方法”往往沦为脱离社会和现实需要的空想,很容易走偏。政治宪法学就是一个例子。我曾在其它场合对它给予严厉批评,将它的主张定性为“宪法虚无主义”。当然,学术有自由,我们显然无权标榜自己正确,而且我要承认政治宪法学者的思想很活跃,不像许多传统宪法学者那样沉闷,但我还是要说它的方向错了。
我尤其想奉劝青年学者,勿为流言所惑,不要随便凑热闹,做学术不能有太强的功利心。国内经常是某某“理论”看上去很红火,许多人投入时间精力“围观”,结果没几分钟热度,到头来发现不过是个陷阱而已。
我还想提醒年轻人,理论和方法这些“菜谱”是我们这些即将退休的人“玩”的,你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采摘,大家不要都守着“中国宪法”这口空锅。你们趁着年轻,要多行动、多实践、多研究具体问题,不要还没入道,就老气横秋地理论长、方法短。
我经常对学生说,方法论其实是等闲之辈琢磨的事情,高手从来是原创者。爱因斯坦写过什么相对论的“方法论”吗?没有,他创造的理论解决了别人解决不了的实际问题,别人才来学习他的“方法”。事实上,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可以有无穷多种,但是人们看重的只有实际上解决了那个问题的方法。
因此,宪法学研究要回到中国宪法的真问题。中国宪法确实没有判例,但是有没有可以研究、值得研究、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青年宪法学者有没有可以采摘的宪法之果?众所周之,这方面的问题和素材是大量的,多得我们无暇顾及。
每年、每月、每周都有重大社会事件发生,而几乎每一个这样的事件都和宪法有关系。虽然中国宪政的官方路径迄今不通,但是民间宪政越来越活跃,为宪法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宪法学者对这些问题是集体失语的。
我比较仔细地翻阅了今年宪法学年会的三大本论文集,发现大部分仍然在高谈阔论理论和方法问题。几十篇论文中讨论重要现实问题的甚少,只有一篇讨论乌坎选举,而乌坎显然是中国最重要的选举事件。
当然,中国当前的出版环境不理想,有些“敏感”话题无法正式发表,但许多其它问题是可以谈的。如果我们避重就轻,回避中国宪法需要解决的真问题,那么我们的研究便不可能受到社会关注。倒不是说宪法研究一定要产生社会影响,但是我们不会否认,宪法研究必须有社会价值,没有价值的研究很快会被社会遗忘。
最后,比较宪法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进入21世纪以来,宪政发达国家的宪法实施机制、横向与纵向分权机制、宪政与民主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宪政转型机制却几乎一无所知。印度是邻国,也是宪政大国,但是我们眼里的印度就只有贫穷和陋习。
泰国也是邻国,但我们对泰国的“知识”就是军事政变和红衫军闹事。对中东欧、对拉美、对非洲国家则所知更少,以至《中国震撼》断言几乎所有的宪政民主转型都是失败,也没有哪个宪法学家出面驳斥,因为我们也只是和那位作者一样以旅游者的身份跑马观花了一些国家而已。
韩大元教授正在组织翻译《世界各国宪法》文本,很有价值,但文本翻译只是起点,远非终点,不能代替具体制度研究。
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一样,“潜规则”盛行,文本未必能读出太多东西。这就要求我们深入这些国家的宪法实践,研究它们宪法制度的实际操作以及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宪政难题。但是在宪法学年会的三大本论文集中,只有一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宪法,而且还是比较单薄的,并未引用任何原文文献。
宪法学之所以出现大批新生力量跑去研究“理论”、“方法”,而不是中外宪政的现实问题,和中国的舆论环境、评价体制和民族心态是分不开的。不仅中国宪政的现实问题没人敢碰,而且系统研究外国宪政也成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打语言基础,还要辛苦挖掘支离零散的个案材料,而且研究出来的东西往往也会受到“南橘北枳”、“不合中国国情”等“外国知识无用论”的指责,而随便忽悠出来一个以“中国”冠名的“理论”却能一夜成名、叱咤一时,一个大标题加上一堆新名词就能镇住一大帮人。
这类不知所云的“理论”在政治上极其安全,一般不愁出版发表的渠道,甚至经济效益甚高。现在年轻的博士在做论文的时候就发愁毕业之后找工作,找到工作之后又发愁发论文、评职称、买房子、结婚养子,生存和竞争压力反而比老一辈学者大得多,不容易静下心来研究一些真问题,受到短期名利诱惑也在情理之中。
但无论如何,这样做最终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等人到暮年再发现自己原来一事无成,那个时候就不能再怪“文革”之类的外在因素浪费了自己的光阴,而只能怪我们的懒惰和投机取巧耽误了自己的发展。
由于我们研究了本来不该重点研究的问题,应该研究的问题却无人研究,从而导致本来有限的宪法学研究资源的大量浪费。中国这样的国家本来就面临着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对立,现在学术和社会也存在严重割裂。我们经常发现,民间关心社会现实问题,但是往往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基础,不少民间人士提出的主张在我们看来激进、幼稚甚至离谱,而我们这些有学术功底的人却不去关心中国社会的真问题。
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中国未来的宪政改革就无法具备必要的知识积淀。
转型中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巨大机遇。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来说,宪法不应该是最无用的法,而应该是最有用的法;宪法学不应该是最无用的学科,而应该是最有用的学科;宪法学家不应该是最无用的法学家,而应该是最有用、最博学、最伟大的法学家。无论学者的年龄、层次如何,只要方向正确并付出适当的努力,这个目标都是可以达到的。我尤其想提醒年轻的宪法学者,不要错失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