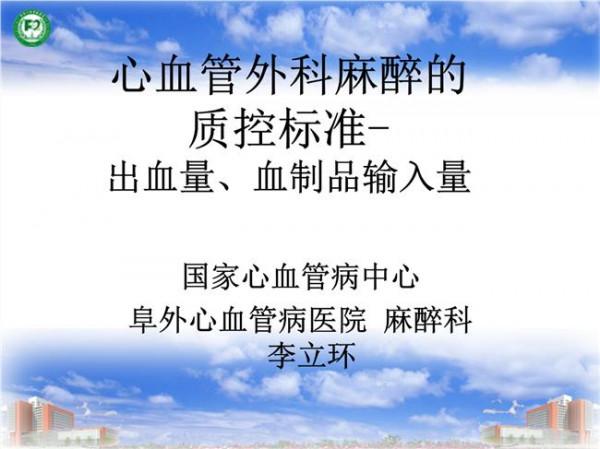何枝可依李零 2010读书札记(三):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李零先生的《何枝可依》
《何枝可依》是李零先生最近的一部书,说是"近",其实也是一年前了。李零先生早先的著作多以学术专著为主,除了在学术圈里口碑不俗外,像我这样的门外汉是知之不详的。从《放虎归山》开始,李零先生转为杂记,包括《花间一壶酒》,还有这部《何枝可依》。
前两部出自山西人民出版社,这后一部转到了三联。全书由历史、考古、汉学、战争、革命五篇组成,总计文章十八篇,全都秉承着李零先生一贯的娓娓道来的口吻,通篇仿佛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高雅的气息。这倒是很符合三联的风格。
虽说散发的气息淡淡的,讨论的却都是惊世骇俗的内容,读来让人或热血沸腾,或义愤填膺,但总能在最后时刻被一把柔和的羽扇给扇上几扇,顿时又回到了冷静的思考中。这大约就是李零先生的魅力罢,既如佛语中提到的"拈花一笑",要的就是一个"笑"字;又如中国文化里的"闻弦歌而知雅意",难得的是这份心领神会的境界。
因此上,能够读懂李零,是一件幸运的事,从中收获的满足感,比在网上游泳强太多了(据说李零先生就不怎么上网)。
十八篇文章不能都讲,我只从中选出几篇。首先是《历史篇》里的《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文章发表于1987年,写成的时间应该更早。难得的是不仅今天读来毫无时间的隔膜感,就连批判的对象也依然存在,或者说当初的问题不但没有消失,如今反倒更严重了。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李零先生呼唤中国历史研究的自觉,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希望大家认识到"中国也是‘正常儿童’"。这种说法,是基于马克思在评价各种人类古老文明时,把希腊看作唯一的"正常儿童",而把其他古老民族叫做"粗野的儿童"或是"早熟的儿童"。
在八十年代中期那个特定的时间里,可以看到两种历史研究的印迹:一种是之前左倾教条的"唯马克思论",机械地照抄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述,不去分析马克思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也会得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这种可能;另一种则是反过来,在不承认马克思历史理论,反对左倾教条的时候,着力于去"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显得多么辉煌,也终究不免是腐朽的,因为它们非但不能挽救中国近代的落后,反而很可能是它的一种宿疾;而欧洲,无论其传统文明有多少落后面,这些落后面也毕竟有其‘生命力’,因为它们是‘导向’近代社会的线索。
"这种声音听起来是多么的熟悉啊!这不正是当下许多持"中华文明劣根性"和"一切西化必要性"观点的人所依据的理由吗?可是在李零先生看来,这两种印迹虽然看起来有着"严重的‘回溯性差异’",但根源却都是从盲目坚持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那儿来的。
所以它们体现出来的并不是对于源头的修正,而仅仅是流向的不同罢了。这种五十步笑百步的历史研究方法,正是我们应该认清并予以批判的。中国的历史研究应该有自己的视野和观察角度。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他分析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绕不开的"分期"、"停滞"和"萌芽"这三个问题。这刚好又是至今,我们在所有的观点交锋中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关于"分期"问题,李零先生认为,正如我们在历史研究观念上要意识到"中国也是‘正常儿童’"一样,我们对待"分期"也应当抛弃"拿欧洲历史作标尺"的惯俗,转而发现属于中国自己的历史划分和评判标准。
例如,中国实际上从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而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国家形态、阶级(或说是阶层)构成和劳动生产方式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出的阶段性规律,才是研究中国历史"分期"所应关注的焦点。
关于"停滞"问题,李零先生是这样看的:
"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王朝循环,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历史长期停滞、不能进化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不带感情地去看,倒可以认为是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标本。……可是问题也出在这里,大家很难不带感情地去看问题。
现在形势变了,许多旧说法被抛弃了,但并不是说大家在历史认识的动机上就完全‘透明’了,和政治背景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私下同一些朋友交换看法,了解到他们当中有一种基本倾向,……就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以直接引出‘停滞说’,把中国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捅出来。……这后面根本的东西还是……大家痛感中国太落后了。"
李零先生用词虽然婉转,其实道理讲得很透。《孙子兵法·火攻篇》里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放到做学问上,是不是也应该做到既不可以出于"怨恨",也不可以出于"功利"啊?
关于"萌芽"问题,李零先生认为也同样需要摈弃"简单比附"的分析方法。其实现代工业文明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和之前的农业文明一样,也都有一个萌芽、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农业文明最初的萌芽也不是多么普遍的,是自然环境和工具进步等多个因素耦合的结果,"发生的地点也相当有限,是从几个点先发生,然后逐渐形成一种‘适应辐射’,影响到许多边缘地区的发生",并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实现了文明的融合和进步。
现代工业文明也是一样。其萌芽的"发生条件显然比农业还要苛刻",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和不同文明的激烈碰撞。所不同的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传播速度更快,农业文明花了上万年才完成的过程,现代工业文明几百年就完成了。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技术。正是由于技术存在着更明显、更悬殊的代差,所以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水平差异,也就远远大于农业文明之间了。
"现代意义的任何资本主义发展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之后的发展。这是我们讨论萌芽问题时不应忘记的一个前提。"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不光是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有关,也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有关"。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和西方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有关的。所以我们在分析"萌芽"问题的时候,就不要只是简单地采用"因素论"或者"系统论"的观点。而是"不妨把眼光放得离今天更近一点"。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李零先生对当时(八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些史学新著进行了评述,并由此引发出对于史学研究到底应该选择哪种方法的思考。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自然科学方法是否一定适用于甚至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的观点阐述。
诚然,"我们不能因为目前研究历史的许多方法,按照科学的一套标准来衡量还很不科学,就认为它们一无足取",实际上"现在自然科学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在许多方面还显得非常无力"。其实岂止是历史,对于经济、社会的很多层面,都是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现成公式的。这在文章发表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接下来在《历史篇》里,我还要提到另一篇文章:《两种怀疑——从孔子之死想起的》。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李零先生在这里比较的,是子贡和孟子不同的怀疑观。
子贡怀疑的是"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让子贡产生这种怀疑的原因,是孔子去世后社会舆论对孔子道德学问的怀疑和诬毁。子贡是坚信甚至是崇拜老师的,因此他对社会舆论的这种恶俗感到很不满,继而产生出了对"纣之不善"的怀疑。这种怀疑可以简称为"坏蛋未必那么坏"。
李零先生认为,在"古代,尧、舜是好人的符号,桀、纣是坏人的符号。好人往好说,怎么都不过分;坏人往坏说,也是理所当然。舆论有舆论的放大效应,自动发酵,迅速冒泡,谁也捂不住。"李零先生的这番评述真可谓是入木三分!
古代如此,今天难道就不是了吗?我们放眼看看,在今天,各种小道消息、负面新闻对人身的攻击,其盲目性和残忍程度哪里会有稍减,简直是越发令人发指了。李零先生借子贡之口引发的观点,也许正是对于这种恶俗现状的指斥吧。
与子贡不同,孟子怀疑的正好相反,是"好人还不够好"。他认为《尚书》中对于武王伐纣时"血流漂杵"的描写是不对的。因为武王是圣人,圣人伐无道,天下只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哪里会大加杀伐,闹得个"血流漂杵"呢?其实今天的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孟子的偏颇来。
就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哪一天不在发生"无义"的战争呀?如果真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是仁义面前无流血的话,又怎么会有"春秋无义战"的结语呢?孟子到处奔波宣扬的仁政,不就全是无的之矢了吗?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孟子。李零先生对此的评价可谓中肯:
"怀疑,常被说成是一种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甚至被当作一种方法,就像港台评论家笔下的《灵山》和《色戒》,那叫‘纯文学’,那叫‘纯艺术’,这种方法也叫‘纯方法’。
其实,方法后面有立场。怀疑只是一种态度或一种立场,它是相对于某种信仰。怀疑和相信,常常互为表里,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历史上,很多‘正统’原来都是‘异端’。……怀疑‘正统’,批判‘正统’,常把‘异端’变为‘正统’。
但可惜的是,坐稳了‘正统’的‘前异端’却常常容不下其他‘前异端’,更容不下继起的‘后异端’。
这是思想的宿命。"
读了这篇深刻的文字,大约很容易就知道李零先生指的是什么了罢。所以我们也该像李零先生那样,对跟自己打嘴仗的家伙们说:"人们常常为信仰而争论,但争论对信仰最没用。"由于"信仰的特点是唯一性和排他性",所以还是孔子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为谋"!
李零先生在《考古篇》里收集的是几篇关于考古的专业文章。我是个外行,所以只是抱着好奇简单读了读,一时半会儿不太容易产生共鸣。可接下来《汉学篇》的第一篇文章《学术"科索沃"——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却着实让我产生了巨大的共鸣。
文章通过围绕巫鸿先生一篇学术专著在美国汉学界引发的口诛笔伐,试图通过纯学术因素的分析,来说明存在于中美(或者可以扩展为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巨大沟壑。
学术上的东西我不懂,但是正如李零先生在上一篇文章里所说的那样,任何所谓纯学术的问题,其实背后都是立场。学术争端表现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其背后必然蕴含着文化主导权的争夺。联系到李零先生对于国际汉学界的介绍,我们不禁要为这种现状鸣不平。
凭什么这些只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的家伙,就敢充当国际学术界,而且还是关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学问?这里面带出来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难免让中国人和一百多年来国运的衰弱联系起来。
李零先生对此其实也是不满的,尽管他没明说。他在文中以学术探讨的口吻指出,"西方学者批评巫鸿的目标",也许"更主要的集中在所谓‘解构永恒中国’,即打破我们习惯上爱说的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
从这一点中不难发现,"西方学者的批评并不仅仅是针对巫鸿,它也包括巫鸿曾经从中受到教育现在也还没有割断联系的学术背景和学术习惯,也包括他还时时引用的中国同行的研究。"
如果李零先生的分析是准确的话,那么我们面对的现实实在是太险恶了。如今还有许多据说是很有学问、很代表良知的老少知识分子,他们口中的国际学术界可不是这样。在那里,到处都是满怀善意的朋友,到处都是足堪取食的"仙丹仙果",随便拿来吃上一口,就可以"长生不老","立刻成仙"。
读了《学术"科索沃"》我们不禁要问,国际学术界对我们真的是这么友好,他们的成果真的是对我们这么灵验,并且还能"敞开供应"吗?人不可以天真到这种程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今据说到处都是君子,但是我没看出他们在自强不息。反倒是那些被他们所攻击、嘲讽的对象,有不少正在默默耕耘,努力地要造出一片有别于"西天"的天地来呢!
《军事篇》里的头两篇文章《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与劫持》、《读<剑桥战争史>》都曾经收录在《花间一壶酒》里,这次不知何故又重新选入本书,也许李零先生有他的考虑吧。
由于之前已经读过,如今再次见面,就算是重温罢。孔子曰:"温故而知新。"一篇文章多读几遍,不但可以重温一下精彩之处,说不定也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呢。
先说头一篇《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与劫持》。我对文中关于"恐怖主义一锅粥"的那一段最为欣赏,因为它说出了我(大概也是许多人)的心里话。
"现在,所有人都在谈‘恐怖主义’,而且是在‘反恐’的前提下谈这个主义。‘恐’在‘反’下,当然是负面的东西。
大家对‘反恐’的正当性几乎毫不怀疑,但谁反,反谁,反什么,怎么反,却言人人殊。……布什用恐怖主义表示所有眼下(注意:只是眼下)美国讨厌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最具代表性。
普京则用它指车臣武装分子或其他分离主义分子,我国则指东突,阿拉伯世界(不是所有国家)和欧美的左翼团体则反唇相讥,说最大的恐怖分子有呀,那正是美英两国自己,布什、布莱尔,再加沙龙或什么人。
这真像庄子说的‘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所不在’,‘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天下大乱,人心大乱,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可指的却绝不是同一回事;说谁是谁,谁说谁,谁就是谁。我们只能说,美国财大气粗腰杆壮,树敌最多,要反的恐怖主义也最多,如此而已。"
读了这番辛辣的文字,感觉就像出了口恶气。这倒不是说我们对死于恐怖袭击的人们不予同情,它只代表我们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假反恐之名,行侵略之实的行径十分不满罢了。
早就听说过什么《剑桥插图中世纪史》、《剑桥插图世界科学史》,还有《剑桥插图中国史》了,但一本也没看过。要不是读了李零先生的这篇《读<剑桥战争史>》,还一直以为这些冠以"剑桥"名义的大作都是来自于剑桥大学的学术专家呢。
我估计和我犯了同样错误的人,一定不在少数,这就叫"望文生义"。原来这些声名显赫的家伙,其实跟剑桥大学没有多少关系,只不过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准确一点儿该叫"剑桥大学出版社版"的某某史才对,都是这些翻译捣的乱。
可是人家翻译也没有大错,无非是为了书名更提气,书更好卖罢了,就像某品牌奶粉一定要强调源自某某国纯正的牛奶,某减肥药一定要突出经某某国机构认证,或者某牛肉面馆一定要在招牌上写上某州一样,要怪只能怪咱自己没见识。
李零先生的文章与此无关,讲的是书中没有涉及中国的内容这一事实,以及从这种现象里体现出来的西方心态。许倬云先生曾经说过,他出国之前以为,世界之大,只有中国;出国之后才知道,世界之大,没有中国。李零先生据此发现,尽管"这种‘没有中国’的感觉,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在各种‘剑桥史’中(除去专讲中国史的书),却是比比皆是。
这是很好的教育。"教育谁?教育什么?为什么好?李零先生没有讲,只有让每个人自己去想了。
"本来这些历史,它们统统都是世界史,然而它们都只标‘剑桥’,不标‘世界’,作者讲得很清楚。世界史总得讲世界吧,但作者觉得,要讲战争,那我们是胜利者,这个历史当然是我们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不仅对了解西方战争史有用,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现在之所谓‘国际学术’到底是什么意思。"
读了李零先生这些感慨,我自己的感慨更多。原来西方所谓的和中国无法沟通,症结就在于此:一曰"看不懂",二曰"看不起"。而我们自己呢,不但"在近百年的文化争论中,我们不是自大就是气短",今天的情况又何尝不如是?启蒙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人们懂得最基本的道理,要是连什么是最基本的道理都没搞清楚,还奢谈什么启蒙?!
结 语
李零先生给自己的书斋起名"待兔轩",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守哪棵株?待什么兔?能不能待得到?全凭大家自己去体会。反正李零先生自己认为:待得到。在我看来,这也许是先觉者对于后来者的期许。从书名也可以看出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孟德的心思,困扰了人们一千多年,可到现在还没完全搞清楚。李零先生的意思,我却看懂了,绕来绕去,无非是这一枝。
以李零先生对问题的态度,生活中一定没少碰见不同意见,有些甚至是激烈的指责,可是从没见他跟谁争论过,就连批评人,都显得那么温文尔雅。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夫唯不争,故天下不能与之争。"还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李零先生的做法,很符合这些标准。老子姓李,李零先生也姓李,说不定真有关系。不像李世民他们家,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硬贴上去的。热切盼望李零先生能有新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