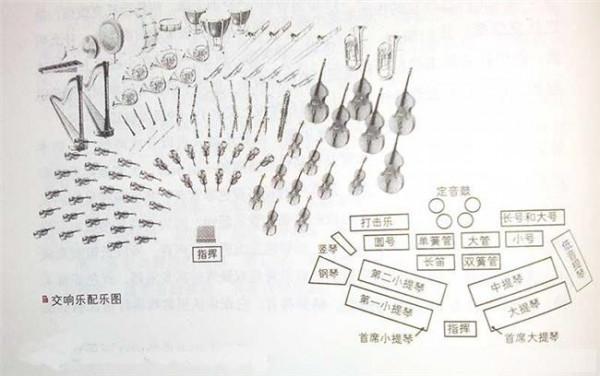盛可以的经历 盛可以:我写作的初衷 是对无趣的一种默默反抗
长江商报消息 10年前,盛可以开始写小说,此前并未从事过与写作有关的职业,也未受过任何科班教育,纯粹自学成才。据说她早年在深圳上班时,因工作清闲,每天都看报纸副刊,看着看着,发现这样的文章自己也能写,一敲二打,网上、网下,短篇、长篇,写作欲望如山洪暴发,于是果断辞职,第一年时间就写出60万字来,其中包括令她名声大噪的《北妹》和《水乳》。
盛可以无疑是一位拥有耀眼才华的小说家,她在小说中所倾予关注的人物,无论是小镇少女,还是打工北妹,或者婚外恋的情妇,都是社会底层的草根族群。我们可以推测说这和她丰富的经历有关,不过,拥有丰富的经历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出好作品。
在采访盛可以的前一周里,我恶补了她的两本小说:《北妹》和《时间少女》。
《北妹》是在豆瓣阅读这个电子书阅读平台上发现的,在支付了6.99元之后,我用两个晚上把它飞快地看完,点到最后一页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就是书中第三个来自湘北的打工妹了。它就像一部20世纪末的流浪汉小说,人物不断地在一个个场景中运动、迁移,为生存而看尽世间百相,可是又对生命怀着最高的热情。
而《时间少女》的体验则完全不同,读到第40页时,我企图放弃,因为这个故事潮湿、不快乐到令人难受,但是当我咬牙坚持到一半时,它又开始召唤我了。在这些拥有最大众化名字的小镇少年少女的身上,我甚至看到了美国现代文学之父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的影子:“每个人都怀抱着自己的真理,这是多么畸异的一件事。”
在对待创作艺术上,盛可以表达了和纳博科夫相似的意思,盛可以说:“一个作家的自我训练有时完全是无形的,并非在真正动笔时才是创作,几乎所有时间都与创作有关,阅读、聊天、行走,甚至做梦,世界上不乏受梦启发创作的作品。”
而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的序言中写道:“写作的艺术首先应将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不然这门艺术就成了无所作为的行当。”
也许,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盛可以的小说用的尽是现实的料子,却编织出一张带有梦境与魔幻底色的毛毯,它能御寒、能装饰、也许还能带我们离开地面。本报记者 刘雯
【个人简介】
盛可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湖南益阳。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北妹》、《水乳》、《道德颂》、《死亡赋格》、《时间少女》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可以书》、《取暖运动》、《缺乏经验的世界》等。作品被译成英、德、韩、日、荷等多种文字。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国女性文学奖、未来文学大家TOP20强等多种奖项。现为广东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专访
“能影响我写作的大约会有阳光、雨露、风雪、光合作用……以及经典与杰出的作品本身”
锐读: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写小说的?如果说写小说是一种技艺的话,你是怎么训练自己的?是从短篇到中篇、长篇这样慢慢摸索的吗?
盛可以:是对生活感觉无趣味、无意义时开始写小说,并且逃离熟悉的环境,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写小说不一定拯救了自我的虚无感,但能让人更清醒理性地看待事物。写小说自然是一门技术活,就像一个人进山拜师学武功,师傅让他扫地、挑水、砍柴……以后师傅不教他真功夫,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些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一个作家的自我训练有时完全是无形的,并非在真正动笔时才是创作,几乎所有时间都与创作有关,阅读、聊天、行走,甚至做梦,世界上不乏受梦启发创作的作品。我的写作没有接受过按部就班的训练,中篇写得极少,我不喜欢写中篇,也写不好中篇,偏爱短篇的精致圆润和长篇的缠绵跌宕。
锐读:你似乎并不太看重批评家对你小说文本的解读?对你而言,写小说更是一种面向自己内心的活动,是吗?
盛可以:我会看别人怎么解读,“看重”就没有必要了,看重了,你就受左右了。能影响我写作的大约会有阳光、雨露、风雪、光合作用……以及经典与杰出的作品本身。写小说,就是从一种不喜欢说话的状态,在叙事中变成一个话唠,一个心计鬼,甚至一个龌龊的变态佬,没有什么比在这些人物间穿行更有趣的了,当然这也常常让人心力交瘁,就像一个人饰演了全部剧中的角色,非常累,也会很有成就感。
锐读:有人说企鹅出版社选中《北妹》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存在猎奇心理”,你怎么看这些说法?他们会这样说,是纯粹的嫉妒或者心理扭曲或者误读你的小说吗?
盛可以:这些年我听到过各种版本的“有人说”,以前会在意,现在早就不会了。我会看重我仅有的几个朋友怎么说,怎么看待我这个人,以及我的写作。企鹅出版社中国CEO周海伦说,她喜欢做出版,因为可以把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品带到远方去,给这些作者的心血之作找到新读者。她们喜欢《北妹》,因为这本书讲述了中国经济繁荣之下的人性故事,表达了中国移民的体验,探索了姑娘们的磨难和转瞬即逝的欢愉,也赞颂了她们的力量和精神。
“我不会把写作当作冷血的谋生工具,我更愿意让写作这件事成为生活的乐趣”
锐读:《北妹》里一切的不公平和痛苦都以诙谐、解嘲的方式写出,令人印象深刻,而《时间少女》却让人很难受,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创作,这是一种对自我创作能力的探索和试验吗?
盛可以:《北妹》其实写的是女性的灾难与苦难,但我是以一种喜剧的语言与形式表现,因为在主人公钱小红看来,一切生命中出现的动荡打击都不足挂齿,她就像野草一样疯长,有一种乐观与自然蓬勃的生命力。我的每一部长篇都长得不一样,风格差距十分大,像你例举的《时间少女》与《北妹》,真的是天壤之别,尤其语言风格,完全不像同一个人写的。
《时间少女》充满了八十年代湘西小镇潮湿阴郁的气氛,喧哗与骚动,理智与情感,城与乡,爱与死,以及青春与残骸,它是我的第三部长篇,如果现在来写,我根本不会用那种完全把自己投放进去的写法,太粘连了。
写了整整十年小说,试过多种写法,最后也知道哪一条路与自我最为契合,当然以后很难说我又会有什么新的追求。我不会把写作当作冷血的谋生工具,我更愿意让写作这件事成为生活的乐趣,就像我写作的初衷,是对无趣与无意义的一种默默反抗。
“我没有预先带着什么价值观人生观去创作”
锐读:现在人们弄出一个“中间代”的概念来对70后作家群打包,你跟这些作家熟悉吗?据了解,他们并不认为在写作上彼此之间有任何可归类之处,你的写作也是一种个人修行,无关乎外界的定义或者眼光,是这样的吗?
盛可以:任何命名对作家个体都没有什么意思。生于七十年代的这拔作家,其实是很强的一代,云雾遮敝的青山,始终在,不喧嚣,不邀宠,不急于将倒影投向湖心。不可否认这一代作家当中,很有几人是非常了不得的,比如冯唐,阿乙。这一代作家有共性,就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他们在年龄上相近,然而写作风格迥异,不可归类。
锐读:有批评家说你应该“珍惜自己感觉的天分和激情的天分,同时关注主流社会的价值。”其实在你的小说中反映了许多真实的社会问题,也透露出不少关怀与悲悯,你认为将天分用于哪些部分,才能完全体现出它们的价值?
盛可以:我不知道哪位批评家这么说过,什么叫主流社会的价值?我没有预先带着什么价值观人生观去创作,我只知道我所写的人物,她活着,她痛苦,她哀号,她奔走于人世。我竭尽所能去描述她们,去塑造她们,去表现她们,如果人们记住了《北妹》中的钱小红,记住了《道德颂》中的水荆秋,记住了我书里的人和事,我觉得那就足够。
锐读:在写作中你会讨好读者吗?你重视普通读者的评价吗?
盛可以:普通读者对作品的评价是最真实的,也是我最想知道的,尤其是当他举出某个让他共鸣的细节,真的令人感动。当然,也有人表示不喜欢我的作品,这不奇怪,也不会失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一个好厨师能做的是,用好手中原材料,掌握火候,用心烹制,只要好吃,自然有人点。
锐读:现在在黄山闭关写作的感觉如何?正在进行的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一睹新作?
盛可以:我在黄山德懋堂十八学士,一个新徽派建群落,这儿空气清新,澄澈,纯粹,非常适合读书写字,呆了两个多月了,可我差不多要出山了,因为外面有事情要处理。手上这部作品不知道还要写多久,因为下半年会有几次出国访问,还会有别的计划。慢慢写吧,不着急,有件事搁着,有所惦记,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