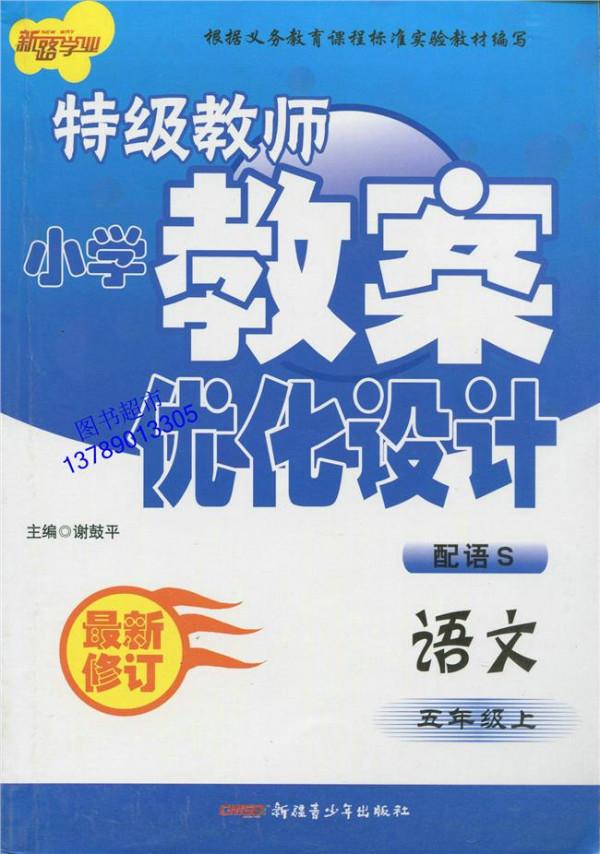日月山徐则臣 【活动实录】高希×梁鸿×徐则臣:从中国到埃及——今日乡村何在
【嘉宾简介】阿米塔夫•高希 印度著名作家、学者。1956年生于加尔各答。他从新德里大学毕业后,前往牛津大学研习社会人类学获得博士学位。 自198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理性环》之后,阿米塔夫•高希笔耕不辍,出版《在古老的土地上》、《玻璃宫殿》和朱鹭号三部曲小说(又名鸦片战争三部曲,包括《罂粟海》、《烟河》、《烈火洪流》)等作品。
他曾获得包括法国美第奇奖、印度挲诃德耶学院奖、英国阿瑟•克拉克科幻奖等奖项。2007年,阿米塔夫·高希被印度总统授予印度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2011年,他获得蒙特利尔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国际大奖。
梁鸿 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非虚构文学著作《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文学著作《神圣家族》。
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度中国好书”,“首届非虚构大奖·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奖”等多个奖项。
徐则臣 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居北京。著有《耶路撒冷》、《午夜之门》、《夜火车》、《跑步穿过中关村》、《居延》、《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等。2009年赴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做驻校作家。
2010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WP)。曾获第四届春天文学奖、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被评为“《亚洲周刊》2014年度十大小说”第一名、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首届腾讯书院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英、日、韩、意、蒙、荷、俄、西等多种语言。
高希:《在古老的土地上》其实写作于25年之前,很高兴在今天终于有了中文版本。这本书本身经历了一段奇怪的历史,因为在在25年前刚刚写成和出版的时候,这本书几乎没有什么讨论,也没有什么书评,销售量也非常少。但是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这本书的读者不断的被壮大,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命运。
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呢?我自己对此都感到震惊,我在写的时候就知道,因为我在书中要处理极其敏感的三个族群,涉及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的关系和故事,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穆斯林还有一个叫印度教徒。这三种人其实在平常的现实政治当中也充满了冲突,我在书写的时候要把它给处理到,不至于损伤不同读者的认知和接受。
但是很神奇的是,在那么多年之后,这本书还是侥幸的幸存了下来,而且它成为了很少的、同时翻译成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作品,并且在两个文化的语境当中都为读者所接受和阅读的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写的主要是在一个海洋的时代里面,印度人在新印度洋地区和世界建立的一种联系。我们现在身处中国,或者说在地域上是在东印度洋的贸易的区域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后来衍生出的一个兴趣。对我来讲,今天这本书中文版能和大家见面,也有很重大的意义。
徐则臣:刚才高希先生说这本书在25年之后,能够受到这么大的欢迎,出乎意料。大家都知道,梁鸿老师近几年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在中国的非虚构文学的创作里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对梁鸿老师这两本书很熟,因为这两本书最初发在《人民文学》上,我是责编。
梁鸿老师跟高希先生,他们俩作为写作者,他们的背景和经历都特别特别的像。我想问梁鸿老师的是,从一个读者、一个作者和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本书,这本书哪些地方吸引了你?
梁鸿:首先作为一个读者,我喜欢这本书,我也在微博上推荐了两次。喜欢不是说他写得多么引人入胜,而是说它这里边有一种非常奇妙的空间的错位和叠加,这本书是双线结构的,一条线是埃及的当代的农村生活,另外一条线是埃及12世纪的,以寻找一个人为线索来写,几乎可以说是两个时空。
当代的埃及农村在高希先生的笔下,是一个和中国的农村有某种重叠的一个地方,落后、保守、要走出去,有一种极大的的愿望要走出去。当然他们走出去是到伊拉克,是到巴格达,我们走出去可能来到北京,来到上海。从这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埃及的当代农村,也是破败,或者说是极需要被改变的。
但是这两个空间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联系。其中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考古,12世纪的埃及,以寻找一个商人为线索。高希先生做了很多资料的考察,在这一过程里面显示高希先生作为学者的严谨和讲故事的高手,两者之间的充分结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的,有一种寻找世界之谜的感觉,虽然这个谜可能只是一个人的谜。
当两个空间叠加在一块的时候,你感受到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消逝,非常奇妙的人类文明的变迁,所以我觉得这是有连续性的。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它是两个空间叠加在一块,你能感受到这本书里面历史既有一个断面,也有一个连续面。
我觉得高希先生也展示一个小说家的特别大的能力,他在写埃及的当代生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鲜活,虽然对这些人的名字我们确实比较陌生,不好记,但每个人内在的精神的困顿,以及他生活在那样一个泥淖之中的挣扎,我觉得是一个人的挣扎,不仅仅是埃及人的挣扎。
作为一个作者,其实我是特别敬佩高希先生的,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他对语言非常敏感,他一方面会考察一个词语的来源,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是一个简单语言,但当你把它放置在历史空间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携带着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的语言,从这一层面看,即使是写当代,他也进入了历史的层面。
我当年写梁庄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我对梁庄人的语言里面所包含的信息,要远远超出我们所日常感知到的信息,只不过我们把它忘掉了。这时候实际上需要一个作家、一个操持语言的人来做这样一个工作。从一个简单的词语入手,哪怕是一个音调来找到曾经存在的历史和一些密码似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做一个作者,其实从中可以获取很多东西。因为我同时也关注中国的乡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有跳出来的感觉,书中有一个家庭叫纳斯比家庭,就这一家人一直想出去打工,想挣钱,因为他们到巴格达挣钱,要远远超出他们在土地里干活的收入,所以就千方百计要出去。
而他们的家,荒凉破败,几乎毫无希望,是被困守在这个文化里的某一个地方。书中一段记录了作者“我”和其中一个主人公争吵,各自说我们怎么伟大,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两个被淘汰的文明的代表,在争相说自己怎么先进。我觉得这个“淘汰“这个字是特别值得研究的,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其实也包括中国文明,都特别值得反思。
高希:关于那个语言的问题,前面我先想说一下,因为梁老师的作品还没有被翻译成英文,我很希望它有机会被翻译,并且为更多的人所阅读,因为这个话题非常重要,我在埃及做田野的时候,因为我是在乡下,所以我其实说的那个阿拉伯语是带有浓重农民口音的阿拉伯语,后来我到城市里面去,比如说开罗、亚历山大这些地方,我去餐厅里面,因为我的浓重的乡下口音,甚至会遭到拒绝,就是他们的那个服务员都不愿意服务我。
而我做鸦片战争研究的时候,我考察比较多的是广东,所以我对中文的有限一个学习其实是粤语,在北京如果说我用的我的那种粤语跟这个人交流的话,可能也会被认为是疯子。
这个城乡之间——从农村到城市,这个大时代的一个主体是很重要的一个主体,那在阿拉伯世界它的发生又带有很多的特质,其中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会觉得很难去赞赏的一种特性。其中之一就是生态的一个崩溃。
25年前我在埃及农村做研究的时候,距离阿斯旺大水坝这个工程已经有20年的时间,那个水坝在20多前其实已经造好了,但是它就使得那个土地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这个土地已经无法恢复它的肥沃,在种植之后,很难去恢复它的肥沃度。因为这个土地的不断的贫瘠化和盐碱化的问题,所以整个埃及的农业就变成了非常依赖于农药和肥料,也就是这些化学的那些药品,所以这个土地是在不断地被化学所周转,所流转。
虽然埃及不是一个特别面积小的国土,但是它适合种植的肥沃的土地仅限于狭长的尼罗河两岸,在25年前,我在埃及做考察的时候,是1400万的埃及人口,现在是9500万。在埃及这样的地方,本国的整个人口增长比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它本身并没有一个,像在东亚地区的那种经济的增长,以至于能够去吸收这些劳动力。
所以在整个中东地区,唯一可以吸收这些人口的劳动力的,其实是海湾国家地区。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其实对于埃及有摧毁性的打击,因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发生之后,那原来的吸收这些劳动力的大国,比如说像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国家,他们就拒绝再从埃及这些地方吸收劳动力,而是把这些劳动的机会转向给菲律宾、泰国、印度甚至中国的外劳。
那跟中国和印度不同的是,在国内,中国和印度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还可以往城市里面去流动,因为有经济的发展,可是在中东的这些地区,这些巨大的人口的压力在海湾战争之后根本就无处可去,他们只能去,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看到的往地中海的沿岸去,但这个仍然是一个人口带来的发展上的灾难,因为这个给中东地区已经很困顿的经济和政治带来巨大的压力,又制造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加上气候变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中东带来的影响是更大的。比如说在叙利亚,2008年的气候干旱使得农村的大量人口去了城市,这也为之后在城市发生的骚乱埋下了伏笔,而在埃及就是因为这个盐碱化,盐水进入土地导致很多土地其实已经不适合耕种了。
在今天这个场合提到这么多不幸的消息,也不是我所愿意的,但是在中东地区这些年来发生的这个变化,确实是对我们所谓乌托邦世界的一个幻想的彻底的打击,我们了解的这个“阿拉伯之春”,其实不是一个只关乎民主,关于社会运动的问题,它背后实质就是一个食物的危机,粮食的危机。
那这种经济上的问题是导致包括埃及在内这些地区的政治压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我们应该说在面对的是一种非常新的情况,但是它所产生的这个后果,我们还是未知的。
高希:我70年代末去埃及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农村的那些地方,你会觉得一千年前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即便是像开罗这样的城市,它其实有一部分是在14世纪建起来的,在那个城市里,你仍然能够感受到中世纪带给你的启发和联想。而我生活的那个农村,那个村子里没有通电,建筑的材料还是泥土,所以在那边去遥想一个12世纪的情景,完全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这个可能是有欺骗性的,包括你今天去看印度的农村也一样,即便是在70年代末的埃及,他们看上去有一个古老的面貌,但是那个农村的生产的形态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大量使用农药和肥料,而在印度今天也是这样子,你可能去一个今天印度的乡村,你觉得它很古老,可是尤其是电视在埃及和印度带来的影响,它改变了年轻一代的农民、渔民,改变他们的欲望和野心。
年轻人从中看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那个生活,所以很难阻止他们不想去加入城市中产阶级。但是要让这几千万的人去加入一个城市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这个本身的负担也不是印度能够承担的。
对,我很想知道,梁鸿,从你的角度来讲,你是怎么来看待中国同样在发生的这种转变的?
梁鸿:其实中国乡村我也是这近十年才有一个真正的观察,因为我老家就是河南中部的一个乡村,我在那生活了20年,和大部分人一样,离家求学,然后来到北京,最后在大学教书。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才重新又回到这个村庄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考察。
刚才高希先生有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值得去想,就是“欺骗性”。其实在我们一般人印象里边,乡村好像变化并不大,只不过多了几栋新房,然后人来来去去,生老病死,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但如果你真的走进乡村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当代乡村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首先人的生活的形态,可能我们都知道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最正常的符号的表达,但是你要是走进乡村去看我们符号中的农民工的时候,或者说那个老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样一个老人,他所经历的情感的伤痛、落寞,以及带来一系列具体的实际问题,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
乡村已经不再是一个自在的、完全一体化的独立主体,它其实跟我们城市发展之间我觉得几乎是一致的,但是反过来呢,中国的乡村又可以说是城市的背面,我经常说一句话还被骂,我说故乡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呕吐物。为什么呢?因为城市的所有负面的东西,在乡村都有一个更加夸张的、触目惊心的方式来出现。
比如说环境问题,尤其是北方的乡村,很多河流没有了,如果有的话是黑的,是发臭的。河流是断的,沙堆就像悬崖一样,一堆堆的堆在河道里面,自然的破坏已经到了一个,难以修复的状态。
就垃圾更不用说了。梁庄是在一个高的河坡之上,你从河坡下面看,那些垃圾就像一个个白色的瀑布一样,固状的、不流动的瀑布,你要从远处看,非常壮观。那种现代化的工业,那种泛滥式的使用,对乡村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当然,人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北方的农村里面,几乎每一个家庭的人,都有出去打工的人,老人在家带着孩子,夫妻俩出去打工,日子也不错,也挣着钱了,但其实他们内部的情感结构,包括人的成长问题,在城市打工的待遇问题等,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是觉得,中国的乡村在当代可能还很难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看,它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病症的一个反映,不单单说我们来解决农村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是要把和城市的问题一起来解决才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城市发展往往是排斥农村的,比如说我们就没有贫民窟,我们的城市是高大上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城市,当然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的表现,但是那些打工的人住哪儿去了,反正我们也不用管,反正住在顺义,或者某一个更远的地方了。
这里面它其实隐藏了很多非常具体的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不是农民的问题,它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一个大的发展规划,当然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对人的看法的问题,人的观念的问题。
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有种特别大的感触,在埃及的乡村,其实它也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怎么样来重新解放自己,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大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之中来找到某种位置。所以在这本书里边,有很多人,有很多农民都在寻找出路。
并且试图从文化上来找到自我的一个解释,这点是特别有意思的,其实中国的农民是一样的,千万不要把中国农民想成一个特别简单的愚昧的这样一群人,中国农民谈的都是国家大事,我们会嘲笑他还谈国家大事,但其实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也在给自己找某种解释,这种解释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这一点乞求,这一点愿望让人尊重,但有的时候你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特别深刻的社会黑洞的存在。
高希:我非常同意你刚刚说的,在埃及、印度和中国这些古老的文明里面,其实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就在于,这些文明其实都是农业文明,至少它的渊源是农业文明的基础,但是在这三个国家里面,农民都是受歧视的,所有做体力劳动的人都是被歧视的,都是被看不起的,但事实上只要你种过粮食的话你就知道,种粮食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难到其实没有人自愿的想去做,但是问题是每个人都要吃东西,每个人都依赖食物,那年轻人由于被电视俘获,而迫切地想要离开土地去城市,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在失去很重要的一种土地上的知识,而关于种地,就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种出粮食来的这个知识,又是经过多少代人的累计才能有的一种知识的经验,可是现在这些知识的经验就没有后继。
在今天,不管是电视媒体还是网络媒体,这些大众媒体上面,其实你看不到一个农民的正面形象,还在耕地的农民以一种非常正面的鼓舞人心的形象的存在,那这个对农民自己来说,他就会产生一种自恨,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仇恨,对那些去了城市里面工作的人来讲,不管他做的是一个多么不济的糟糕的工作,他转而仍然会厌恶他仍然在家乡土地上耕作的那些父母或者是兄弟。
我很想知道,在中国现在年轻人要给父母养老吗?赡养父母这样一种传统,现在还存在吗?
梁鸿:在农村肯定是这样的,在农村老人并没有特别多的养老保险,所以说农村的父母是一定要依赖于孩子的。但是反过来,农村的孩子现在特别依赖父母,只要父母还能走动,因为年轻一代的孩子都留在农村,他们自己在城里面打工。
所以有些父母,既使70岁以上的,也还要带好几个里孙外孙。所以现在的农村老人的养老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前段时间好像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农村老人自杀,现在农村自杀问题其实已经变成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
因为没有希望,有的是钱的问题,有些确实是精神上的一种荒芜和落寞。所以在中国的农村,如果说这种养老保险,再没有大的改变的话,我觉得再下个十年,可能问题更大。因为这些老人已经精疲力尽了,也带不动孙子了,他的孩子还不回来,那他怎么办?所以是有很大的问题。
高希:印度也是,像今年,农民自杀在印度是已经变成传统了。今年已经有几千个农民自杀,这个现象我觉得可能之后只会加剧。
徐则臣:我有一个朋友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对印度、埃及的,包括对中国的一些乡村问题很感兴趣,谈到了乡村的现实,乡村的一个精神结构,文化跟经济发展一个关系,正好我跟他聊了,我说《在古老的土地上》谈到穆斯林,最严苛的一天要做五次礼拜,其实印度有一些宗教也有非常严苛的礼仪制度。
然后我的朋友就说,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经济的发展跟宗教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冒不冒犯,如果觉得可以的话,高希先生谈谈这个问题。
高希:关于农村和宗教,经济发展和宗教的关系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但是至少有如下的这个观察,:在埃及的时候,其实农村,包括在印度,在农村地区的那个宗教,人是虔诚的,但是人不去表现得很虔诚,而那些希望表现得很虔诚的那些观念,其实恰恰来自于那些去了城市读书,然后又把一些比较外在的表现,其实也有一种极端化的倾向的,把那种宗教的观念带回农村,其实这个恰恰是一种外来的而不是内在于农村本地的一种对宗教的态度。
而事实上你看到那些贫困的地方,其实它并不一定,而且往往并不出产那种宗教的极端分子,而恰恰是在,像沙特那样子的,有非常多的富人的地方会生产出宗教上的极端主义。
徐则臣: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因为在这个本书里面提到一个人,没事就看手表,没事就看手表,一天要做五次礼拜。然后去年我去了一次斯里兰卡,参观了几个宗教的圣地,有很多人,我们就跟他聊天。整个斯里兰卡人的幸福指数非常非常高,因为可能有宗教,有各种的原因,精神生活很富足,但是整个经济不是那么好,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或者是没有宗教的一帮人,我们就很好奇,问他们,如何解决精神生活跟物质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们觉得说无所谓,每天起来,吃完饭就开始隆重的宗教仪式,他们觉得很富足,然后我们一个朋友就说到了经济如何发展。我有这样的疑问。
高希:是的,因为发展这件事情是需要不满足和不满现状来作为一个前提的,就像英国人刚去尼日利亚的时候,他们其实分给当地人两倍的土地,但是发现尼日利亚的人只耕种一半,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些土地就足够了,所以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需要两辆车呢,还是你需要一种对当下的满足。
本书的完整活动实录,请移步三辉图书的小站,感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