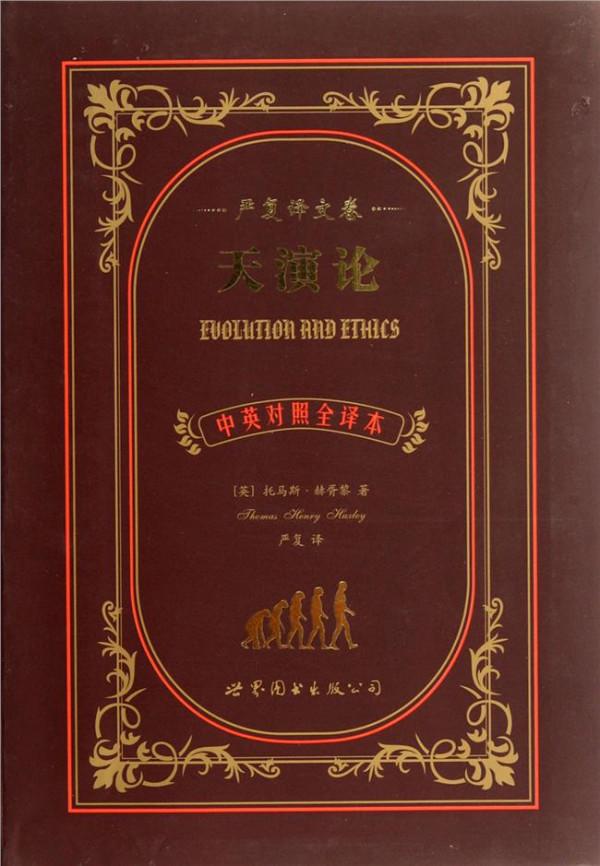严复天演论时间 《天演论》版本时间考析两题
论一:据现有史料来看,持《天演论》于1895年译成、出版这一观点论据有:一、严璩著《侯官严先生年谱》云:“乙未(1895)府君四十三岁。自去年夏间中东挑衅,海军既衄,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次失守。至是年,和议始成,府君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
先从事于赫胥黎T.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未数日而脱稿。桐城吴丈汝纶,时为保定莲池书院掌教,过津来访,读而奇之。
为序,劝付剞劂行世。是年复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群韩》诸文,均刊于天津《直报》。”(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548页。)二、陕西味经书院的《天演论》刻本,今藏于陕西省图书馆。一册,封面题“天演论”,扉页竖书两行,题“光绪乙未春三月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
论二:邬国义先后在1981年第3期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及1990年第3期的《档案与历史》上发表文章认为上述论说不能成立,因为陕西味经本《天演论》“卷下”“论三”中出现“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即1896年)”字样,“陕西味经本《天演论》是未经严复修改的初稿印本。
”(注:邬国义:《〈天演论〉陕西味经本探研》,《档案与历史》1990年第3期。)汤志钧的《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中所举论据与邬文基本相同外,还进一步指出:“‘味经本’《天演论》是叶尔恺接任陕西学政后送交‘味经售书处’印行出版的。”(注:汤志钧:《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为了弄清《天演论》卷上、卷下翻译时间次序,笔者将陕西“味经本”《天演论》与手稿本、英语原著逐一核对、比较,发现:
其一,陕西味经本《天演论》的卷上、卷下,不同于赫胥黎原文序论及牛津大学讲演稿时间次序。1893年,赫胥黎应罗曼尼斯讲座之邀,前往牛津大学主办自该讲座创办以来的第二次学术演讲,由于听众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与文化品位,故1893年赫氏讲得颇为深奥。
赫氏讲演因此受到许多批评,“对我批判的人当中,不少人使我深为感激,他们细心地注意到了由于我忘记了关于通俗演讲的一句格言,使我的表述受到了妨碍,恐怕甚至受到了削弱。
”(注:《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译:《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页。)1894年,赫氏接受了批评意见,“为尽力弥补我的过错,我在那篇讲演前加了一篇引言,内容主要是居于基础性的或重复性的东西,对此我加上了‘导论’(Prolegomena)这个标题。”(注:《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译:《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页。)
对于导言与讲演稿之间的关系,赫氏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有人认为我增添到大厦上去的这个新建筑物(导论——笔者注)显得过于巨大,我只能这样去辩解:古代建筑物的惯例是经常把内殿(演讲稿——笔者)设计成为庙宇最小的部分”(注:Issued in Evolutionary Ethics,Edited by Paul Thompson,1993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3.
)。导言篇幅虽较浅显易懂,但篇幅远大于讲演稿。关于讲演稿,笔者2001年11月从北京图书馆中发现选编者对材料来源作了说明:Published version of his 1893:The Romanes Lecture.
From:Evolution and Ethics(注:P46-86.)(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4).这说明讲演稿于1893年已单独公开发表过。
由1893年讲演稿及1894年序言组成的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收入《赫胥黎文集》第9卷。对此,笔者存疑。学界普遍认为严复翻译《天演论》所依据的原著底本系《赫胥黎文集》第9卷。
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检索到1894年曾印行Evolution and Ethics单行本,说明1893年讲演稿及1894年序言曾合在一起发行过单行本。严复翻译《天演论》所依据的原著底本也可能是后者。
严复在翻译Evolution and Ethics中先译的是赫胥黎1894年所作的序言部分,之后才是赫氏于牛津大学讲演稿。考释如下:《天演论(味经本)》卷下(即1893年牛津大学讲演稿)论十六:“今非谓如卮言之所云云,择种留良其事之必有所窒也。
”卮言,指赫胥黎于1894年所作Prolegomena(现代汉语可译成“绪论”,严复后接受吴汝纶建议,改为“导言”。)这一点严复手稿本也和陕西味经本完全相同(注:严复:《天演论(手稿本)》,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470页;王庆成主编:《天演论汇刊三种》,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版,第72页。
)。可见,严复翻译“卮言”在前,翻译“论”在后。即译完1894年赫胥黎所作的导言之后,再译1893年为牛津大学讲座写的讲演稿。严复翻译两个部分的先后次序在时间上与赫胥黎写作时间次序正好相反。
1898年慎始基斋本改为:“所谓择种留良,前导言中已反复矣,今所谓蔽,盖其术虽无所窒用者,亦未能即得所期也。”(注:严复:《天演论》,欧阳哲生编校:《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查英语原著:There is another fallacy which appears to me to pervade the so-called‘ethics of evolution’.
It is the notion that because,on the whole,animals and plants have advanced in perfection of organization by means of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nd the consequent‘survial of the fittest’,therefore men in society,men as ethical beings,must look to the same process to help them towards perfection.
I suspect that this fallacy has arisen out of unfortunate.Ambignity of the phrase‘survival of the fittest’.
Fittest has a connotion of‘best’,and about‘best’there hangs a moral flavour.In cosmic nature.
However,what if‘fittest’depends upon the conditions.(注:Thomas H.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seeing Evolutionary Ethics,editors:Matthew H.
Nitcki and Doris V.Nitecki,1993 S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laza.
N.Y.12246,P132.)(据我看,还有一种错误存在于所谓“进化的伦理之中”。就是这种说法认为,既然从全体上来说,由于生存斗争和因之而来的“适者生存”,动物与植物进展到结构上的完善;所以在社会中,人们作为伦理的人,必须求助于或寻求同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趋于完善。
我怀疑这种错误是从“适者生存”这一词的词义上的不幸的含糊不清引起的。“适者”含有“最好”的意思。而“最好”又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味。可是在宇宙自然界,什么是“最适应的”有赖于各种条件。(注:《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第56-57、1、1页。))
从赫胥黎原著中看不到“卮言”、“导言”或类似的意思,更谈不上从中窥探出“导言”或“卮言”与牛津大学讲演稿时间次序,但严复有意识的行文,向我们提示了两者时间次序上的先后关系。
1901年富文本以及1905年商务本,均将上述引文“所谓择种留良……”数句删去,表明严复后来也觉不妥,即导言实际上在讲稿之后,若不是讲稿难懂,赫胥黎受到批评,赫胥黎用不着写导言。更何况1893年的讲稿怎么可能提及1894年作导言?
严复之所以先译赫胥黎绪论部分,他在1898年正式出版的慎始基斋本所作《译例言》中作了说明:“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查陕西味经本与手稿本绪论部分都未加案语。因此,严璩说其父1895年经甲午战争刺激,“未数月而脱校”,有可能指译完赫胥黎1894年所作的序论部分,而不一定是1893年用于牛津大学的文字艰深、内容庞杂的讲演稿。
1899年3—4月间,严复在《与张元济书》中说:“承示欲印密克《教案论》,甚善!此书前经合肥饬译,鄙处之稿,不记何人借去。书衡比部既有抄本,正好付印。但此书尚是一人一时见解,不比他种正经西学,其体例不尊,只宜印作小书,取便流传足矣。
尊以旨谓书式欲与鄂刻《天演论》一律,此自无可无不可。盖后书亦不过赫胥黎绪论之一编,并非天演正学;且所刻入卢氏《慎始基斋丛书》,作为一种,我们固不必墨守其式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25页。
)严复在《支那教案论》“提要”中称“原书成于光绪十八年”(注: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版,第238页。)。该书严复于1899年译成,是年4月由上海南洋书公学译书院出版。
信中“赫胥黎绪论之一编”非指1894年赫氏写的绪论,比照“Evolution & Ethics and Other Essays.pp.v-ix,1-116,are reprinted with minor format changes from Collected Essays[1894]1898.
Vol.Ⅸ.London:Macmillan.
The Latin and Greek quotations,but not the French,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注:Issued in Evolutionary Ethics,1993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30.
)(笔者译文:《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论文》中第v-ix,1-116页是从1894年版及1898年版的《短文集》中节选来的,版式上稍作修改即重印。
除法语外,征引的拉丁及希腊语皆译成英语。)在参照赫胥黎作的Preface(序言)中的“The discours‘Evolution and Ethics’,reprint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present volume,was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as the second of the annual lectures founded by Mr.
Romanes”(注:Issued in Evolutionary Ethics,1993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30.
)(重刊在这本论文集前半部里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指此译本的后半部],是我在牛津大学的讲演。他是罗马尼斯先生创立的那个讲座的第二次年度讲演(注:《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第56-57、1、1页。
)。)《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还在“这本论文集”后作一注脚,称“原书包括著作的五篇论文,书名是《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现在这个译文只包括两篇论文——译者”(注:《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第56-57、1、1页。
)。其他三篇论文为:Science and Morals(《科学和道德》),Capital——the Mother of Labour(《资本:劳动之源》)及Social Diseases and Worse Remedies(《社会病及其恶性修复》)。
可见《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译文出现了歧义。原著中reprint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present volume是作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修饰The discourse‘ Evolution and Ethics’这一同位语的。
即《进化论与伦理学》作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前半部分出现,“其他论文”即指笔者文中列举的三篇。这三篇与赫胥黎在牛津大学的讲演稿及后来的导言关系不大,“现在这个译文只包括两篇论文”可能会误导读者,造成读者误认为《进化论与伦理学》还没有译完,还有其它论文。
这一点严复认识非常准确,“绪论之一编”表述也很清楚。这也说明严复在译《天演论》中,也读过赫胥黎的Preface。味经本卷上包括“卮言一”至“卮言十八”;卷下自“天演论一”以后,署“论二”,至“论十七”。由此可见,味经本的发稿者对“卷下”有“天演论一”说法也是十分清楚的。
下文对味经本《天演论》出版者略作分析。
实际上,1897年前后,叶尔恺、刘古愚及“院中诸生”不但读过《天演论》,而且校勘并出版陕西味经本《天演论》,史实如下:
严复在丁酉(1897)四月十七日,“于案上闻炮声,知其(俄罗斯使人胡王)至也。”(注:王庆成主编:《天演论汇刊三种》,第118页。)叶尔恺在给汪康年信中说:“然十四、五、六、七四期之报《时务报》,弟亦未得阅,此时谅也无从索补矣。
报中文字,愈加精警,提撕警觉,殊具苦心,《辟韩》一篇,尤与鄙人夙论相合,甚佩甚佩……俄使今日入城,当轴者懦懦焉,惧其有所要求,不卜究竟如何?”(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9页。
)此信日期注明四月廿日,与“四月十七日”相差不远,可见叶尔恺手头无《天演论》手稿本。此信还表明他对严复著作颇为关注。是年(1897)叶尔恺就任陕西学政,“九月廿八自京动身,初四抵三原,初七接篆”(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473、2472、2474、2475、2476、2477、2476、2477页。
),叶对出版行业颇为重视,赴任时曾托汪康年办理有关印刷设备,“如石印、铅印机器价值若干,可否设法运秦”(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473、2472、2474、2475、2476、2477、2476、2477页。
)。就任后,叶在致汪信中说:“此间举人萧钟秀赴沪,为复人邠学会考察汽机采办活字机器,经弟札委,到沪后,一切尚望费神招呼指教为幸。
”(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473、2472、2474、2475、2476、2477、2476、2477页。)叶尔恺任陕西学政时的其他信札还表明他准备出版一些书刊,尤其是西学方面(注:“弟以格致之学现虽无器具,亦当先涉其书,明其理。”参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476页。)。
叶尔恺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一日信中说:“味经书院所刻书可为捧腹者甚多,或字本古体必改从俗体……陋至此”(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473、2472、2474、2475、2476、2477、2476、2477页。
)。“弟前发味经刻《天演论》一书,所校各节,极可发噱……句法之古奥近子者必以为有脱讹字,或径增改原句读,以求文理之平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味经每刻一书,其初校之笑话,必须逐一签出,甚是淘神,而刘及院中诸生或竟大惑不解,反不能无疑也。
总之,此间人士除八股外,直不知有他书(得见《輶轩者》不过十年)。一言以蔽之曰,陋而已矣。”(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473、2472、2474、2475、2476、2477、2476、2477页。
)有学者认为味经本《天演论》乃是叶尔恺主持的(注:汤志钧:《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此明显不妥当,因为叶不可能在致汪康年的信中书自己主持的《天演论》校勘如何不好,那岂不是自己骂自己?由此看来“弟前发味经刻《天演论》”中“发”当作“邮寄”,而非“主持”。
信中又说:“刘古愚孝廉其人……惟服膺康党甚至,是其无识之处”(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473、2472、2474、2475、2476、2477、2476、2477页。),“刘”即“刘古愚”,从信中言辞可知康梁变法已失败。
叶尔恺写此信时,刘古愚参与的味经本《天演论》已完成,且刘古愚已经被味经书院辞退,“现刘已辞退,明岁味经延请何人,尚未定也。”(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473、2472、2474、2475、2476、2477、2476、2477页。
)此信末尾署“十一月二十一日。(已新正廿四日收)”(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473、2472、2474、2475、2476、2477、2476、2477页。
)结合戊戌变法失败及时间“已”,可断定“已”当指“己亥”(光绪二十五年),故叶尔恺写信日期当在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叶尔恺信中言论为考析味经本时间提供了参照系。从信中可见味经售书处《天演论》时间初步可定为1897年8月至1898年年底间。
下面结合手稿本修订时间,对味经本出版时间作分析。严复在手稿本自序注有时间“丙申重九”(注:严复:《天演论》(手稿本),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412、1438、1453、1476、1442-1445页。
)(1896),在手稿本卷上结束(也即卷下论一之上),注有:“丁酉四月十七日删节 复识”(注:严复:《天演论》(手稿本),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412、1438、1453、1476、1442-1445页。
)。论八完注有“丁酉六月初三日删节讫”(注:严复:《天演论》(手稿本),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412、1438、1453、1476、1442-1445页。)。在“丁酉四月十七日”与“丁酉六月初三日”之间未有其他日期。
《天演论》全书末尾,严复有按语,称:“斯宾氏至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注:严复:《天演论》(手稿本),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412、1438、1453、1476、1442-1445页。)斯宾塞生于1820年4月27日,76岁当为1896年,故此按语当写于1896年。
味经本论三中有包括“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在内的大段内容(注:王庆成主编:《天演论汇刊三种》,第38-41页。),手稿本将包括“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的大段内容(注:严复:《天演论》(手稿本),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412、1438、1453、1476、1442-1445页。
)删去,当证明严复在修改手稿本时,时间上已非1896年。再有手稿本删改此节注有时间,已是1897年所为。比较前后的日期,当是“丁酉十七日”至“丁酉六月初三日”之间删节。
这从侧面表明味经本卷下出版时,可能并未看到丁酉四月至六月间严复的手稿修改本。否则,味经本当中也有相应的改动。一句话,味经本“重刊”(注:《天演论》(陕西味经本)封面题“天演论”,扉页题“光绪乙未春三月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光绪乙未,为1895年。参见王庆成主编:《天演论汇刊三种》,第1页。),《天演论》当在此前后出版。
陕西味经本《天演论》扉页上的时间不可信,邬国义已指出陕西味经本《天演论》“卷下”“论三”中出现“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即1896年)”字样这一论据外。笔者发现封面题“天演论”的陕西味经本,扉页题“光绪乙未春三月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注:光绪乙未,为1895年。
见王庆成主编:《天演论汇刊三种》,第1页。)中有方框线,横约一寸,竖约三寸。竖书两行“光绪乙未春三月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字号相当于小一号,字型明显有别于正文的宋体字。
此处时间有明显的作伪痕迹,主要是“绪”未作“緒”,“陕”未作“陝”,“经”未作“經”。当时人绝不会用后来的简化字。因此,这个时间是靠不住的。有论者认为陕西味经本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本子”(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317、515页。
),此结论现在要重新考察。正文第一页右上顶格书:“赫胥黎天演论卷上”,第二行右下有“侯官严复学”。与《天演论》后来本子比,味经本此中表述方法说法与后来《天演论》众多版本比较,属少见。
扉页题“光绪乙未春三月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作伪者署此时间作何解释?联系严复作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0月前后《与梁启超书》说:“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317、515页。
)严复将稿子寄往何处?首先,梁启超当是很清楚,否则严复会在信中有所交代。要不然,突然来这么一句话就很让人感到意外。“原稿”当指既无吴汝纶序言,也无自序,更无译例言。而这些正和陕西味经本《天演论》完全相符合,可见两者联系绝非偶然。笔者以为严复致梁启超信中提及《天演论》“原稿”(注:信中相关的内容见本文后半部分。)中可能署有“光绪乙未春三月”。
梁启超通过刘古愚的学生李岳瑞认识刘,李岳瑞与时务报馆联系密切。梁启超、汪康年等主办的《时务报》第一册刚发行,1896年9月1日,汪大燮致汪康年称:“前得信后,久未见孟符,所事未能商办。嗣孟符交来第一次报,言有卓如信而未交到,阅之甚为欣忭。
”(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46、746、746、750页。)“嗣见报快甚,孟符言宜得上谕置之论序之言,此言也甚有理,《申报》不足法也。何不稍改体例,以完璧”(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46、746、746、750页。
)。汪信中又称自己在京只是“译仆人”,而“孟符译署已传到,亦未有暇,渠却未言不管,而其忙碌情形,以可见也。”(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46、746、746、750页。
)后汪又致信汪康年称:“孟符所销极为有限,倘各路如此,则垫本不敷矣,甚为悬念。”(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46、746、746、750页。)《时务报》第三册公布了各地代收款者名单,京城即为陈炽、李岳瑞。
1896年(注: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称该年著有《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时在1896年,梁赠书当在1897年。)刘古愚致信给《时务报》报馆的梁启超:“今命杨孝廉蕙、陈孝廉涛、孙茂才澄海游沪郢择购机器。
杨孝廉等虽非奇特之士,然皆有志者,愿足下进而教之,毋吝裁成也。”(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105页。)梁启超将自己及康有为著作寄给刘古愚,“是年,先生又收到陕西刘光蒉(古愚)两书,他在《复刘古愚山长书》中,对于在陕兴学、致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同时,将南海先生撰《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四上书记》,及他自撰《西学书目表》赠刘。
”(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105页。)梁启超致刘古愚信有关译事强调甚多。笔者认为刘古愚很有可能通过梁启超向严复索观《天演论》,并在自己主持的味经书院翻印。
另一方面,作伪者署“光绪乙未春三月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还可能知道严复动手翻译《天演论》英文原著的时间,有旁证:严璩著《侯官严先生年谱》云:“乙未(1895)府君四十三岁。自去年夏间中东挑衅,海军既衄,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次失守。
至是年,和议始成,府君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于赫胥黎T.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未数日而脱稿。”(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548、1410页。
)所谓“重刊”可能是作伪者知道味经书院刘古愚等出版《天演论》前,1897年前后《时务报》馆已经出版《天演论》,这一点参见下文叶瀚致汪康年的书信,时务报馆刊印的《治功天演论》在前,陕西味经本可能据此称“重刊”。
二、《赫胥黎治功天演论》流传时间考析
《天演论》曾一度命名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在知识界流传。《赫胥黎治功天演论》流传及其时间,学界并不清楚。笔者下文对此考析。
梁启超撰于1897年的《论译书》有两处涉及《治功天演论》:“欲通西学者,必导原于希腊、罗马名理诸书,犹欲通中学者,必导原于三代古籍、周秦诸子也。旧译此类书甚寡,惟明人所译,且语多洁屈。近译者,有《治功天演论》、《辨学启蒙》等书。
(《几何原本》、《奈端数理》等为算理之书,算理者,理学中之一种也。)”(注: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329页。)“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
然必译书者之所学与著书者所学相去不远,乃可以语于是。近者严幼陵新译《治功天演论》,用此道也。”(注: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329页。
)查严复在修改《天演论》手稿过程中曾把书名译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天演论》手稿之自序原题“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548、1410页。)就可证明这一点,序后注有日期:光绪丙申重九。严复手稿中译例有:
一、书中所指作家古人多希腊、罗马时宗工硕学,谈西学者所当知人论世者也。故特略为解释。
一、是译以理解明白为主,词语颠倒增减,无非求达论者深意,然未尝离宗也。
将上文所引与梁的论述对照,不难发现梁氏论及翻译理论的表达中有严复话语的影子。而严复正式发表在1897年12月18日《国闻汇编》第二册上的序言是(《译天演论自序》(注:《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I),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07页。),与手稿本中《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标题有异。据此,梁启超不仅看过未发表的《天演论》,且对丙申重九严复所作序言以及译例已了解。
除梁启超外,史料表明孙宝瑄也读过《治功天演论》。孙宝瑄在1897年闰十二月初二日记说:“诣《蒙学报》馆,晤浩吾(注:叶瀚,字浩吾,浙江仁和人,与孙宝瑄、汪康年有同乡之谊,时任《蒙学报》主编。叶瀚著有《尊圣论》等,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论教,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以归,即严复所译者。”(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第155页。)此处《天演论》被称为《治功天演论》,可能是1896年的手稿本或以此为底本的传抄本。
当然,孙宝瑄在《蒙学报》报馆借到《治功天演论》,这正说明严复本人作为《国闻报》及《国闻汇编》的发起者,其与报界等媒体接触、联系较多。蒙学报创办之事见于《蒙学公会公户(并简章)》,载于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897年10月16日)《时务报》第42册,署名为“仁和叶翰、钱唐(塘)汪康年、湘乡曾广铨、吴县汪钟霖同启”(注:《时务报》第44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3辑·时务报》,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898、2977-2988页。
),其目的“……蒙学公会务欲童幼男女均沾教化为主。”(注:《时务报》第42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3辑·时务报》,第2893页。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1897年11月5日)梁启超在第44册《时务报》上发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注:《时务报》第44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3辑·时务报》,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898、2977-2988页。
),后转载于《集成报》第21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梁启超称“教小学教愚民,是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
启超既与同志设《时务报》,哀号疾呼,以冀天下之一悟。譬犹见火宅而撞镜,见入井而怵惕,至于所以救焚拯溺,切实下手之事,未之及也,既又思为学校报,通中西两学,按日而定功课,使成童以上之学童诵焉,自谓得此,则于教学者殆庶几矣,而于教小学教愚民二事,昧昧思之,未之逮也。
岁九月归自鄂,而友人叶君浩悟、汪君甘卿,有蒙学报之举。”(注:《中国近代期刊丛刊·集成报》,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册,第1180-1181页。)
孙宝瑄与叶瀚主持的蒙学报馆这一舆论信息发散中心联系密切。《蒙学报》为周刊,其和上海时务日报馆有着亲缘关系,从现存刊物来看,有1—72期,时段为1897—1899年(注:《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849)》,北京图书馆1961年版,第1192页。),其时蒙学报与时务人马基本一致。
1896年严复在上海曾请梁启超看过《天演论》手稿。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记录:“(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梁启超)二十四岁。……马眉叔先生所著之《马氏文通》,与严又陵先生所译《天演论》,均以是年脱稿,未出版前,即持其稿以示任兄。
”(注:《戊戌变法》(四),神洲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178页。)是年10月前后严复《与梁启超书》说:“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梁启超撰于1897年的《论译书》一文中,称《天演论》为《治功天演论》(注: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第325页。
),和孙宝瑄所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书名完全相同,再联系梁启超与《时务报》、《蒙学报》馆的关系,可以认为通过梁启超时务报馆得以出版《治功天演论》。
时务报馆出版《治功天演论》事见1897年6月6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七日)叶瀚致信汪康年:“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已否付印?如印就,乞各寄一部”(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582页。)。孙宝瑄通过《蒙学报》报馆主编叶瀚得到《治功天演论》。孙宝瑄手中的《治功天演论》可能是梁启超读的《治功天演论》。
孙宝瑄日记中1897年闰十二月“初四日,晴。暮归,览《天演论》。《天演论》宗旨,要在以人胜天。世儒多以欲属人,而理属天,彼独以欲属天,而理属人。以为治化日进,格致日明,于是人力可以阻天行之虐,而群学乃益昌大矣。
否则,任天而动,不加人力,则世界终。古争强弱,不争是非,为野蛮之天下。其说极精。……天演之学,始于额拉吉来达,嗣传其学者曰德谟吉利图,中稍变于斯多噶。盖额拉,周景王时人,为欧人智学之祖,大旨以变言物,故谓万物有已过、未来而无现在,与中土《易》理合。
《易》之既济,即额拉之已过、未来也。又以火化为天地之秘机,以为万物皆出于火,皆入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毁灭。此理盖得今日之化学而益明也。(严复所论。
)德谟者,生于春秋定、哀间,以富人子游学,尽散其资,在古人中最先创莫破微尘之说者,近代化学宗之,而阐合质定率之理焉。至斯多噶之徒,始创为造物主宰,以为无不知,无不能,盖近婆罗门八明之论,而额拉氏所未言者也。
”(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第155-156页。)文中称“严复所论”可见孙宝瑄手头的《治功天演论》本子肯定不是1895年陕西味经售书处的重刊本,因为味经本上卷尚无严复按语,也无严复的序言;更不可能是1897年《国闻汇编》中的《天演论悬疏》,因为书的标题不一样。
也不是通过吴汝纶的《天演论》笔录本,丁酉二月初七日(1897年3月9日)吴汝纶在致严复信中就说:“吕临城来,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
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大著恐无副本,临城前约敝处读毕,必以转寄。”(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560页。)所以,孙宝瑄所读当是1896年左右的《天演论》手稿本或副本,也即1896年左右的《天演论》手稿本曾经一度命名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
总之,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只有建构在准确的历史复原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有所发现或合理地诠释,而史料考析本身可以真实地展示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避免根据研究者自己的学术逻辑去裁减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