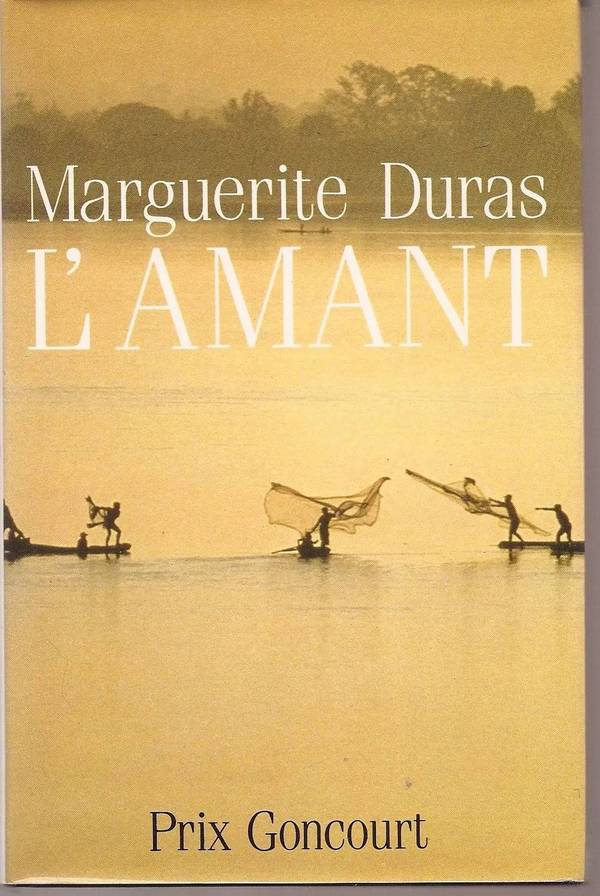于佩尔的<她>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编者按: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的演技毋庸置疑,她总是能够精准地处于自己正在饰演的角色状态当中。所以当于阿姨在两部戏之间尬戏时,尤其是在塞吉·波宗和迈克尔·哈内克两位大导之间穿梭时,她会如何平衡呢?2017年,似乎又是于阿姨霸屏的一年,将会有几部新片上映。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有趣的是,此时的于阿姨应该奔波于奥斯卡相关的各种公关活动中,她的海报被一次次用做最佳女主预测的背景板,让我们静静期待本月26号的结果吧!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记者:您现在正在里昂拍摄塞吉·波宗(Serge Bozon)的新片《海德女士》(Madame Hyde,2017),拍摄情况如何呢?
于佩尔:非常好。这是我跟他合作的第二部影片,第一部是《完美无缺》(Tip Top,2013)。塞吉·波宗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我必须追随他进入这种形式主义。如果我们有一些包含叙事、讲故事或是树立人物角色的惯常想法,我们很快会就会碰壁。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我们应当随着这种形式走。每天我都在重复这一点。他很专横,很明确。此外我总是不明白我扮演的是什么,也不明白我的台词是什么意思,因为我饰演的是一个科学教授——塞吉是数学家出身,很高水平的那种,因此他让我读很深奥的东西,但这可吓不到我。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谈到我时曾说过我没办法抽象地思考。即使表演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诠释手法,也同样是一种抽象艺术,这种抽象无法阻止对自身的多个方面的否认。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记者:像许多您曾在荧幕上饰演过的角色一样,海德女士也是具有双重性格的。饰演这样的角色有怎样的乐趣?
于佩尔:这里面女英雄“海德”的一面通过一系列特效表现出来,而这些特效并不是加在我身上的。这里把电影起源时的一些元素带了回来,同时也唤起了最纯粹的手工艺形式的拍摄手法。我们用的是老式放映机,它让人们想到了梅里耶(Méliès)。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我在这一阶段能从中看到的很有限:它是一种关于电影转变能力的思考,以及令人相信人为手法的意愿。这些方面由技术来负责,我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而没有过多地想这类问题。波宗仍然给了我很多差不多是心理上的指示;可以说他树立了一个性格。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对他来说,海德女士象征着力量和危险。她能够变出火焰,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她能引发大灾变。我能想象这部影片讲述了许多有关这一视角的东西。这些对立的力量是如何引领我们和整个世界的?波宗的电影里总是有一些政治的元素在里面,尤其是它们都处于确定的世界中。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完美无缺》就身处于能够代表当今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而一直持续拍摄到11月11日的《海德女士》,也逃脱不了这一法则。
记者:今年夏天,您参与拍摄了迈克尔·哈内克(Micheal Haneke)的《快乐到死》(Happy end,2017)。您对他是如此忠实。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于佩尔:反之他对我也是…这是我们第四次在一起拍摄了。并且我们还没有完全拍完这部新片。我还得再赶去拍一场戏,因为装饰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影片叫做《快乐到死》,但是好像它最初是叫《快乐结局》,而且他给我们准备了惊喜!就像是撒了胡椒的蛋糕,其上的胡椒只有在影片最后一场戏才会暴露出来。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于佩尔谈新片《海德女士》:世界因为她的接触而熊熊燃烧" />
记者:这种在塞吉·波宗和迈克尔·哈内克的世界中来回穿梭会不会让人感觉不稳定?
于佩尔:不会的,因为只是回去拍《快乐到死》的一场戏而已。从组织筹划的角度来看有点儿复杂,因为我在晚上拍塞吉·波宗的电影,而第二天早晨我就要赶到迈克尔的片场。结果我睡眠不足。但是,不,这并不困难。在哈内克那边,我们是在工地上拍摄。
只是不太好找布景而已。那是一场和“我儿子”的戏。我饰演的角色是一个家族企业的头儿,但是她自己听命于她的父亲,由简-路易斯·特林提格南特(Jean-Louis Trintignant)饰演。
我准备好和我的儿子共同带领公司,但是他在某种意义上有些脱离社会并且精神失常。我的角色出身于法国北部的一个大家族,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家庭,在经济和感情上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家庭成员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
此外我们还在杜埃发现了一幢特别的大别墅,里面仍然住着些大家庭。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电影并没有困扰我。印度的演员们在宝莱坞经常这么干。听说他们一天要拍七部电影,从一个片场到另一个片场。我有点儿像是一个“宝莱坞女演员”!(笑)
记者:迈克尔·哈内克以讲述封闭世界而闻名,观众和演员们经常会被囚禁其中,您在他的封闭体系里面能尽情释放吗?
于佩尔:他有一种超凡的场面调度能力。封闭体系,对于它本身我并没有什么大的感觉,它能够延伸到无穷远。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大师级电影人。迈克尔·哈内克的电影往往都描绘出很微妙的情境,比如在《快乐到死》中,有一些群戏,各种角色都会在场。
他把他们掌握地恰到好处。您可能会说这对于一个电影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人们能在他身上看到一种对于背景乃至剪辑的严谨的思考。这在其他一些导演身上我们并不能如此切身地体会到这点。
但是在哈内克身上,他会将这种特质分享给整个团队。我们看着他寻找最准确的背景。在《快乐到死》里面,这些甚至让我更加震撼。他总是在剪辑中审视他的影片。他有着一种昆虫学家的精确,不允许出现任何偶然。他强迫性地在贯彻这些。
记者:您也参演了巴沃·德弗恩(Bavo Defurne)的电影《纪念》(Souvenir,2016),这部影片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映。
于佩尔:在这部影片里我饰演一个沦落为馅饼工厂女工的歌手。但是得益于一个年轻人(凯文·艾泽斯 Kévin Azaïs饰演),她借助唱歌重获新生,这位年轻人为她的事业助了一臂之力。这是一部完全风格化的情节剧,似乎只有弗拉芒人才能做到。
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影片很成功。我已经能从情节上感觉到这点:所有这些在馅饼工厂和歌唱之间的不协调元素都写实而富有诗意,正如情节剧能呈现出来的那样,从一边到另一边的过程被掌握得很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