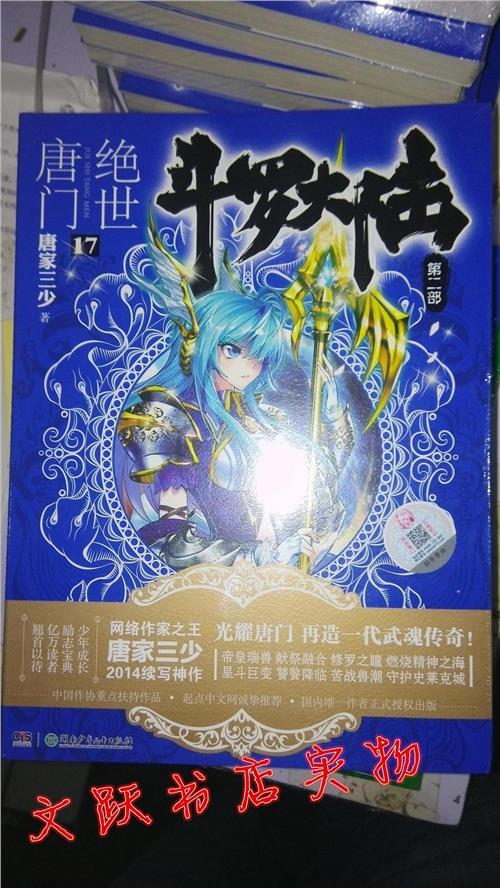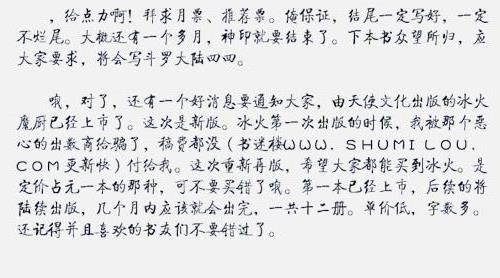倪柝声在监狱 第十八章 倪柝声弟兄在解放后至入狱前的工作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73-186页。)
1949年5月,倪弟兄看见时局越来越紧张,解放军正南渡长江,就从福州打电报,打发正完成会所督工的李常受弟兄赶快放下一切责任,坐飞机到福州,然后到台湾去。李弟兄离开一个月,政权就改变了。倪弟兄自己留在国内继续第二期的鼓岭训练。
下半年第二期训练到一半,解放军已进到福州。倪弟兄为应付上海教会面临的问题和生化厂正在酝酿的难处,就提前结束他在鼓岭的时间,回到上海解决问题。他回来以后,花了一个多月,处理生化厂债务。
债务清理后,我暂时从生化厂停下来。倪弟兄那时很关心今后在中国众教会的前途,很关心神的工作和弟兄姊妹的情况,所以想办法接触共产党要了解有关宗教政策问题。那时正好他的一个办药厂的好朋友,就是仁和药厂的老板黄肃丰认识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吴克俭。
倪弟兄就请黄肃丰介绍他去认识这个人。吴克俭与倪弟兄见面后就告诉他中共的宪法是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的,只要不犯法,政府不会干涉宗教信仰。
倪弟兄根据这话,以为国内还有几年可有自由传福音、建立教会。他把工作最后一笔款,设立了以琳印刷所、翠华染料厂和生化渝厂上海办事处,盼望借此帮助弟兄姊妹,可以带着职业事奉主。这一切想法都是全心全力为着主,也是为着教会,这是主所知道的。他所有的安排,也证明他决心留在国内,与众弟兄姊妹同艰苦、共患难。
次年1950年他有事到香港,在那里带领教会复兴,同工们当时都劝他不要回中国,对他说:“你进去由得你,但出来由不得你。”但他说国内有那么多弟兄姊妹,他怎能把他们撇下不顾呢?他以为他必须回去与弟兄姊妹站在一起,同受试炼,并尽他的力量解决问题和矛盾,同工们不管怎样劝,也不能改变他的定规。
所以3月12日他只身回中国。他回去是为着神的经纶、为着主的恢复、为着主和教会、为着福音的扩展、为着保护弟兄姊妹,甘心情愿受了许多的苦楚,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
他有一个心志,要与大陆的弟兄姊妹一同受苦。那时他对一个弟兄说,他清楚他的前途,不是被提就是殉道。他的回去使他成了矛头所指向的攻击对象,因此弟兄姊妹和教会也面临着更大的试炼。
下面我要说明自1950年3月到1952年2月这两年中,倪弟兄为着神的经纶、为着主的恢复,如何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像一把大伞,首先全心保护弟兄姊妹和在中国的众教会,包括在各公会里的弟兄姊妹;第二,要保护鼓岭山上的土地;第三,要保护青年弟兄姊妹在学校和各单位里不受共产党无神论思想的影响。第四,要保护教会的福音移民到边疆的行动;第五,要保护工作的款项。
一、与“三自”的来往
首先为着保护弟兄姊妹和在中国的众教会,包括在各公会里的弟兄姊妹,在西国传教士离开中国后,倪弟兄盼望在中国各公会的弟兄姊妹,能在合一的立场上,走上合一的道路。所以,他那时想如何能积极与西国传教士接触,另外也叫我们中间同工们,去跟公会里那些属灵派带头人,谈谈合一的问题。
倪弟兄本人认识很多传教士,他就主动去跟他们谈。当时内地会许多传教士也很赞成我们的路。倪弟兄也请一些与传教士关系比较好的同工,去跟这些传教士们谈。
结果在金华的内地会接受了我们交通,愿意他们离开后,他们的信徒由我们来带领。这样的情形在其它地方也有。同时他也叫同工们去接触与我们比较接近的属灵派弟兄姊妹。他知道我父亲跟乌鲁木齐路的杨绍唐牧师比较熟,杨从前属内地会,过去在上海各会堂领会时我父亲也有去过。
倪弟兄叫我父亲跟杨绍唐谈,又叫唐守临跟赵世光谈,因他们俩人很早就认识。他又叫缪韵春姊妹找上海灵修院的院长焦维真谈,因为缪韵春的妹夫焦华甫是上海德国领事馆翻译,他的妹妹就是焦维真。
倪弟兄又叫张愚之去北京跟王明道谈。王当时极力反对共产党,写文字要大家“战,战,战”。这些谈话的结果,杨绍唐说他早应跟我们在一起,但我们没有薪水制度,是靠信心生活,如果他到我们中间,生活会成问题,所以他就不来了。
赵世光说,他是传福音的,大家分工,他救来的人,就把他们带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喂养他们,这样他也不来。焦维真说,她是办神学院的,底下很多学生,所以也没办法到我们中间来。张愚之跟王明道谈也没有结果,王明道那时很激烈反对。所以,倪弟兄没有办法把这些比较靠近我们的团体说到走在一起。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在1950年9月份搞起来的。当时中国处在全国解放初期,美国打到北朝鲜,激起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爱国之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声浪越过越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即赴朝参战。
中国基督教过去是被中国人民称为“洋教”,因为它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帝国主义曾利用基督教来侵略中国,而有一些传教士,如马礼逊、伯驾曾直接参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到解放前夕,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扶蒋反共活动,如司徒雷登一面作传教士,一面作在蒋介石统治中国时的美国驻华最后一任大使。
美国传教士毕宇范作过蒋介石的顾问等。所以,过去在中国人民脑海中,认为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用来侵略我国的工具,将帝国主义和基督教混为一谈。
如1925年的“反基”运动,就是从反帝国主义引起的。现在又面临这一个问题,抗美援朝,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过去和美帝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基督教,怎么办?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但是基督教在全国抗美援朝声浪中今后的前途如何?最先靠拢党和政府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吴耀宗、刘良模等,还有圣约翰大学的一些新神学派人士如丁光训、李储文等,他们都是地下党员,曾在英美读神学,回来后李储文作了国际礼拜堂的牧师,丁光训则作了南京金陵神学院院长。
他们早年接触共产党,共产党也信任他们。他们于1950年春组织基督教访问团,了解各地教会解放后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并于4月合同一些京津基督教青年会人谒见周恩来总理,要求政府协助解决。
周总理提出今后基督教在中国要有出路,就只有割断帝国主义的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于是吴耀宗起草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又提出“三自宣言”,号召广大信徒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并号召基督教各宗派、团体“应拟定具体计划,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
到1950年9月份为止就有全国各地基督教负责人一千五百多名签名响应。
〈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将宣言及全部签名名单刊载,并发表社论予以支持。1951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会议上三自领导人揭发控诉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罪行,并发表联合宣言:“要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割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
三自爱国运动是个政治运动。1950年成立机构时称为“抗美援朝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后来有一些教徒对“革新”两字误解了,以为是要革掉我们的信仰,所以到1954年改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7月正式成立,这个组织是中国基督教界内部成立的组织,不是政府的机构,而是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领导的。
各大城市都成立了分会。上海也有分会,领导人大半是青年会派的人,如李储文、刘良模、尹裹、施如璋、李寿葆、罗冠宗,再加上几个老牧师如谢永钦、陈见真等。
1951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后,吴耀宗、刘良模等就回上海召集各大公会的教牧人员和独立性教会(包括聚会处)的传道人,一面要各宗派登记跟帝国主义的关系和接受他们多少津贴,一面在各大公会和独立性教会搞控诉美帝国主义的运动。
那一次倪弟兄也去北京参加了聚会。许多人都很注意他,他自己也知道他受注意。那时政府宣扬必须站稳人民立场。我们南阳路聚会处是由刘良模来领导的,但是遭到倪弟兄的反对,其理由是:第一,从1922年开始我们就已经脱离了外国差会和大公会,我们没有和任何差会、公会、外国宗教团体有过行政上、经济上、神学上的关系。
我们没有任何名称,只称自己在某某地奉主名的聚会。我们不需要礼拜堂,在家中就可以聚会。
我们没有雇用的牧师,同工没有固定的薪水,他们都凭信心生活。我们反对神学,话语的信息是直接从神启示而来,所以我们自称是土生土养的地方教会,不存在割断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将“接受帝国主义津贴登记表”空白退回去了,上面加上一个“非”字。
第二,倪弟兄认为,青年会派的人之信仰和我们不同,他们虽然挂上一个基督教的招牌,但是他们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们信耶稣是讲自由、平等、博爱,是社会改革家,来为人类救苦救难,为人类服务的。所以,倪弟兄认为按约翰二书的教训,这等人我们不能接待他们,也不能问他们的安,免得我们在他们的罪上有分,所以称他们为“不信派”。
我们将空白登记表退回去,不控诉帝国主义,和三自领导人对立起来。这就引起宗教事务局和“三自”对我们的怀疑,认为我们是对抗、隐瞒。他们经过调查后,找倪弟兄谈话,指出要他交待与1932年来上海的八个弟兄会外国人的关系,要他交待1933年和1938年,他两次去英国和史百克的关系。
倪弟兄回以弟兄会的八个外国人是来访问我们的,他们要我们成为弟兄会闭关派在中国的分会,遭到我们的拒绝,以“致英国罗福区弟兄会的一封公开信”为证。
至于和史百克的关系,也不过是在圣经亮光方面有同样的看见,并没有和史百克成立从属的关系,成立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关系。“三自”又要他控诉逃去台湾的李常受,认为他是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并且带了许多青年去。倪弟兄1950年一次在生化厂的办公室亲自对我说,他怎能控诉李常受弟兄呢?这怎能说弟兄彼此相爱呢?因这缘故,以后矛头就对着倪弟兄,想要控诉他。
刘良模等碰了壁,就想发动弟兄姊妹群众来搞控诉帝国主义。刘良模在幕后策划一个守真中学的学生,青年弟兄名吴维樽站起来控诉老诗歌第六十首。这首诗是倪弟兄写的,说到“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他一站起来讲,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手稿,弟兄姊妹都站起来责问,当时王大和很气愤,他眼睛睁大说:“这是控诉帝国主义,还是来控诉我们的信仰?”他的一副眼镜因太激动也跌地破碎了。吴维樽被吓得口瞪目呆,刘良模在后面坐着面红耳赤。
弟兄姊妹将吴维樽手中的手稿夺下,纷纷上台发言。那时有一位青岛来的中学校长,是在上海生化厂作事。而翟宗沛姊妹怕会出事,她研究马列主义很深,头脑也很清醒。她马上上台,叫大家安静,然后替大家作分析。这时刘良模在暗中溜走了。这样我们对“三自”对抗的局面,越过越深,此后青年会知道我们这么同心,也就不敢再来搞控诉运动了。他们称我们作“小台湾”。
倪柝声是否加入三自?
上海宗教事务局第一任的处长周力行又有一次在大会上讲我们反对三自革新运动,和青年会派搞不团结,说我们讲他们是不信派。周力行挥拳说,我一定要打垮“属灵派”。这就使大家有一个错觉认为“三自”是要来搞我们的信仰。
但是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凭着团结出发,在北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时,特邀倪弟兄去参加。国务院领导人在大会中谈到宗教政策时,强调宗教信仰自由;谈到割断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时,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站稳人民立场。
倪弟兄在会后向北京聚会处长老们发表了一篇谈话,后来回上海于1951年8月20、21日和9月12日,倪弟兄在南阳路大聚会所讲了三篇话,题目是:一、我是怎样转过来的。二、我们对于政治所应有的态度。三、走那一条路。1951年10月,上海教会把这三篇话,印成一本小册子,名为《我是怎样转过来的?》
在倪弟兄未去北京开会以前,他一面是自称早是“三自”,拥护“三自”,认为我们是早就赞成“三自”,就是自立、自传、自养的,一面为使弟兄姊妹不产生对“三自”有对抗情绪,还是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所以在1951年他发动全国聚会处四万多信徒联合签名拥护三自运动。
将原“破坏土改”的签名单顶了上去;“三自”另编了一本〈天风〉专辑,将所有名单都印上去。他所拥护的是“三自宣言”,赞成三自的原则。这不是说他拥护我们参加三自组织。
后来宗教局发现有问题,专辑就被压下不发行,但我在倪弟兄办事处亲眼看过这专辑。因为上海宗教事务局还是认为倪弟兄有篡夺“三自”领导权的阴谋,只有在政府领导下的“三自”,才是真正彻底的“三自”。倪弟兄的所谓“三自”是不反帝的,所以不能称数。
所以脱离宗派,不等于已经实行“三自”了。“三自”是要在反帝的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因为宗教局认为倪是有篡夺“三自”的阴谋,所以矛头就专对着他,要把他打下来。
倪弟兄究竟是不是要弟兄姊妹参加三自呢?不!他没有要大家参加三自。在一次同工、长老、执事聚会中,他说我们政治思想不能落后,政府不干涉我们信仰,但要我们站稳人民立场,他就拿盘子和杯子作比方,说盘子是政治立场,杯子里的是信仰,我们盘子要取人民立场,但信仰的内容不能改变。
倪弟兄所说的站稳人民立场是指政治上反帝说的,不是指加入三自说的。有人以为倪弟兄1951年所发表的〈我是怎样转过来的?〉是指他已同意加入三自,但他说的“转过来”是指转过来认识要站稳人民立场,是在政治上与政府合作,但他仍没说与三自合作。
1956年肃反时,上海宗教事务局罗竹风说,“如果倪柝声早参加三自,我们也不会定他为反革命,上海聚会处也不需要进行一次肃反运动了。
”这话证明倪弟兄虽然说思想转变过来,但是在他被逮捕以前还没有同意加入三自。他因为不同意加入三自,也不承认史百克和弟兄会等人是帝国主义,所以矛头就对着他。这是引至五反运动时他被逮捕真正的原因。
倪弟兄1952年被逮捕以后,围绕着参加三自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唐守临为代表的,主张加入三自。一种是以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为代表的,反对加入三自。他们反对加入三自的理由有以下几点:1.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属灵的,不能参加任何组织;2.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我们不能参加三自;3.参加三自是政教合一;4.我们地方教会已经脱离宗派,不能再加入宗派,所以不能参加三自;5.我们只能到工作岗位上去爱国,到里弄去爱国,不必在教会里爱国;6.参加三自就改变我们的信仰;7.尊重别人的信仰,就是碰了我们的信仰;8.参加三自如鱼入网,跳死为止。
唐守临和任钟祥加入了三自
1953年春,张愚之听到北京王明道坚决不参加三自,认为他很刚强,就去北京和王明道取得联系,吸取他的经验。1954年春,李渊如预先召集一些人为教会加入三自的问题祷告。当时唐守临是主张加入三自的,李渊如和汪佩真说:“如果教会参加三自,我就退出教会。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会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唐守临要去北京参加会议,但遭李渊如的阻挠,她坚决反对聚会处参加三自。后来唐守临决定要去,李渊如又劝他说:“如果你去,你必须说一点三自如何干涉我们信仰。
”唐守临去参加会议,他们叫唐坐在主席团席位上,但唐在小组内、外污蔑三自机构打击信仰,并一再为王明道辩护。唐守临从北京开会回来以后,李、汪知道唐加入了三自,并且作了主席团成员,知道他开始是坚决不做三自委员的,后来经过政府首长们耐心的教育和感化及三自的帮助,他思想转变了,接受了大会的盛意,担任了委员和常务委员;知道他想带教会走上三自爱国运动的路。
李、汪、蓝就说唐堕落了,出卖教会,并阻止弟兄姊妹去听大会的传达报告。
当时任钟祥从三自爱国机构领取了1400份告全国同道书,他和唐预备发给聚会处全体信徒,结果被强迫退回。1954年10月,汪、李等要聚会处的长老写信给宗教事务局声明退出三自,不同意唐担任三自的委员和常务委员,并对唐说他没有得大家同意加入三自,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大家,要做三自委员就不能做教会长老,张愚之也天天催逼他辞去三自常委。
宗教事务局罗竹风处长几次召集同工、长老去谈话,讲三自的意义,但是由于同工,长老不同意,唐于1955年春写信给三自辞去委员和常务委员之职,退出了三自。
以后罗竹风处长又私下找唐去公园谈心,劝他加入。他又改变主意,加入三自。这就是日后说的对三自的“三进三出”。当时普遍弟兄姊妹里的感觉,都不同意参加三自。
1955年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三自争取聚会处派代表去参加,结果被蓝志一拒绝了,不准聚会处产生代表出席会议。后来,罗处长愿意到我们中间来讲一次话,李、汪不让罗处长和弟兄姊妹见面。
当李渊如听到罗处长在一次报告中说要了解聚会处信徒到底是否反对参加三自的消息以后,李、汪就叫执事们到各分家去,将不参加三自的几点理由讲给信徒听,教大家背出来。这从政治上来看,她们这样做已经构成了破坏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
1955年10月北京阎迦勒发表了一篇谈话〈样样都看清了〉,他表示加入三自,参加政协学习班,李、汪大为惊讶,纷纷写信责备他。这是在聚会处肃反前夕的事。那时情形十分作难,因为同工们当中并不同心。10月份,王明道被捕,三自要大家学习他的检讨书。许大卫早在1954年被逮捕,留在看守所。
二、申请保留鼓岭土地的前后
1956年2月,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进行肃反的时候,在定“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许多罪行中有一条罪行就是“破坏土改”。
胜利以后,倪弟兄结束了在重庆的生化厂而回福州去。在福州郊区有一座山名叫鼓岭山,在这座山上有许多西国传教士盖的小洋房,还有一些土地,租给当地农民种的。西国传教士盖了这些房子作为避暑和休养之用。1948年倪弟兄得悉在鼓岭山上的西国传教士都要回国,他就用很便宜的价格,将所有的房子和土地都买下来,预备将来栽培同工之用。
1948年下半年,全国基督徒聚会处主要同工在上海开了特会,将自己交出来后,倪弟兄就叫他们报名,上鼓岭山“执事之家”,参加为期半年的短训班。第一期结束后,1949年又办了第二期短训班。1949年下半年两期的短训班都结束了,倪弟兄就回上海,一面经营生化药厂的事,一面在聚会处应付在上海解放后,教会面临的一些难处。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以后,倪弟兄在江西路生化药厂办事处看到〈解放日报〉头版大字,那时我也在场。他说:“土地改革法中有一条是寺院、庙宇和教堂的土地免于改革,政府是相信群众的,只要我们全国聚会处四万余人联合签名,申请政府将福州鼓岭山上的房屋土地免于改革,说这是教会的产业,为培训聚会处同工之用,政府也许会同意的。
”所以,他就发起了这个为保留鼓岭土地房屋免于土改的联合签名。在上海由长老布置各家执事,在擘饼聚会后宣读这份申请书,请弟兄姊妹盖印或签名。
同时通过福音书房全国聚会处通讯簿,将申请书寄到各地去,请他们签了名后,汇总到上海来。这样约有四百多个教会四万余人的签名单都汇总到上海来了。
倪弟兄就将这份申请单寄到福州人民政府去。但是福州人民政府没有批准。原因是他们从上海知道我们没有加入三自,而基于此他们不承认我们是正式基督教团体。他们认为只有加入了三自的才能算是正式教会。同时他们知道这块地是倪柝声私人买的,所以一直没批准。
1950年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后,在上海的三自爱国会要我们控诉帝国主义,参加三自爱国会,但我们不承认和帝国主义有任何关系,也不加入三自爱国会。上海宗教事务局从福州知道联合签名的事以后,认为这是倪柝声个人要保护鼓岭山上他个人的土地,而要挟教会中的群众破坏鼓岭土改。
为这件事,他们要倪弟兄检查。因为土地一部分是租给农民,所以从他们看来,倪弟兄那时是地主。后来就由倪弟兄、俞成华、李渊如三人签名印了一份“悔改我们落后的思想”的检讨书,寄往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并送三自爱国会和宗教事务局。
三、带领弟兄姊妹“学习政治”
1951年上半年,倪弟兄从北京参加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基督教团体”会议回沪后,他认为他的思想已经转变过来了。他要领导弟兄政治学习。那时,在学校里的青年弟兄姊妹都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从猿到人这一课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人是神造的,不是从猿进化来的。
弟兄姊妹在各学校单位碰见这难处,都带到倪弟兄那里来,因为他们在这一课上,如果学习不通过,以后就不能加工资或升职,并且会遇到种种难处。倪弟兄说,我们一面是有信仰,一面又是人民。
我们要学习政治,但要结合我们的信仰来学习,所以他在南阳路聚会处召集青年弟兄姊妹开了几次大会,讲神创造的奥秘,从宇宙的自然规律是神创造的讲起,一直讲到人是神造的,人体上的奥秘可以证明这点。
在这情形下,倪弟兄就说让他自己出来带领学习政治。为这缘故,他自己去看许多马列主义的书。之后,他觉得需要把这件事担起来,所以他到宗教局、统战部和三自去反映,说政府明明说不干涉我们的信仰,而我们信仰是根据圣经。
圣经明说人是神造的,要求信徒接受从猿变人的理论等于是要求他们改变信仰。这个问题引起宗教局的注意,他们当然不能说要求信徒改变信仰,所以后来他们改缓了态度,容许信徒不讲从猿变人的理论,只要求他们接受劳动改造社会的观念,对生产积极。
倪弟兄在1951年4月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后,他认为他思想转变过来了,看见了没有超政治的事,看见了没有两个立场,只有一个人民立场,看见了我们可以一面属灵,一面立稳人民立场反对帝国主义,看见了有个人的罪和社会的罪,并看见两个罪的不同。
他说:我相信神在今天乃是要在祂的教会中造出一种新型的基督徒,就是能够把我们以前那一种对于罪的意识、观念和今天社会对于罪的意识、观念配合起来的基督徒。
”并说:“就是在这几个月之中,一、二年之中,要有很大转变。”这是他在1951年8月下旬和9月中旬所说的话。可是在同年6月间,当上海“三自”联络员刘良模先生来聚会处领导搞控诉运动,要倪弟兄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地方教会时,他却百般加以阻挠。
他看到刘良模要发动聚会处信徒群众搞控诉运动,却遭到失败以后,他就看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他自己来领导大家政治学习。那三篇讲话是他想把政治和圣经相结合起来,搞通大家的思想。但是结果怎样呢?新型的基督徒出来了没有?并没有。
有弟兄问他;“假定作人民和作基督徒发生冲突。怎么办?神的要求和人的要求冲突的时候,我是跟着神走呢,或者是跟着人走呢?”他不作正面回答。但是,在会后,和同工长老、执事谈话时,他说:“当人的要求和神的要求冲突时,我们还是要跟着神走,这需要神的怜悯。
”第二天,我在江西路生化办公室,他对我说:“我们要有两个良心,一个是基督徒的良心,一个是人民的良心。这两个良心处理不好,就要出问题。”这就是说有两个是非标准,这两个是非标准如何结合得好,是很成问题的。
倪弟兄在1951年9月中旬讲了〈走那一条道路〉这一篇谈话以后,过了五个月,就是1952年2月,他被东北公安局逮捕,押往沈阳东北药厂批斗,因为他在政治上已经成为一个盗窃国家资财的不法资本家,成为人民的敌人。
1952年7月,上海生化药厂进行五反运动时,我和在江西路生化办公室的一些弟兄姊妹如江睡悟、谈国兴、顾孝颐、黄惠理等,都认为生化厂五反检查队是因为教会不肯加入三自,不肯控诉帝国主义而来搞倪弟兄的经济问题,所以迟迟不肯归队。
在胶州路生化药厂的工人弟兄站稳了人民立场,就控诉倪弟兄,斗争他危害人民经济利益的罪行。生化厂五反检查队对我反复地进行教育,但我听不进去。因为在外面,在教会中有一些人包括倪的妻子张品蕙拼命劝我不要控诉。
我说我不肯作犹大,出卖倪弟兄。因此,在1952年10月10日我被逮捕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捕。政府判了我三年徒刑。到1955年10月10日我被释放了。从1952年10月到1955年10月,在这三年中,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情况,我不知道了。
但是,并没有看见新型基督徒出现。有些信徒是在政治上进步,而在属灵方面放弃,如生化厂的一些青年弟兄李日绪等、以琳印刷所的陈说如等。陈说如为以琳印刷厂要加工资事,坐在长老室里斗争长老。还有其他反抗的如李、汪、张、蓝等,破坏三自运动,组织青年弟兄姊妹读教会殉道史,准备为主殉道。
从1953年到1956年这三年中,青年弟兄姊妹增加得很快。在各大专院校都有青年学生得救了,来参加青年聚会。大专院校青年弟兄姊妹聚会的人数有三、四百人。带领青年聚会的同工有许达微、陈本微等。
四、关于推动移民和办生产事业
除了以上几件事,倪弟兄在这时期又积极推动弟兄姊妹为福音移民出去,特别到边疆地方去。他在1948年上海教会复兴时,就有了移民计划,当年7、8月间,倪弟兄发表了一篇福音移民的工作谈话。8月19日,他在鼓岭训练上提出今后工作的路,强调必须要以移民传福音。
1949年他又提出移民的五条线,分五路传扬福音,把全中国打下来。这件事到肃反时也成为倪弟兄的反革命罪名之一,说他有野心要“以福音消灭革命”。这在前面已经讲过。
除此以外,倪弟兄为着保护工作的款,在这段时期办了许多生产事业。这在前面也详细讲过了。这些到五反时期成了他的主要罪名。
以上所讲的补充了倪弟兄在这两年为主、为教会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