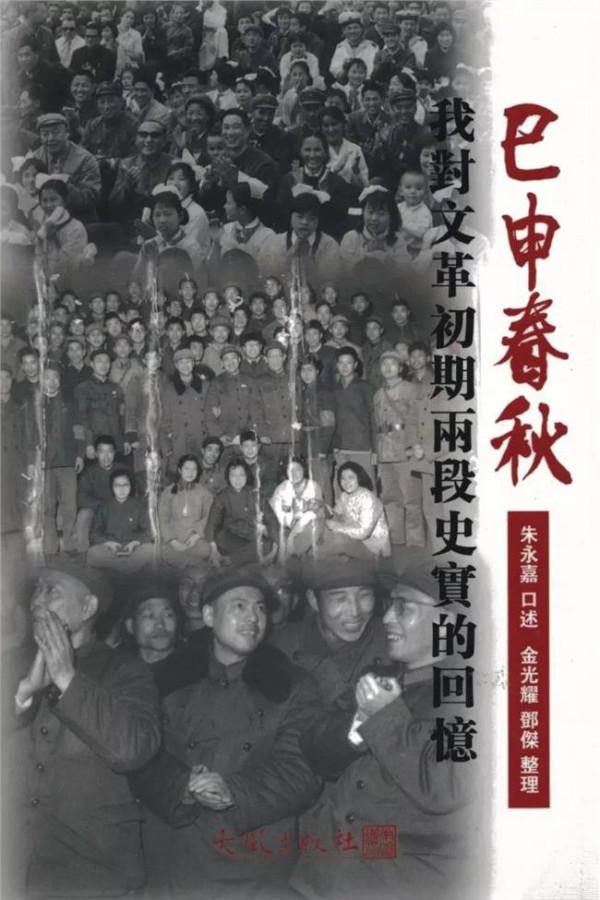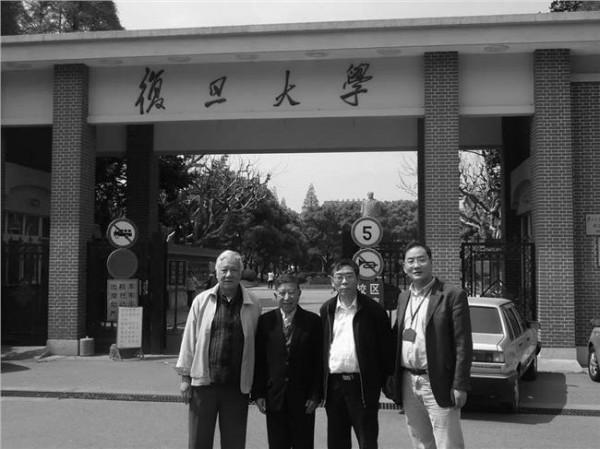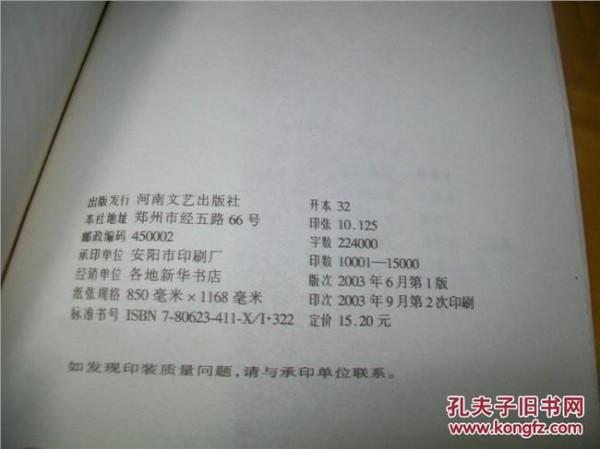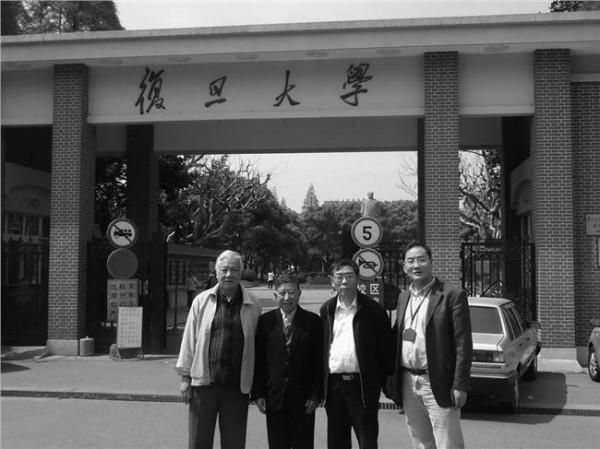谭其骧嘉善 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
按:我们写文章,讨论问题,爱国主义总是一条底线吧。在这一点上,可以告慰自己的,我这一辈子,尊奉谭先生当年的精神,是始终不渝的,在今天,这一点更加重要。我们看一下奥巴马上台以来在中东问题所采取的手法,与他的前任已有所不同,他不似前任那样赤膊上阵,在阿富汗战争是如此,在伊拉克战争是如此,现在懂了,前任的办法太蠢,十年战争,那里的人民不支持你们,你们还得走路,伊拉克撤军是如此,阿富汗这次焚烧可兰经的事件,引起阿富汗人民的抗议和斗争,奥巴马也只能公开道歉,但也很难平息那里民众的义愤。
卡尔扎伊那个儿皇帝不好当啊!一旦美国撤军还不把他丢在油锅里煎呀!奥巴马的做法便不同了,在阿拉伯之春及利比亚的问题上,他就不直接派大量陆军登陆去推翻那里的卡扎菲政权,而是用人权问题作大棒进行心理战,支持那儿的反对派,然后利用自己的海空优势,在那儿狂轰滥炸,卡扎菲政权倒台了,那么利比亚的人权状况是否完美了呢?恐怕更糟,利比亚和北非地区更乱了,很难稳定下来,那么什么人获益呢?欧美的资本家,他们可以安享那儿的石油资源了。
叙利亚的问题也是如此,在联合国强行通过人权问题的决议,为武装干涉制造舆论,这个戏正在上演,不妨慢慢观察其如何流露狰狞面目的。
在伊朗问题上,他们的手法也是大同小异,尽量在那里挑起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挑起叙利亚伊朗国内的矛盾,从而有可乘之机。要最终达到控制整个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目的,奥巴马为什么不直接出兵呢?因为金融危机,债台高筑,军费支持不了。
并非不想直接出兵,而是没有长期支持进行中东战争的能力。所以只能采取捣乱再捣乱的办法。尽管他们拼死拼命地挣扎,即便得逞于一时,但留下的烂摊子无法收拾,故霸权主义日薄西山的命运恐怕很难改变,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奥巴马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呢?其实是一回事,他们不是要重返亚太地区吗?战略重心东移,在东北亚一次又一次频繁的军演,在南海挑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为什么呢?保持他们世界霸权地位,觊觎南海的石油资源,那可是中国的领海,那里有中东一样的丰富石油资源。
所谓普世价值,集中到一点便是人权问题,这是美国对华心理战的一个基本战术,挑起你国内矛盾,海外的一些报刊,不是天天在为那些所谓维权人士请命吗?我不是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而把分散的个别的问题串在一起,那个影响就不同了,它可以借此以动摇你的人心,唯恐天下不乱,最好在你们内部形成有组织的反对派,然后才有可乘之机。
所以我们在这些看起来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和分歧,实际上是有深刻国际国内背景的,今年第一期的《党史纵览》上,刊载了《解密李先念与江泽民的九次通信》一文,李先念同志在给江泽民第二封信中说:"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和西方大国亡我之心是不会死的,他们会采用各种手段来颠覆我们,我建议认真地好好想想我们的问题,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应该引起全党注意的。
"这封信是1989年9月5日写的。李先念同志的这封信今天读来弥足珍贵。我讲这一番话,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时期我文章后面跟帖中的争论,其现实和历史的背景不是更清楚了吗?从目前知识界的思想观念上讲,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分野客观上还是存在的,我在这里只是把问题挑明了罢了,能明白的人该明白了吧。
这里我附带说一下,对美国人民我们始终是友好的,对中美关系我们还是希望向好的方向发展,今年是尼克松访华四十周年,中美关系这四十年来的发展来之不易,我们希望互利互赢,不希望二败俱伤,但许多事由不得我们主观的愿望,从我们自己讲,老祖宗有一句话,还不能忘,那就是"敌存灭祸,敌去招祸",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不得不警惕危险的降临,有一点敌情观念比没有敌情观念,甚至认贼为父的要好。
要有一点爱国主义的情怀
科学是没有国界可言的,作为科学家,总还要有一点爱国主义的情怀,要有一点对自己民族千百年来文化传统的认同,否则的话,怎么对得起生我养我的这一片土地,怎么对得起民族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哺育呢?我们知道清末沿革地理的起步,是从边疆地理开始的,那时为什么要关注边疆地理呢?那是因为列强对我国边界的瓜分和掠夺,历次划分边疆的谈判,列强都欺侮我们对疆界的无知。
这一点谭其骧先生在一九三四年与顾颉刚先生一起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宗旨上,便有所反映。谭先生起草的发刊词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
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知道谭先生开始研究沿革地理时,就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作为一个科学家可不能没有这种情怀。在那个时候,谭先生便立下了宏大的志向,在那篇发刊词中,提出了要有一本供史学工作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要有一本可用的《历代地理沿革图》,要有一部《历史地名大辞典》,要对廿四史中的地理志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一番详密的考订和整理。
那时他还只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搞科学,在青年时期便应该立下宏大的志愿。
毛主席提出要有一本详细的《中国历史地图》供他读史时查阅,正为他实现自己的宏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科学史上重大的成功,都需要有这二方面的条件,这二者缺一不可,从这一点讲,谭先生是幸运者。我五〇年进复旦时,历史系在史学方面知名的有成就的老师不少,真可以说是名师荟萃,如周予同、周谷城、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潘硌基、朱滶、毛起、叶粟如等,五一年五二年,还有蔡尚思、马长寿、田汝康、胡曲园、王造时、陈仁炳等。
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为人还是学术成果,都是谭先生独居魁首,至少他主编的那部八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传之千古。当然这也是与他一起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们三十多年含辛茹苦勤奋努力的结果。所以胡乔木讲的"科学事业是在困难与寂寞中成长起来的"这句话还是对的,作科学事业,要有宏大的志愿,要持之以恒,要耐得起寂寞,才能传之长远。
不能有任何浮躁的情绪,投机的心理,即使骗取了一时的荣誉,那也只是一闪的流星,不可能给后人留下任何值得记忆的思想和内容。
在爱国主义的情怀上,更要一以贯之,有始有终。就以绘图这件事讲,一九五五年在规划这项任务时,是重绘清末民初,杨守敬在其门人协助下编绘的《历代舆地图》,谭先生接受的课题项目的名称叫做"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这个机构编简称"杨图委员会"。
杨图只画中原王朝设置的政区疆域,甚至连中原王朝的疆域都没有画全,所以不包括在今天中国境内的全部领土,也不包括在今天中国境内的一些边疆政权。"杨图"上起春秋,下迄明代,不包括夏、商、周,也不包括清代。
"杨图"所用的底图是《大清一统舆图》,它与今图的差异很大,不利于古今地名的对比,故也无法把它的内容移植到今图上去。所以谭先生主张打破"杨图"的局限,以一八四〇年前清代的疆域为疆界,以今图为底图,重绘历朝历代的历史地图,也就是打破他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上所说的东邻为觊觎我们边疆领土而提出的以清代十八行省作本部这个概念,也就是为列强蚕食我边疆领土提供根据的说法。
其实何尝东邻是如此说,西邻也是如此说的,当年为苏修服务的齐赫斯基也是如此说的,所以在六四年市委才把我们调到华东局内刊去写文章。这个文章刊登在华东局内刊的第一期,文章的署名是罗思鼎,这个笔名怎么来的呢?现在不是正在提倡学习雷锋吗?雷锋日记中不是有一句名言,"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毛主席倡导向雷锋同志学习,所以用罗思鼎的笔名,正是为了发扬雷锋精神而用的谐音,文革时期,我们有许多文章是用这个笔名发的,在这些文章中,至少有一点,那就是爱国主义精神是始终不渝的,至今我们还应懂得霸权主义者分裂我们的国家,觊觎我们的边疆,这样的威胁至今还没有消散。
分而治之,也许始终是列强反华的一个基本手段,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解体,难道不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在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根本问题上,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怎能没有一点爱国主义的情怀呢?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始终对谭先生抱着景仰的心情。
拉郎配,实在难呀!
为了尽快完成重编改绘"杨图"如此繁重的任务,在完成重大科研项目时,自然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既需要外部的协作,协调方方面面的协作关系,内部也需要一支相当数量的队伍,然而如何组成一支这样的队伍,那就大有讲究了。
谭先生在世时,围绕改编重绘杨图的工作,是有一个庞大的团队,设置了一个历史地理研究室,还办了一个历史地理专业,这个工作团队是逐渐形成的。最早参加历史地图绘制工作的邹逸麟与王文楚,是谭先生在北京中科院物色的。
王文楚是复旦历史系一九五六年的毕业生,分配去了北京中科院历史所工作,邹逸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是分配去历史所工作的。他们家都在上海,是尹达提出让他们俩回上海协助谭先生工作。还有就是吴应寿,原来是谭先生的研究生,谭先生还请了章巽先生参加绘图的工作,章先生过去曾与顾颉刚先生一起参加过绘制历史地图的工作。
最早这五个人的团队是谭先生自己选择和认定的共同合作的伙伴,他们尊重谭先生,谭先生也能与他们合作,这是自愿结合的团队。后来谭先生起草成立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名单时,把我朱永嘉也列上去了,他是认可我与他合作的,但我因忙于其他事务,没有具体参加绘图的工作。
五八年大跃进时,复旦党委为了加快绘图的工作,培养青年队伍,所以决定从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中选出周维衍、魏嵩山、赵少荃、林汀水、项国茂、王天良、祝培坤、稽超、朱芳、林宝璋、刘明星十个人参加编图工作,具体人选是年级支部挑选的,那就是拉郎配了,是组织上的安排,并没有好好征求他们本人的意愿,他们参加这项工作之前,对改编重绘"杨图"的工作一无所知。
我问过当时的学生支部书记,你们选人的标准是什么,他们说人老实,坐得住,并没有考虑他们原来的业务和思想基础,就这样匆忙上阵参加工作了。
开头我还帮他们做过一点如何识图点图的辅导,谭先生给他们讲过一些基础知识,他还和章巽先生一起为他们作点图时必须的示范性考释文字,印发给他们作为参考,认真地希望他们成为绘图的新生力量。
因为古今地名的对接,毕竟还是比较机械的工作,郡界的区划就比较复杂了,王朝疆域的区划那就更复杂了,所以辅导他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然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及大跃进的浮躁心理,对年轻人的影响,变成让他们到研究室来占领资产阶级的学术阵地,在敢说敢想的号召下,大轰大嗡的提出高指标,这样势必伤害正常的师生关系,影响绘图的质量,增加审图的工作量,这样便很难在师生之间建立亲密融洽的情感关系。
章巽先生曾对谭先生说,也应该管管这几位学生,不能让他们飞扬跋扈。谭先生说:"他们是来改造我的,我哪里管得了他们。"在那样的场景,又是"拉郎配"式的,参加到这个工作团队的青年人,怎么可能与谭其骧先生建立亲密的师生关系。
加上文革初期斗鬼风的冲击,更是在师生关系上雪上加霜了。从这些青年讲,他们是组织上委派来的,虽然有使命感,但对绘图这样长期枯燥的工作,如何真正培养起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这与谭先生自己挑选的学生如邹逸麟、王文楚、吴应寿在师生的相互关系上不一样。
文革期间,从六九年开始恢复历史地图的工作,领导班子是军宣队的王耀忠和青年人程显道、周维衍,谭先生是一批二用,在那种氛围下,谭先生的心情不会愉快,青年人也不会虚心以师长来对待谭先生。尽管我坚持让谭先生对图幅最后把关,实际上还是坚持当初吴晗确定下来的主编负责制。
谭先生在研究室大批判的环境下不能畅所欲言,我还是让《文汇报》记者采访他恢复工作以后所碰到的问题及他的心情,让他在另一种环境下畅所欲言,又不伤害青年人的革命积极性,然后才能协调好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应该肯定这些青年人在文革期间绘图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但是从感情上讲,他们与谭先生之间很难建立起融洽的师生关系。从青年的视角讲,由于他们是奉命而来的,抱着任务的观点,没有或者缺少对这个专业工作的热爱和兴趣,那就很难自觉地去开拓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尽管他们都把青春献给了绘图的工作,但后来许多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这个岗位。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过程,怪不得那些青年人,许多想法和做法是那个社会思潮下的产物。
我只能尽量协调他们在工作上的相互关系,使绘图工作尽可能比较正常地继续进行下去,无法弥补他们师生之间正常的感情关系。文革结束以后,谭先生后来招的研究生,如葛剑雄与周振鹤情况就不同了。
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需要有一个团队一起来完成,在这个团队内当然要有几个专家和学者来领衔,也要有一支青年队伍来做许多具体工作,他们之间自然形成一种师生关系,尊师爱生是建立亲密师生关系的基础,他们之间既需要志同道合,更需要情投意合,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队伍。把师生关系变成阶级关系,把不同意见的交换变成一面倒的大批判,在科学上要谋求进展,那就很困难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有切身体会,在五十年代末,我写过一篇批判梁启超唯心史观的文章,那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公式,去套梁启超的文章,此文发表在《复旦学报》上,我老师陈守实先生看到以后,给我打招呼,不能那样批评古人。
梁启超是陈先生在清华研究院的老师,陈先生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始终抱着敬畏的态度,谭先生对邓之诚、顾颉刚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不是说对老师或者作古的老人不能批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批评应该抱着直率、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事不是对人,这是老师们自己的表率使我懂得如何尊敬师长。
我曾经是历史系的总支委员,分管统战工作和学术工作,那些老师都是学术的带头人,所以尊师这条线我是守住的。文革初期,我挨批判时,说我是修正主义苗子,走的是白专道路,统战工作奉行的是投降主义,根据是当时我没有回系里贴周予同和周谷城的大字报。
实际上尊师是我在历史系为人的一条底线,不要说大字报,即使在会议上,我从未对自己老师说过一句大声呵责的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然而在求真求是这一点上,也应该是吾不让吾师。谭其骧先生青年时,作为顾颉刚的研究生,关于汉代十三州部的问题,他写信对顾先生的论点提出不同的意见,顾颉刚先生收到谭先生来信后,当天便写了五千字的复信,肯定了谭先生的一部分意见,也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
这是对事,不是对人,是为了求真求是,也是为了尊师。顾颉刚先生同意谭先生在信中的三条意见,不同意的也有三条意见,这样的切磋琢磨,不仅没有伤害师生之间的情感,反而使师生之间的感情更加亲密了。
一九七五年初在北京召开四届人大时,我与谭其骧先生一起去出席大会,我们俩人住在同一房间,那时顾颉刚先生来看谭其骧,谭先生也把我介绍给顾先生,让我在一旁倾听他们深情地叙述往事,并不因为我在而有任何顾忌。
所以在如何处理师生关系上,中国文化有它优秀的传统,我们只能发扬这个优良的传统,师生之间应该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达到情投意合的境界,唯有如此,才能有利于我国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待续)